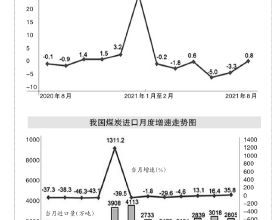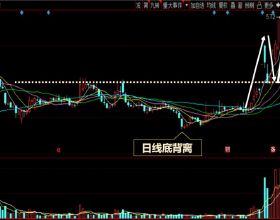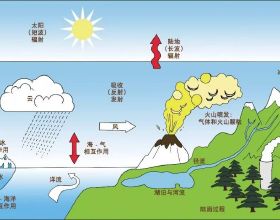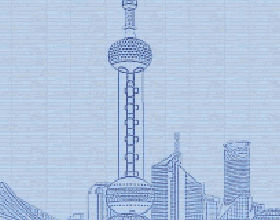陝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確認為西漢文帝帝陵——霸陵,糾正了《類編長安志》等傳統史籍關於霸陵位於鳳凰嘴下的千年誤會。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確認,填補了西漢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環,使西漢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確定,但圍繞著霸陵和文帝的歷史之謎並未完全揭開。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為何一改從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漢的兩千年厚葬舊俗,力行薄葬新風?
文帝為何違背祖制,不跟隨父皇高祖劉邦、皇兄惠帝劉盈入葬咸陽原皇家墓葬區,而是另選遠離咸陽原的白鹿原營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環繞的結構佈局,與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明顯不同,這一耐人尋味的陵制差異,究竟透露出什麼微妙的資訊?
節儉薄葬之謎
早在上古時代,人們就有了靈魂不死的觀念。《禮記·祭義》有“事死如事生”之說,認為財產的佔有不因生死而發生本質變化,財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榮,也是死後生活的保障。殷商時期,這一觀念更加強化,先人魂魄受到後人無限崇拜,社會心理開始崇尚厚葬。考古發掘的殷商貴族王室墓,王陵規模浩大,墓穴精緻豪華,隨葬物品豐富。
周代商後,繼承了厚葬之風,不同階層人士的墓穴和隨葬品規格都有不同的規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隨葬品越多。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超越禮制束縛的僭禮、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締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華厚葬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西漢初年,歷經秦末戰亂和楚漢之爭,人口減少,經濟凋敝。據《史記·平準書》,當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都沒有用四匹同樣毛色的馬匹拉的車駕;“將相或乘牛車”,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車;“齊民無藏蓋”,平民百姓家裡沒有儲蓄餘錢;物價騰貴,“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一萬錢才能買一石米,一百金(10家中產家庭總資產)只能買一匹馬。
雖然自高祖劉邦起,漢朝就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但社會生產力歷經惠帝到文帝時期仍然沒有完全恢復。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客觀制約下,文帝沒有實行厚葬的經濟基礎。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觀上的節儉治國思維。據《史記·孝文字紀》,文帝在位23年間,沒有新修宮室苑囿樓堂館所,沒有增添車馬衣物,平時只穿粗厚絲綢製作的衣服,最寵幸的慎夫人所穿長裙也不會拖到地面,帷帳上沒有刺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為天下人做節儉表率。
文帝“嘗欲作露臺”,讓工程技術部門估價後發現需要耗費百金。文帝認為,“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百金相當於10戶中產家庭的全部財產,他繼承先帝皇位都誠惶誠恐,若修建如此鋪張奢侈的露臺更是罪上加罪,遂停廢此事。
文帝在現世生活中的節儉態度,自然會投射到他對身後陵寢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隨從商周到秦漢近兩千年的厚葬餘風,身體力行地改行薄葬。而文帝實行薄葬,可能還有防止身後被盜墓摸金的顧慮。
由於人們把厚葬當成炫耀地位財富的方式,導致大量珍寶重器聚集地下,盜墓現象由此產生,嚴刑重法都無法遏制。吳王闔閭墓違禮厚葬,結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盜掘。著名的秦公1號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豐厚,榮登遭盜掘次數和盜洞數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發掘此墓時,剛揭開墓上的耕土層,就發現盜洞247個;發掘到第3層臺階平面時,也有60多個盜洞;發掘到槨室時,還有10多個盜洞。考古學家據此推測,秦公1號大墓從漢代一直被盜掘到唐宋,成為摸金校尉們的“網紅打卡地”。
西漢時期,社會精神豪放曠達,江湖氣頗重,“掘冢”挖墓成為常見的發家致富營生,逼得漢文帝必須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慮防盜問題。
中國古代帝陵修建,通常從皇帝即位時就已經開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前177),文帝曾到霸陵視察工程進展情況。看到帝陵風水極佳,施工有條不紊,文帝興奮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如果用北山的石頭做成棺槨,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頭縫隙中,再用漆將石頭、麻絮黏合為一體,那任誰即使有金剛鑽也無法撬開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馬溜鬚頌揚之聲,只有中郎將張釋之從容進言,“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如果裡面有人們想要的東西,比如大量貴重陪葬品,即便是將華山秦嶺等南部山脈全部封禁,也會留有可乘之機,被人打開發掘;“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如果裡面沒有激發人們貪慾的豐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頭棺槨也會安然無恙。文帝聽後,幡然醒悟,“稱善”。
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只陪葬陶製品,不使用金銀銅錫等貴金屬裝飾;甚至“不治墳”,不起高墳,其意不僅是“欲為省,毋煩民”,節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墳冢惹人注目,引來摸金之徒。
後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宮駕崩,遺詔中言“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認為生老病死是天地萬物的自然歸宿,無需哀痛,對死亡頗為看淡;並批評當時的厚葬之風,“當今之時,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帶頭破除厚葬之風,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過三天,全國百姓三天之後必須脫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喪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樣,不得有任何改動。
文帝遺詔並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發現的金銀裝飾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燒製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鐵器、銅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樣三分之一大小,並非實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實際出土,基本上印證了史籍中關於文帝薄葬的記載。
但在距離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親薄太后南陵,考古工作者卻發現了上百件明顯帶有異域草原風格的金銀飾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樣製作,具有實用性,質量等級高於文帝帝陵陪葬。這一發現,不僅印證了史籍中薄太后文帝母慈子孝關係的實情,更隱藏著文帝霸陵選址遠離父皇高祖劉邦長陵、皇兄惠帝劉盈安陵的秘密。
遠離父兄之謎
劉邦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建立漢朝後,在長安西北的咸陽原設立皇家墓葬區,駕崩後安葬於咸陽原長陵,其子惠帝亦在咸陽原營建安陵,陪伴父皇。經過兩代君主的示範帶動,大漢天子入葬咸陽原已經成為政治正確。
漢惠帝早逝無親生子,以呂后、呂產、呂祿為代表的呂氏外戚企圖擁立非惠帝之子為帝,以繼續控制朝政。漢家社稷危在旦夕。周勃、陳平等元老在呂后去世後,果斷髮動政變,誅殺諸呂,立惠帝之弟、且是劉邦在世諸子中最為年長的四子代王劉恆為帝,是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繼承大統,走向人生巔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臨一個在既有空間內無法化解的難題。西漢帝陵規制遵循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後,父為昭,子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廟排位中,父親即始祖兒子為昭,在左;兒子即始祖孫子為穆,在右;始祖孫子之子又為昭,在左;始祖孫子之孫又為穆,在右,以此類推。在昭穆序列中,父子始終異列,祖孫始終同列。
具體到咸陽原西漢帝陵格局,高祖劉邦長陵居昭位,在左。惠帝作為高祖之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長陵右邊即西方。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則應在長陵左邊即東方。但文帝並非惠帝之子,而是惠帝同父異母兄弟,同屬高祖之子,同居穆位,不能居長陵之左即東方,而右邊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營建上處於左右不得逢源、東西無法過問的尷尬境地。
如果繼續在咸陽原營建帝陵,不僅文帝本人的位置無法擺佈,母親薄太后即薄姬的名分亦頗為尷尬。
薄姬原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國公子魏豹妻妾,魏豹本與劉邦共同對陣項羽。後有相面大師為薄姬看相,認為薄姬貴不可言,當生天子。魏豹自認天命在身,遂脫離劉邦中立,試圖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劉邦大怒,派大將曹參滅掉魏豹,將薄姬納入後宮,但“歲餘不得幸”。
薄姬後來在“少時”閨蜜好友——此時深受劉邦寵愛的管夫人、趙子兒兩位美人的幫助下,才得以侍寢。據《漢書》,薄姬在侍寢前告訴劉邦,“昨暮夢龍據妾胸”,昨夜夢見有金龍鑽入懷中。當夜薄姬便“有身”,十月懷胎後生下文帝。但薄姬生子後並沒有改變境遇,而是繼續不得寵幸,長期沒有晉封。
正是因備受冷落,薄姬才被嫉妒心極強的呂后放過,在劉邦死後隨同此時已經受封代王的兒子到代國居住成為代國太后,而不是如劉邦其他寵姬一樣幽閉宮中。
文帝即位後,薄太后母以子貴,從代國太后升級為大漢太后,但在她面前仍然有一個無法邁過去的正牌太后呂后。如果文帝在咸陽原營建帝陵,母親陵墓也要一起安放此處陪葬劉邦長陵,在禮制等級規格上不免要低呂后一等。這是名列“二十四孝”、為母親親嘗湯藥的文帝斷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只能另闢蹊徑,選擇在長安東南的白鹿原營建帝陵,以便按照大漢太后的規格來設定母親陵墓。
而文帝之所以選擇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寢,亦與漢初內憂外患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這一形勢不僅關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選擇,更關乎霸陵內部的陵墓佈局。
陵墓佈局之謎
西漢初年,中央朝廷同時面臨西北匈奴和東南諸侯國的雙重壓力。當年劉邦之所以選擇西北咸陽原為皇家墓葬區,其意即是透過在皇陵周邊大規模設定陵邑、充實人口,修建長安西北防備匈奴南下的門戶屏障。文帝選擇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低、東南高的高敞地形優勢,能夠對東南各諸侯國形成地理壓制態勢。
外攘匈奴、內安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廷內部凝聚力的增強和皇帝權威的加強。高祖劉邦雖是開國之君,但其天下是與功臣共同打下。劉邦雖然透過叔孫通制定朝儀方知天子之貴,但從其晚年無法更換太子一事,可以發現其皇權仍然被功臣集團深度制約。惠帝劉盈仁懦,不僅被母后控制,還被功臣壓制,遑論振興皇權。
文帝入繼大統後,運用一系列“區別對待”“打拉結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陳平、周勃一文一武為首的功臣集團,對朝廷高層進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舉其上臺的功臣。同時起用賈誼等後起之秀,採用賈誼“列侯就國”之策,將周勃等擁有侯爵的軍頭漸次趕出長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擺脫功臣集團在長安對皇權的牽制。
隨後,文帝在賈誼等人的謀劃下,有意透過禮儀制度建設,抬高皇帝威嚴。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區發現,100多個象徵官署機構的外藏坑都圍繞著帝陵,呈現出一種向心式的政治佈局。這一佈局形式,在高祖長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沒有出現,反映出西漢歷史程序中皇權增強的事實。
正是在內部凝聚力增強和政令統一的基礎上,文帝才能將主要精力用於處理諸侯國問題以加強中央集權。文帝部分採納賈誼《治安策》中“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初步解決了齊國和淮南國兩個最大的政治隱患,使得兒子景帝能夠用短短三個月就輕鬆平定吳楚等國反叛中央的“七國之亂”,最終為“文景之治”的出現和兩漢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吳鵬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
來源:中國青年報
欄目主編:張武 文字編輯:李林蔚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邵競
來源:作者: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