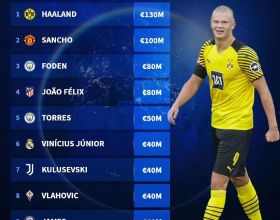那條街拐角處的洗衣店很有名。其實我作為本小區居民,倒從未覺得這家店如何與眾不同。直到有一天一個法國記者朋友跟我說,說這家店是整個巴黎市區裡最便宜的洗衣店之一。我開始以為他也曾住在附近,可他自己說從來沒住過這邊。那有什麼樣的理由能讓他對這麼一家小洗衣店的價格這麼熟悉呢?——“因為我愛打橋牌,我記性好!”
那家店的店主總是愛跟顧客開玩笑。有一次,當我把信用卡給他時,他把卡插進卡機,忽然抬頭問我:密碼是多少?
我一下子險些把幾位數的密碼脫口而出。話到嘴邊我突然意識到,不對啊!怎麼能讓別人幫我輸密碼呢?正恍惚間店主已經把卡機遞給我、讓我輸密碼了,臉上掛著嘲弄或者還摻點歉意的笑,明亮的眼睛緊緊的盯著我。
沒多久,這家洗衣店的老闆似乎已經換成別人了。明亮的眼睛再也不見。這十幾年來,巴黎的小鋪小店,也就是中國人口中的個體戶,似乎越來越多。而個體戶之間的換手,似乎也越來越頻繁。各種小生意,洗衣店、小食品百貨超市等等等等,隨處可見。有人說這跟社會風氣的流行、時尚潮流有關係。比如說,越來越多的男人不願意留大鬍子,所以就需要有理髮店,經常去刮一刮。比如說,女孩子現在更願意對已經買來的時裝添點自己的奇思妙想,加上花邊兒啊,多釘個扣啊,自己動手加長或者改短啊。所以各式各樣的小縫補店越來越多、生意興隆。而在房前屋後或者陽臺內外自己動手DIY修剪花草、增添設施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小五金器材店、各種小工具的租賃店遍地開花。但依我看,這恐怕更多的還是因為經濟大環境。老百姓有養家餬口的需求,政府透過各種手段,在稅收、用工等政策上“放水”,儘可能滿足這種需求,同時也減輕了就業壓力,降低了社會治理的成本。
而這家洗衣店斜對面原來已經廢棄不用被當做倉庫的鋪面房,現在也被房東拿出來出租。原籍阿爾及利亞的薩伊姆把這房子租下來,專門理男發。光剪不洗10塊錢。這在巴黎來說實在是不算貴。不到30年前那時候,街面上最便宜的同樣的一個男發,也就是這個價錢。不過那個時候,是法郎。歐元開始實施的時候,6.5法郎等於一個歐元。要是這麼算,那就是巴黎男性平民剪推頭髮(還不包括洗)的基本生計,二十多年,漲了6.5倍。當然這麼算肯定不科學,因為時間地點人物都轉移了。這個名叫薩伊姆的阿爾及利亞人,理髮不光用電推子推,還要用剪子剪幾下。還給你用一個一次性的刀片刮刮鬢角。這些都是他的成本。
在薩伊姆這裡理髮,還有一個成本要付出,就是你得聽他嘮叨。他對法國政府從來不滿意。“政府說讓大家免費打疫苗,那一定是個陰謀!法國沒什麼東西是免費的。現在疫苗免費,以後一定會從別的地方找補回來!”我不知道,如果政府要是跟他收錢,他會怎麼說?“都是政治。不是法國國內政治,就是國際政治!”
薩伊姆還順便提到說,他遠在阿爾及利亞的家人中,父母、姐姐,姐夫,一共4個人都在這場新冠疫情當中去世了。“他們有的是年齡太大,有的有糖尿病等基礎病。”那他們都打疫苗了嗎?我話到嘴邊兒,想一想,算了。我還是別問了。
有關抗疫,法國人提出來的另一個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是:國家,和代表國家權力的政府,有沒有權力要求老百姓閉門不出?有沒有權利因為什麼理由,不管是抗疫還是避險;不管是為了你好,還是為了他們管治方便,而實行宵禁、禁足、封城或隔離?這個話題好多人跟我提過,不過當我面說的極其激烈、聲調激動的,是安託萬。安託萬剛剛出了校門就獲得一家房地產中介公司的“無限期勞動合同”。這是法國用工勞動合同的一種,類似於鐵飯碗。是最受年輕人追捧的一種工作合同。安託萬得到的不是臨時工,也不是季節工,更不是實習合同,而是一份正式的無限期勞動合同。這個母親為波蘭人父親為法國人的雙重國籍的年輕人,從小受的是法國教育。“我們法國人理解的自由、個體、集體等等這些概念,和它們之間的關係,跟你們中國人所理解的,肯定不一樣!”嗯,有道理!頗有些“互不干涉內政”、“尊重你們自己的選擇”、“雖然你們的做法我有些看不慣,但是我絕不說出來的”和道路自信的大國外交風範。
此次已經兩年多的抗疫的過程,所體現出來的法國人的一些特別品質,是一次最集中的體現。這些特別品質包括,譬如說;“不自由,毋寧死”;“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對權威的蔑視,——無論是政治權威還是專業權威;得過且過的僥倖心理;反對一切成見;保護少數人的意見(“你有擔心被傳染上的權利,他也有不怕被傳染上的權利。”) 。
這不,近幾天,連續多日,法國染疫病例每天都在6萬例左右。疫情爆發以來,總人口6700多萬的法國,新冠累計感染者846萬人,佔比12.6%,死亡12萬人。同時,疫苗接種成績也不錯,覆蓋面已達到89%。
洗衣店老闆明亮的眼睛也好,薩伊姆的抱怨也好,還是安託萬義正詞嚴的質問也好, 在大家還都不得不同病毒繼續纏鬥下去的時候,哪些細節會深存心中並令人感慨不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