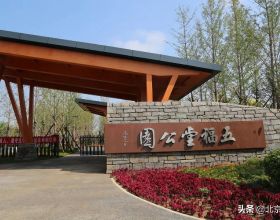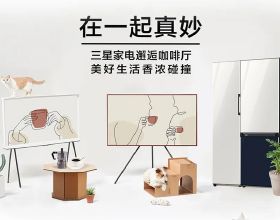一、前言
對私有財產突擊式地課以重稅,在古代屢見不鮮,朝廷多巧設名目,從黔首中汲取財富。然像漢武帝這種赤裸裸地公開搶劫,鼓勵民間互相檢舉的,歷史上極為罕見,也極具代表性,更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開了個惡頭。
二、算緡與告緡
緡,本意是穿銅錢的繩子,後來就成為了貨幣單位,一緡錢就是一貫,一千錢。而一算也是個單位,為一百二十錢。所以算緡告緡是寫在臉上的經濟政策。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漢武帝接受了御史大夫張湯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議,下令徵收算緡錢。規定商人“率緡錢二千而算一”,手工業者“率緡錢四千算一”,對不是三老的、北方邊疆騎士的卻能擁有軺車的人,也要徵收一算,若是商人就要加倍。船戶如果擁有超過五丈長的船,也要徵收一算。對於瞞報者或申報不實的,一經發現,罰到邊境戍守一年,並沒收所有資產。
算緡的出現,是和當時漢武帝與匈奴之間的戰爭有直接關係。戰爭是耗費財富的無底洞,《史記·平準書》就明確記載了驚人的消耗烈度:“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當時朝廷財物匱乏,將士常常領不到俸祿,這對局勢極為不利。為了更大程度地從民間汲取資源,漢武帝首先在貨幣上下手,收歸鑄幣權,作皮幣鑄白金。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世人皆知“犯我強漢,雖遠必誅”,卻難知民間要為之承受多麼大的負擔。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商人們趁著變更幣制的機會,囤貨以逐利,這是朝廷絕不能接受的,引來了更大規模的課稅行動,朝中大臣們也皆言貧富差距已然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算緡令下達後,富豪們反而頂風作案,爭相藏匿自己的財富。朝廷與黔首之間永遠是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迴圈鬥法關係,眼見算緡遭到抵制,朝廷頒佈了兩個辦法。
一是樹立正面典型。凡事都會有例外,人群中也自然會有背叛階級的個體。在富豪們爭相藏匿財富的風潮下就產生了一個異類,此人名叫卜式。卜式極善於牧羊,頗有產業,他向天子上書表示願意獻出一半的家業來資助邊疆戰事,他還說:“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繳納給官府),如此而匈奴可滅也。”過了數年,漢武帝發現還有這麼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對他大加表彰,拜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20等爵中的第10等),昭告天下。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卜式那樣有崇高的覺悟,樹立典型的做法收效甚微,民間還是不肯乖乖交錢,於是第二種辦法應運而生,即告緡。告,乃是告發的意思。朝廷為了讓告發之風盛行,對告發者許以了豐厚的獎賞:“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這是與對瞞報者的懲罰相配套,瞞報者的財富被沒收後,告發者足足能夠獲得其中一半。
三、適用告緡的不只有商人
《文獻通考》的第十四卷對這場運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做了很好的總結:“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故擇其關於商賈者登載於此,而餘則見《雜徵榷門》。”馬端臨將受害者分了兩個群體:一類是在算緡法下受到懲處的不法商家;另一類就是被告緡法波及到的人,他們雖然並非商人,但只要有所積蓄,都被認作是“商人”。
告緡法可以說是算緡法向民間的擴大,漢武帝透過鼓勵互相告發來獲取遠遠高於算緡帶來的財富。即使將範圍擴大到民間,朝廷也仍有必要選派一群人作為骨幹,來有預謀、有組織地進行不可控的運動。這群人就是酷吏,與告緡法有較大直接干係的有三位,一個叫張湯、另一個叫楊可、還有一個叫杜周,在《史記·酷吏列傳》中,他們都是榜上有名之人。
這三個人在執行告緡上分工合作:張湯是向武帝提建議的;楊可是主持者——“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幾乎沒有逃過一劫的;而杜周是負責治罪的,凡他經手的案件,也幾乎沒有嫌犯能無罪釋放。在從上到下的“通力合作”中,朝廷聚斂的財富是空前的:“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
四、算緡告緡真的能讓朝廷長久受益嗎?
算緡告緡的初衷很簡單,就是解決與匈奴間的戰爭經費問題,是個短期應急的政策,但現實遠沒有這麼簡單。算緡告緡實施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公元前119——公元前110)。
漢武帝時期,匈奴的最高統治者是伊稚斜單于(chá),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王庭的決戰中,伊稚斜被大將軍衛青擊潰,並在五年之後撒手人寰。伊稚斜的死意味著漢朝之後再無像樣的外敵,之後也再無如此大規模的征戰,問題就出在這裡,伊稚斜雖死,算緡告緡卻仍延續了四年之久!而且越往後發展,它的負面影響就越明顯。
首先是朝廷的腐化。在楊可主持的告緡令下,上林苑堆滿了財物,漢武帝便拿來修建昆明池,以高達十餘丈的樓船充實其中,還修建著名的柏梁臺,過上了更為奢華的生活。各級官僚當然也是賺得盆滿缽滿,朝廷把徵來的緡錢分給各個官署,水衡都尉、少府、大農令、太僕這些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僚,常常在各郡國整治沒收來的土地。而且在當時還出現了“冗官”的現象,發展到漕運都難以滿足的程度:“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柏梁臺不久便毀於大火,這反而激發了漢武帝更強的好大喜功的慾望,宏偉的建章宮問世。
其次是底層的墮落。孟子曰:“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如果百姓沒有自己的產業,或者說自己的產業時刻面臨著被剝奪的危險,那麼整個底層就會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就拿“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為例,當百姓發現檢舉他人是無本萬利的行為時,當然就會選擇捷徑,為什麼要透過自己的雙手去幹正經的行當?那太累了。
而且這種風氣會衍生出享樂主義的盛行:“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因為百姓也知道自己的錢是透過檢舉而來,今天你可以透過檢舉別人發財,明天別人也可以透過檢舉你而發財,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儘可能地把錢花光,這樣我既獲得了享受,別人也抓不到我的把柄。而良心未泯的人即使不會去檢舉別人,也不敢再去奮鬥了,而是選擇“躺平”以自保。
第三就是從長遠來看,這種風氣反而不利於朝廷徵稅,算緡告緡註定是竭澤而漁的結果。《鹽鐵論》中的儒生們就看得很明白,他們儘管從道德上鄙視工商業者,但也反對橫徵暴斂,因為這會破壞整體的生態環境:“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睏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谷熟而舊谷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併曜,晝夜之有長短也。”
圍繞著鹽鐵官營問題,桑弘羊與儒生們展開了激烈交鋒,這就是著名的“鹽鐵之議”。而桓寬根據記錄寫了《鹽鐵論》,成為研究西漢中期歷史和桑弘羊的重要史料。
第四是邊疆武備問題依然嚴峻,算緡告緡連短期的目標都完成得一地雞毛。元鼎四年(公元前110),漢武帝北出蕭關,在新秦中組織狩獵,以此檢閱邊防軍隊,但是他發現一些地段千里之內沒有防禦工事,因此他把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全部誅殺。這件事成為了武帝最終廢除告緡令的誘因,既可見他的龍顏大怒,也可見他對算緡告緡結果的反思。
五、結語
太史公作為親歷者感嘆道:“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算緡告緡製造的悲劇,他也認為是事物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互相影響所導致的。這正是短期政策不可避免的後果,絕不僅僅是完成短期目標這麼簡單。短期政策旨在以有限的時間集中最大的資源,它所帶來的傷害姑且不算,這麼多的資源被集中起來,任誰都難以坐懷不亂。平心而論,短期政策確實能解燃眉之急,但是藥三分毒,它總不能當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