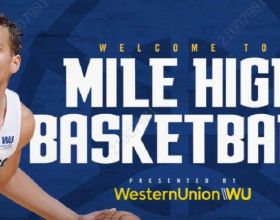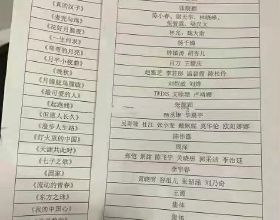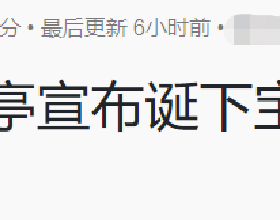“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這篇僅85字、出自蘇東坡之手的《記承天寺夜遊》小散文被網友送上熱搜,因各種表情包模仿了張懷民被蘇東坡半夜叫醒時的樣子,加上“你這個年紀,你這個階段,怎麼睡得著”“砰砰砰!懷民:誰啊?蘇:懷民亦未寢”之類文字,將古今感受串聯了起來。張懷民一夜之間成了“新梗”(梗即笑點)。
張懷民火,源於兩點:
其一,該文被收入中學課本,屬必背內容,為形成“劇場效應”奠定了基礎。
其二,強制學習造成閱讀體會與內容分離,學生們只好用戲謔來建立親近感。文學是鮮活的,如果文學教育變成了經學教育,不給孩子們以創作空間,他們就會用自己的方式再創作。不應忽視這種“魔改”的價值,它和藝術大家馬塞爾·杜尚給蒙娜麗莎像畫上鬍子,成為名畫《帶鬍鬚的蒙娜麗莎》,有同樣的後現代精神,應保護這種創造力。
尷尬的是,張懷民雖被梗學重點關照,可他究竟是誰,幹過什麼事,史籍闕載。不過,和通常印象相反,當時張懷民的權力大於蘇東坡,如果不是好朋友,蘇東坡未必敢招惹他。
長城是日夜不休建起的
張懷民火,因為他在蘇東坡筆下是被動者,為安撫蘇東坡的頑皮,他不得不犧牲一夜安眠。不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這都非小事。
楊聯陞先生在《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中說:“農人每年的時間表,無論對統治者來說,或對農人本身來說,都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千百年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認為是天道,不可動搖。
《周禮》中記載:“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據《唐律疏議》記載,日暮至五更二點(凌晨3時24分至3時48分,古代每點相當於今24分鐘)是宵禁時間,夜行屬犯夜者,罪至笞刑20下。
不過,據學者倪根金考證,兩漢之際桓譚的《新論》和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都有材料可證明漢代人已熬夜。
《新論》稱:“扶風漆縣之邠亭,都言本太王所處。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市,如不為期,則有重災咎。”意思是邠亭(今屬陝西彬縣、句邑)有夜市,百姓都會參與,誰不來,就會遭災。
《說文解字》在解釋“豳”字時,稱“民俗以夜市”。
除了夜市,還有“夜作”,比如《水經注》說:“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南越也。晝警夜作,民勞怨苦。”就是說長城是靠日夜不休建起的。
在古代,婦女織布多在夜間,因為織布收入少,據學者黃今言計算,熟練女工織布一年,收入4000錢,農耕一年則7200錢。所以女性白天從事農活,晚上織布。可見,古人想求個安穩覺,也非易事。
李白也喜歡熬夜
熬夜初期是被迫的。據學者徐暢考證,秦漢時百姓服役,政府按季節分為春程人工、夏程人工、秋程人工、冬程人工,夏程人工的工作量是冬程人工的1.96倍,因為夏天更適合熬夜。
《後漢書·廉範傳》中記:“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範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
允許晚上幹活了,就把老百姓高興成這樣。
在古代,有些工作必須在晚上進行。比如牛馬需半夜喂草料,所謂“馬不吃夜草不肥”,據《居延漢簡》記,晚上馬用草料佔到全天的50.8%,“養馬奴”須半夜起來幹活。
漢代末期至南北朝時期寫成的《古詩十九首》中,有“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時熬夜已有感時傷生、寄託情懷的意味,其實熬夜會增加患抑鬱症的機率,抑鬱症患者也更喜歡熬夜。
唐代中期,在商業推動下,禁夜令已鬆弛,詩人王建在《夜看揚州市》記下繁華景象:
夜市千燈照碧雲,
高樓紅袖客紛紛。
如今不是時平日,
猶自笙歌徹曉聞。
唐代杭州是“駢牆二十里,開肆三萬室”。晚唐詩人薛逢則寫道:“洛陽風俗不禁街,騎馬夜歸香滿懷。”而李白的《靜夜思》《月下獨酌》《飲中八仙歌》《夜宿山寺》等,都暴露了他喜歡熬夜。
蘇東坡為什麼愛熬夜?
不過,李白的熬夜比起蘇東坡,便差了不少。
蘇東坡的《石鐘山記》《後赤壁賦》都是熬夜之作,此外還有《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韻前篇》《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夜泛西湖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書上元夜遊》《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上元夜》《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等詩詞。
蘇東坡為什麼愛熬夜?因為北宋夜生活太豐富。
宋代至少有60多個城鎮存在夜市。學者李華瑞指出:“宋朝的酒茶課額一般可達2000多萬貫,其中來自夜間經營收入的份額可能不低於30%。夜間經濟整體在國家財政貨幣收入總額中所佔比重,保守地估算應在5%至10%之間。”
蘇東坡出仕後,長期生活在汴京和杭州,這裡夜市尤其發達。據《夢粱錄》載:“如頂盤擔架賣市食,至三更不絕。冬月雖大雨雪,亦有夜市盤賣。至三更後,方有提瓶賣茶。冬間,擔子賣茶,傲子慈茶始過。蓋都人公私營幹,深夜方歸故也。”《東京夢華錄》亦載:“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耍鬧去處,通宵不絕。”
北宋皇家較開明。宋太祖在乾德三年(965年)為方便商家,敕令:“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宋仁宗時,一日聽絲竹喧譁,一問才知是附近酒樓喧譁,有宮人說,宮中這麼冷清,外面卻這麼快活。宋仁宗說,如果宮中也這麼熱鬧,酒樓就冷清了。
高度包容下,汴京馬行街、北州橋成“都城之夜市酒樓極盛之處”,每晚“人物嘈雜,燈火照天”。
對於張懷民,記載不多
習慣了汴京夜市的繁華,蘇東坡到黃州後,自然也耐不住寂寞。
黃州今屬湖北省黃岡市,在唐代和北宋,它是貶宦地,即蘇東坡詩中所說:“索漠齊安郡(黃州又稱齊安郡),從來著放臣。”唐代杜牧曾被貶黃州兩年半,宋代被貶到這裡的有王禹偁、張耒、夏竦、蘇東坡、吳居厚、張懷民等。
黃州位於天下之中,但遠離政治中心,當時較貧困,生活條件好於嶺南。貶到黃州,算是寬大處理,一般只收初犯。南宋時,北方盡失,黃州靠近邊境,不再作為貶謫地。
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名義上是團練副使(相當於今保安隊副隊長),但那是散官(不管事,只留名頭),因他身負刑事責任,不得簽署公事。
烏臺詩案是李定、舒亶誣告蘇東坡寫詩“譏刺政事”,宋神宗有意寬赦,卻不敢出手,稱:“蘇軾積怨太多,恐言官們因蘇軾的事害朕。”蘇東坡在獄中被關押100多天,被提審10多次,最後被髮配到黃州,司馬光、蘇轍等29人受牽連。
張懷民雖是被貶到黃州,但無刑責,一度任黃岡縣令,有實權。
對於張懷民,只有兩段記載。
一是蘇轍在《黃州快哉亭記》中說他:“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
二是《東坡志林》載:“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僕。”
這些記錄證明張懷民是放達之人。
貶至黃州詩風大變
蘇東坡到黃州後,詩風大變,從早期追求“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開始反思“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
在黃州,蘇東坡的俸祿降至“祿米62石/年、月俸650錢、食料300文/月”,他寫信給秦少游說: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慮之。
無可奈何,蘇東坡只好親自耕種,即:“餘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餘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來而嘆,乃作是詩,自憨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在黃州,蘇東坡共寫詞100多首,在生平全部創作中佔1/4,撰文800多篇,佔全部創作的1/3,還有200多首詩,佔全部創作的1/13。蘇東坡自己都覺得寫得不錯,給好友陳季常寫信說:“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寫道:“(蘇東坡)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意思是我和我哥原本文章水平還差不多,到了黃州後,蘇東坡的文章突然功力精進,我再也比不上了。
黃州是蘇軾變成蘇東坡的關鍵點。
自己定位成“閒人”
林語堂說:“蘇東坡最可愛,是在他身為獨立自由的農人自謀生活的時候。”
剛被貶到黃州時,蘇東坡用兩年時間研究《易傳》《書傳》《論語說》,並第三次抄寫漢書,即“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
好友陳季常邀蘇東坡去武昌玩,蘇東坡不敢去,說:“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雲‘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意思是怕閒著沒事的人傳閒話到汴京,那就不是小事了。黃州偏狹,“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苦悶可知。
寫《記承天寺夜遊》前後,蘇東坡的狀態是:
我謫黃州四五年,
孤舟出沒煙波裡。
故人不復通問訊,
疾病飢寒疑死矣。
為平息內心苦痛,蘇東坡曾到安國寺借禪室“閉門思愆”,在《東坡志林》中,蘇東坡記錄了讀《壇經》心得:“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
透過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蘇東坡開出“靜而達”的境界,在《與子明兄書》中,他寫道:“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間,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
正因“靜而達”,才有《記承天寺夜遊》中“閒人”的自我定位,月夜找張懷民,因宋人有“雅游”之習,士大夫不用酒肉、歌舞、女伎,只與兩三好友為伴,隨意漫步。
張懷民這樣的好友不僅在古代,在今天也屬難得,只是功課壓力太大,孩子們難有耐心仔細品味,只願給他貼張苦臉。(責編:沈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