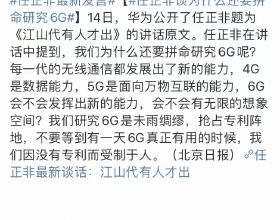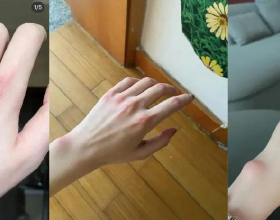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儀式感相對比較淡漠。這主要是出生年代物質匱乏以及社會運動頻繁導致社會交往受限所致。
儀式感就是將日常行為儀式化後使某一天的日子特別有意義,甚至把生活安排得精緻甚至是奢侈,以賦予其具有紀念意義的行為。比如:生日。
在印象中,小時候都會爭著去給上了年紀的人去祝壽。老年人生日那天,一般本家親戚都會前往祝壽,菜品相對較平時豐盛很多。我們爭著去的目的,就是想吃平時少見的菜品。小時候,本身對祝壽的意義是沒有認識的。
七十年代,給別人祝壽的禮品也很廉價,一包白糖,一把麵條,一封餅子也就足夠,講究的人還會配上一斤白酒,那時的白酒是憑票購買。當然,主人也是用攢了又攢的臘肉招待客人。這些現在看不起眼的禮品和菜品,在當時是非常匱乏的,如果是憑票購買的物品更顯珍貴。
八十年代初,物質供應短缺的現象開始改變,到九十年代,物質供應基本不存在短缺現象,人民生活有了極大的改善,這是黨為人民謀幸福的結果。
土家族有這樣的風俗,不管自己多大,原則上,如果爺爺、奶奶或者父母任何一人健在,自己都是不能慶賀生日的。然而,現在的人們似乎都已經忘卻了‘母在不慶生,父在不留須’的這把傳統枷鎖。現在有些幾歲的小孩過生都有幾桌客人,其實,這也並沒有什麼不好,只要不是太張揚,能夠彰顯社會和諧和文明,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的先哲喜歡用獨到的視角審視人生百態。他們從十歲到九十歲都作了概括性的表述,並用哲理性的語言表述人生世態。如:先哲們說九十老童,你看凡是年逾九十的人幾乎都是五官縮蹙、須稀發疏、雌雄難辨,哪個不是丟三落四,耳聾口拙、你說東他說西的。精準的概括令人忍俊不禁,也讓人擔心受怕。
按先哲們的概括,五十歲是知天命的年齡。原因是因為五十歲的人常常會有感慨人生的習慣,並且在感慨中會發現自己走過的路有錯誤的選擇也有正確選擇。
五十歲的自己,自認為,從小到大,老天對我還是公平的,給了我機會,也給了我失去後的補償。當然,補償是相對而言的,因為,本身不存在純粹的補償。
雖然老天儘可能公平的給每個人平等的機會,可在漫長的人生路中,依然會因為人性的優柔寡斷產生奇蹟和遺憾,並不是沒有差距,而是差距一直存在。這是因為有些機會我們意識到並抓住它,而有些機會從手中滑失過後,我們才意識到機會的寶貴。所以,有些感悟一定是痛徹心腑的,而有些感悟是喜上眉梢的。
五十歲回頭看,機會的選擇常常會交織成“性格決定命運”的認同。
其實,人最終的生活標準就是安身立命,標準應該就是無憂和不攀比。妻持家寬裕為無憂,為官者無貪婪為無憂……;學者,著作不求於等身,業者,不求於首富為不攀比……。
無憂和不攀比只是一種境界,其實,人都是有憂慮的,只是憂慮不同而已。有的為事業憂,有的為子女憂,有的為生活憂,有的為過往遺憾憂……。無憂雖然雅緻,這只是對生活的嚮往和追求,真正無憂的人我想是不存在的。
五十歲回想過往,我也有憂。
從職業看,我有憂。因為最好的職業是當官,而我一介草民,無職無權,自然有有憂之理。
從身高看,我有憂。淨高不足160釐米的我,年輕時,總被美女的父母,因為身高的原因把我拒之門外,也有美女連拒之門外的機會都不給,還直接說我三級殘廢。其實,單論長相我還是過得去的。
我有一鐵桿兄弟,姓汪。這姓少,不好記,最開始我是這樣記的,汪—汪汪—汪,沒幾天就記住了,效果挺好的。
他比我高多了,但從汪兄身上就會發現身高和長相是不成正比的。但他能娶一個漂亮賢惠的妻子,也沒有遭受拒之門外的尷尬,估計他用了四種欺騙手段,一是死纏硬磨;二是憑經驗挑逗;三是裝可憐的樣子;四是假裝勤勞吃苦。
有人說這是男人的套路,五十歲回頭想,其實,這就是壞人的伎倆。我可能也是因為帥氣的長相害了我,認為東方不亮西方亮,假裝清高,臉皮又薄,又不死纏,又無經驗,導致二十八歲才喜得千金。五十歲回頭想,如果我也像汪兄一樣長得情況緊急,可能也是妻妾成群。
從打牌看,我有憂。十打九輸,不論牌類都是如此。舅子說:“打牌莫問他輸贏”;妹夫說:“逗嘛,逗舅母子還要輸”,別說,烏鴉嘴還真靈。可是,狗改不了吃屎呀!我不說話是要憋死人的。哎!雖是技不如人,可承受洗刷之苦,是誰都憂啊!
其實,憂與無憂的人生都是一生,重要的是憂並快樂著,才是人一生的最高境界。
五十歲是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過生,雖不隆重,但很溫暖。在這裡我非常感謝妹夫一家和舅子一家的精心安排和準備,也非常感謝所有記住我生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