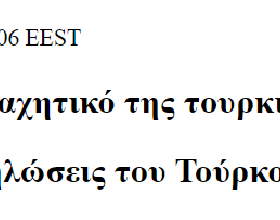作者:劉成章
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一天,我突然從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裡,聽到一首令人耳目一新的信天游:
羊啦肚子手巾喲三道道藍,
咱們見個面面容易哎呀拉話話難。
一個在那山上喲一個在那溝,
咱們拉不上那話話哎呀招一招個手。
瞭得見那村村喲瞭不見那人,
我淚個蛋蛋拋在哎呀沙蒿蒿林。
這首歌是由民間歌手王向榮唱的。他富於感情的嗓音,像煙雲,也像鷹喙,在陝北高原的蒼涼曠野上,追尋、呼喚著愛。其時,我正在陝北一個歌舞團從事專業創作,藝術鑑賞標準可謂高。可是,我還是一下子被它震住了,激動得不能自已。
信天游浩若煙海,以千千萬萬計,不過,其中有金鐘也有朽木墩墩。而這首信天游,光彩奪目,鶴立雞群,是當之無愧的金鐘。
印有三道道藍的羊肚子手巾,白是白,藍是藍,其意象悲切悽婉。它從長風陣陣的高天落下,在一片靜謐中飄蕩,一下子就把你拉到黃土高原的蒼茫中。
郭紅松繪
我國古代的優秀山水畫,常常描繪大山大水,氣勢浩闊,開圖千里。而這首信天游,也可以說是一幅傑出的山水鉅製,展現出的是全景式的陝北。當“見個面面容易哎呀拉話話難”唱出的時候,你不能不感受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苦難而艱辛,勇敢而頑強。接下來唱出的音符和字詞,散射著情感的溫熱和醇香,是無悔的沉醉,是苦苦的尋求,充溢著悲愴和悽美,裡邊沒有任何深奧主題、哲學意義以及說教的痕跡,純粹是抒發人的血肉性情。
過去,陝北人煙稀少,滿目寂寥,除了山疙瘩還是山疙瘩,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寂寞得憂傷,總想把自己的聲音唱給人聽,溝通眾生,於是創造了高亢遼闊的信天游,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迴旋於肝腸,飄蕩于山野,醉人於大千,讓人虛靜澄明,生髮無盡的想象。
後來,我還聽過孫志寬、王宏偉、蘇文、楊文祥、聶雲雷、王二妮等眾多歌手的演唱,都是美的享受。閻維文對這首歌的演繹,給我的印象猶深。他的氣息像河水般起伏,他的音域如平川般寬廣,他口裡的詞還未吐出之時,那“嗨哎嗨嗨嗨嗨”的襯音,已使重重疊疊的群山鋪排到天邊。後起之秀杜朋朋是米脂人,典型的陝北窮人家出身,十五歲學藝時總是沒錢吃飯。貧窮和飢餓,結結實實地淬鍊了他。他的演唱,更使我歎服。當他唇齒間的“羊肚子手巾”一截截亮出來,顯露“三道道藍”的美麗時,陝北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到伸手可觸。其時好像人們將要睡覺,萬籟俱寂,卻有一束又長又細的柔韌的光芒,在幾里外的山巔上游走震顫。那是落山的太陽遺落下的一束光芒,一束最生動最空靈最深情的光芒,在遠遠的雲彩下久不熄滅,使每道山每條河都閃爍著金玉之輝。
宋金時期的元好問曰:“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明代的《牡丹亭》雲:“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近代的信天游說:“什麼人留下個人想人?”人們一輩輩地詰問探詢,也說不清這男女之情的霧暗雲深。這些內容被米脂後生一唱,其藝術神氣豐厚飽滿,直擊人心,令人歎服。
2019年,陝北神木的石峁遺址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的樂器口簧——我們的陝北石峁先民在新石器時代,已經用獸骨製作口簧了。口簧除了娛樂,還承擔著莊嚴的使命,他們以吹奏口簧的宗教儀式,促進子孫繁衍,其中包含的是人性最本真最原始的感情。而這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抒發的正是這種純而又純的人的自然性情。想到這裡,我的神思立馬回到了先秦時代,在那時,這首信天游對應的當然是音樂和文學,是《詩經》裡的愛情篇章,是《關雎》,是《蒹葭》。
愛情,是亙古不變的生命旋律,是男女心靈最美好的碰撞,最刻骨的糾纏。“食色,性也”,如果翻譯為通俗語言,可以是:“人生一世,食色二字。”色,或愛,佔了人性中的半壁河山。如果沒有愛情,人生將會多麼枯燥。別看農民文化程度不高,他們往往比知識分子愛得熱烈,愛得透徹。他們對情侶的稱呼真是絕了——“肉肉”“親親”“命蛋蛋”“心尖尖”。他們總有說不完的情,道不盡的愛。正如《藍花花》一歌所唱:“我見了我的情哥哥有說不完的話。”可是在《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裡,是“見個面面容易哎呀拉話話難”,因為人多眼雜;是“拉不上那話話哎呀招一招個手”,因為距離太遠;連人影也看不見了,別說拉話和招手,只能看見個如夢如幻的“村村”;想在一起拉話,但最終一句話也沒拉上,肝腸寸斷,“淚個蛋蛋拋在哎呀沙蒿蒿林”。從古迄今的無數愛情,使人愉悅使人苦。“想親親想得我心花花花亂,煮餃子我下了一鍋山藥蛋。”“東山的糜子西山的谷,哪達兒想起你哪達兒哭。”“羊肚子手巾一尺五,擰乾了眼淚再來哭。”陝北人之重情,世所罕見。
前不久,我在網上看了馮滿天、牛建黨和中國交響樂團共同演出的《信天游隨想》,其主調就是《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他們對這首歌作了大膽的舞臺呈現。百般樂器,嗩吶為王。他們用了嗩吶。陝北傳統樂器中,本無中阮,他們也用上了。由此,我看見了這首歌更多的美質。
作家柳青的同縣老鄉牛建黨,雖然是個嗩吶手,但他演唱得悲切,令人撕心裂肺。如果說此時觀眾還可強忍住淚水,那麼,他一吹響嗩吶,聲聲都撞向人們的淚點,惹人淚流滿面。接下來,馮滿天和牛建黨出人意料,突然間狂舞起來,同時邊奏邊說邊唱。他們一下子擺脫了抒情主人公的角色,開始了鬧秧歌般的娛樂;或者,他們仍是抒情主人公,但是早已花好月圓,不過是在重唱當年之歌。歌曲中潛藏的力量,瞬間成了狂風暴雨,席捲擊打著舞臺。他們的唱已不是唱了,而是吼,是喊,是跑腔走調,是瘋狂宣洩,有如米芾的醜書,縱橫揮灑,動盪搖曳,風姿萬千。由於馮滿天的恣意癲狂、忘情投入,中阮的弦,一根接一根地彈斷了——斷了也不管,繼續彈。彷彿愈偏離章法,愈離譜,愈出紕漏,愈有味道,愈趨完美。當他們的表演戛然而止,大有“容華謝盡,山河永寂”之感。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是從口簧裡吹出的聲音,是接續《關雎》《蒹葭》的聲音。它迴歸自然,迴歸本真,虛化了人物和敘事。它的抒情主人公,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它呈現出的是迷離縹緲的意象。它迴旋於人的肝腸、大地的肝腸。因此,這首歌既是唱愛情,又遠遠超出了愛情的疆域,具有深廣的內蘊。它是對美、對追求美的莊嚴禮讚。
在諸多色彩之中,陝北後生固執地愛白,陝北女子卻對紅和藍有著特殊的情感。這兒單說藍吧。藍是天的顏色、海的顏色、馬蘭花的顏色。“要穿藍,一身藍,藍襖藍襪藍布衫。”這種亮麗的藍,就常年閃耀在白生生的羊肚子手巾上,固守著生命的本真,固守著對未來的憧憬。那是有聲有韻的藍,那是充溢著靈氣的藍,那是多情的藍。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19日1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