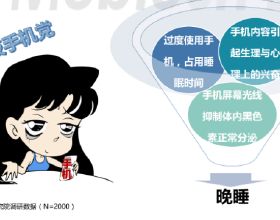儘性以至於命。
——《易經》
得之不得曰命。
——《孟子》
在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儘性而至於命,得之不得則由命,是關於命性之辨的一個人生信仰。在這一人生信仰中,有兩種“命”的思維,一是求在我而為己立命,儘性以至於命;二是求在外而無需計較,得之不得則由命。
“儘性以至於命”,是《易·說卦》的思想主張和論點。此是在踐履“天命之謂性”(《中庸》)上為己立命,安之若命,“由仁義行”。堅定這一人生信仰,就在於篤定道德之必然而行之於自然,率性而行,最終達致“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的人生境界。
得之不得由命,是《孟子》詮釋孔子人生修為的思想和主張。它要求人們正確看待成功與失敗,而不可以一味計較外在的得與不得,真正做到寵辱不驚。堅定這一人生信念,就在於把主要心思精力用在求之有道上,既要甘願捨棄不仁不義之得,又要在不能得上體驗無怨無悔的心安理得。
一、性命之辨,求在我與求在外之別
人生的命性之辨,明確的論說出自《孟子》。這一學說的出現,彰顯了對人性的深刻覺知和探究,體現了對人生的深邃反省和反思,無疑是儒家人性觀和人生觀的一個標誌性思想成果。
(一)情慾之求,有命而不謂性。
在《孟子》的命性之辨中,認為“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盡心下》)情慾之性,財富功名之求,求或不得,故言“有命”。“不謂性”,言非是欲仁而得仁的求在我之性。
聲色臭味和安逸的“五者”之慾,雖為生下來即有之情性,然有其止分而不能皆如人願,故謂之“有命”。人生存在社會之中,必然會受到社會分配的限制。“不謂性”,是不可言為“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
在宋代儒家學者朱熹看來,世人以此“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四書集註》)。世俗之人往往以生之即有為性,如《荀子》就以情慾的生之本有為性。本性趣向惡,故言性惡。執此情慾之性,必欲求之,則無復有性善之性。
情慾之性的“有命焉”,旨在揭示聲色臭味和安逸五者,於人生雖是無之則不可以生活的不可無者,然又是欲得而不必得的“得之有命”。如以此情慾為性,孜孜以求利,就必然為物慾所牽引,而流於物化上的泯滅天理。
“君子不謂性”,言君子之謂性者,是情慾有所節制當宜的性善之性。人之慾望無止境,慾壑難填,不可放任自流,而要自我節制,達致中和,“求之有道”。情慾之性,人與禽獸相同,而非為人之本質,故言“不謂性”。
(二)理義之求,有性而不謂命。
在《孟子》看來,“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仁義禮智和天道“五者”,是天命之性,為人生中的必然之理則。天命之性,也非是不需要藉由“求其放心”(《告子上》)之修為即可得者。
就這一論說的意旨,朱熹指出,世人以此“五者”為命,“一有不致,則不復用力”(《四書集註》)。不復用力,則訴諸命運。實則,這裡的“五者”在世人看來,非是生來即有,而需要外力方可以達致。如《荀子》所認為的那樣,必須要藉由外在的師教循法方可以達致其自得。
在君子之人格看來,仁義道德是天命之性,無此則不可為人,故謂之性。《孟子》言“性善”,就旨在以天命之性為性。“君子不謂命”,是說性善人人雖本來既有,非由外鑠而得,然也要藉由修持敬存方能不失。“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告子上》)性善之才本來即有,“萬物皆備於我”。若能“反身而誠”或思以操存,就會自然有得。
(三)性命之辨,所求有內有外。
在儒家思想看來,生理情慾為人的生之即有之性,應得以適當滿足,而有道的名利之求無可厚非,不可責難。只有貪私之小人,唯利是圖,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忘記自己社會倫理止分,推卸積善成德的做人責任,方要受到譴責。
在《孟子》的價值主張中,求在我而有益於得者為性,求在外而得之不得者為命。同時,認為正命為命,天命為命,故有為己立命之說。性命之辨,反映了君子、小人在性命價值內涵上的不同主張和價值定義。
在這一人性辨別中,道出了君子、小人不同的價值取捨,形成了不同的行為導向,造成了不同的效驗後果。只有理清這一性命之辨,方能在人生第一關口上便可明辨是非,毫不含糊,以至於在操則存、舍則亡上做一個明確的了斷。
君子恆以天道的賦性為命,同時認為性善是求得則得,不受外在的影響,故也謂之為性。人性之善,雖非是無需修為的自然而致者,而好像是需要外在的教化喚醒己之自覺,但喚醒只是認知問題而非是實有與否的問題。只要是人,就有性善的潛能和可能。每個人只要“反身而誠”,皆可求諸己而自得。
二、窮理盡性,為己立命而致命遂志
要達致“儘性以至於命”,就得“窮理”。“窮理”,是格物致知之事;“儘性”,是事天立命之事。求諸己而為己立命,就要先“知天”。知天命之性或己之本性,就要有“致命遂志”(《易·困卦·大象》)的實踐功夫而盡其性。
(一)格物窮理,旨在知天知命。
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中,認為“天命之謂性”(《中庸》)。性由天命,而為己之稟賦。己性由天命,則有其內在的理則。此一理則,非是受外在自然而必然決定的宿命,而是主體選擇必然而踐行自然的立命。立命先要知命,知命先要窮理,窮理又是格物致知之事。
在《中庸》看來,盡己之性,就要盡人物之性,進而參贊天地之化育。這裡,成己之功為,體現了儘性之仁;成物之作為,運用了窮理之知。朱熹認為,“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四書集註》)這裡的窮理,是窮盡天下之理。一旦豁然貫通,則是“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對人性或天命之性的探究,也可藉由察天道之功為、人生之事為,或究歷史之事蹟而致其人性之知。學聞者,不過是即物窮理的間接知識罷了。博學多聞,就旨在因已知之理而益窮其於至極。一旦豁然貫通,則天人合一、性命合一、心身合一,固是心之大用無不明。“知之至”者,就在於窮其理而知天命,知人生意義之所在。
(二)盡心知天,就是自誠而明。
求諸己而“知天”的學問,又可藉由盡心以致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盡其心”,就在擴充四端之心。既然“萬物皆備於我”,藉由“反身而誠”的“盡其心”,就可知己之性。
己之性既本自天命,則知己之性,就可以“知天”。實則,在儒家的致知和窮理上,乃是或由外以至內,藉由認知天地、萬物之性以知己之人性;或由內而至外,藉由盡心儘性以知天之所命。這一致知的不同路徑和方式,又是“自誠明”(《中庸》)和“自明誠”的路數。
基於天人合一的價值思維,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自誠而明和自明而誠的兩種致知方式,實是共存而相互促進的,二者不可偏廢。在孔孟一派的歷史文獻中,無不呈現這種雙向並行而互促的認知模式。
在《孟子》中,既有言惻隱、羞惡、辭讓和是非之心為人人皆有,“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公孫丑上》);又有言“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離婁上》)。與“思誠”的“反身而誠”不同,天道之誠乃是自在之為。人若修其“天爵”(《告子上》),就是盡天命之性。
(三)事天立命,就在致命遂志。
“儘性以至於命”的價值思想,又是“事天”的“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人不能為己立命篤定,則“率性之謂道”就有或失的可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有“惟精惟一”,方能不失其道而夭壽不貳。
人生的“事天”修為,固然需要“存其心,養其性”(《孟子·盡心上》)之工夫,更需要“立命”的“夭壽不貳,脩身以俟”。“存其心,養其性”,只是“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的全其天之所付事,而“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乃是顯諸外而篤行不已之事。“夭壽不貳”,則分定;“修身以俟”,則無間。
事天立命之事,乃在於致命以遂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盡心下》)“俟命”,既是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的德之純,又是不論得志或不得志而循道的純而不已。“俟命”,則“守死善道”(《論語·泰伯》),而致命遂志。致命是盡其性命,遂志是成就善道之志。
猶如“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文子·上德》)一樣,聖人是“畜道待時”以為成仁成聖。先為於“畜道”,是求諸己而求在我者的道德自得;後以為“待時”,是面臨機遇與不遇之時而採取不同的行為。或以義衛身,或以身衛義,時措其宜而已。
三、求之有道,得之不得而順受其正
為己立命,是必欲得之,不得則不輟其為。儘性而自得,不如此則不能算是盡其心,盡其力。得之在命,是求之有道,得之不得由命。孔子之所以罕言命,就在於既不能得則不必在意求。有道以得之,則必求其得;無道以得之,則雖得不求。
(一)順受其正,盡其正命。
人生所求,若是“求之有道”,則必是“順受其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子·盡心上》)“順受其正”,既是為己立命而正命的“盡其道而死者”,又是“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和非因桎梏而死。“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和“捨生以取義”(《孟子·告子上》),皆是正命而死者。求之有道,就會不入死地,而規避桎梏之死。
人生有時是命不該得,就不得妄意以求。否則,就會遭受非正命之患。“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以道殉身”,是時逢“天下有道”之境遇;“以身殉道”,是遇“天下無道”之情境。二者,皆是“順受其正”。
在富貴之達上,適值有道之世,是求之有道則可得;遭遇無道之世,是無道可得則不求其得。“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文子·符言》)既有“求之有道,得之在命”的道德堅守,就能有“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的心境自然。
(二)君子所性,性命分定。
立命,則儘性以至於命。君子以為命者,乃是命定的求在我者,求諸己而自得,非是求在外的必得。君子所性者,乃在於“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盡心上》)的“分定”。有此性命的“分定”,就既能“大行不加”,又能“窮居不損”。
盡其性命之分定,則必是雖欲“廣土眾民”,然得之而不為樂;雖樂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然得之而非為性分自得之樂。“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說苑·談叢》)“死而不悔”,就在堅守“所性”而能“夭壽不貳”。“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的分定,也在於此。
孔子之為聖人,就在於能夠“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說苑·至公》)。得志於行道,則入仕而致用;反之,處以獨善其身。人若能立命以儘性,則得志時必是求有道而無不得,當其時而無不成。
(三)得之不得,付之由命。
得之不得的“有命”,非是宿命論,而是安之若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萬章上》)“進以禮,退以義”,則無非自得;“得之不得”,則以其“有命”而淡然處之。
人生既然要堅守“求之有道”的原則,見利、見得而思義,則必有不欲得者。既是不欲得的不必得,則不必曰“有命”。只是那該得而受客觀原因不能得者,方可謂之“有命”。
人生固是事事不能皆如人願,但不如意者必有其因由,不可歸之於宿命。宿命者無可奈何,而“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盡人事而聽天命的價值意旨。雖不能如人所願,但盡了力就會於心無愧。
君子修諸己,而不求諸外。“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荀子·非十二子》)。人能修為其可貴、可信、可用之品德和才能,然不能使人必貴己、信己、用己,而得其所貴、所信、所用。雖有不得其得的失落,但我已然盡我之能為則無有抱憾。
盡己性命,又付之由命,還體現為當理而不避死難的價值意旨。“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呂氏春秋·士節》)有此“視死如歸”之心志,豈可在乎功名利祿上得之不得的“有命”?
既然“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為非,而未必免於禍”(《文子·符言》),則必於“得之在命”上心安理得。人之習情,見不必得之“有命”常是患得患失,“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老子》)。“貴大患若身”,患得患失,必然是“寵辱若驚”。若能道德自得而無身外之妄求,就必能寵辱不驚。
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滄桑而綿延不絕,已充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迎接各種挑戰的開拓能力。這一文化內涵,既本自“學·思·觀”的探求真理而來,又呈現著“學·思·觀”的理性自覺和開放思維。讓我們齊心協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時代洪流之中,為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冷靜的思考,清醒的應對,果敢的鬥爭,無愧的付出。堅信“文化自信”,踐行“文化自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歡迎評論交流探討。文中圖片來自網路,感謝版權原作者。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