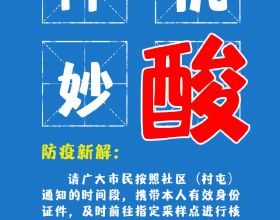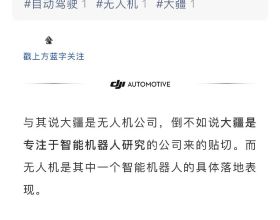我們知道,清末民初,翻譯家林紓用文言翻譯了一大批西方小說,成為那時許多中國人瞭解西方文學的啟蒙讀物。其中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在翻譯時,譯者並沒有完全忠實於原文,有一些地方甚至對原文進行了較大的增改。
這些小說也給少年時的錢鍾書打開了窺見西方文學廣闊世界的窗戶,給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在多年後進行學術研究時,他對比了原文和譯文,認為譯文中有的增改雖然不符合原文,但是為譯文增色不少,起到了“抗腐”的作用。這些帶有個人特色的改寫,在客觀上激發了更多本國讀者的閱讀興趣。
其實,在中國現代文學對外傳播過程中,也有這樣的“訛”化的翻譯。譯者沒有嚴格遵守翻譯的忠實原則,但譯作在傳播效果上卻頗為成功。老舍的名著《駱駝祥子》在美國的傳播即是一例。翻譯者對作品進行了“創造性改譯”。鉤沉這段歷史,對我們今天理解翻譯的複雜性,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不無裨益。
長篇小說《駱駝祥子》最初於1936年9月開始在《宇宙風》上連載,直至1937年10月整部小說連載完畢。這是老舍多年觀察城市底層勞動人民生活,並花費半年多時間收集材料,閉門專心寫作一年多的成果。
1945年,《駱駝祥子》的首部英譯本Rickshaw Boy在美國紐約出版。當地文學評論家馬上在《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芝加哥論壇報》《華盛頓郵報》《大西洋月刊》等報刊對這部作品進行推薦,受到大量美國讀者喜愛。這不僅與老舍精湛的語言藝術、作品中對當時北平風俗的精準描繪息息相關,也與譯者伊萬·金的翻譯和改編策略有著極大關聯。
伊萬·金將當時美國的一些本土文化元素融入了《駱駝祥子》中。在翻譯過程中,他甚至增加了角色,刪改了人物對話,更改了故事主線與結局,增添了二戰後美國積極倡導的某些精神文化在譯本中的比重。在伊萬·金譯本的重要推介雜誌《每月一書俱樂部新聞》的推薦語中有這樣的評價:
“檢驗一部小說是否成功的最終標準,是它能否引起我們共情。”E·M·福斯特(英國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說。只要你還生活著,你極可能會被這部小說的主角深深打動。他為了最卑微的幸福所作的努力,將使敏感的讀者流下同情的淚水。命運無法打敗他,人善的本性在他身上呈現並最終大獲全勝……我們五位評委一致認為《駱駝祥子》——一位迄今為止不為美國公眾所知的中國作家的作品——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小說之一。
這表明,伊萬·金的譯本中主人公的情感、人生觀與世俗觀念,都能夠與美國社會當時所提倡或流行的精神相暗合,讓大洋彼岸的讀者對主人公產生共情。翻譯時,伊萬·金選擇將原著中祥子發現小福子上吊自盡而走向徹底墮落的結局,改編成了祥子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小福子,兩人一同離開並找尋到自由的“大團圓”結局。
如此,伊萬·金透過對典型人物——祥子圓滿事蹟的講述,向美國讀者傳達了在困境下仍保持著強烈進取意志的中國民眾的戰時精神,展現了中國作家充滿人文主義溫度的筆觸。這為當時美國戰後大量身處貧困境地的人們給予了有效的精神鼓舞。
伊萬·金譯本在美國20世紀40年代大獲成功,這種成功同時伴隨著譯著對原著語言及文化習慣的背叛。但這種缺失並不是永久的。Rickshaw Boy中被刪改去的內容和語言風格,在《駱駝祥子》後續出版的英譯本中逐漸補足。
1979年、1981年及2010年,美國分別出版了珍·詹姆斯、施曉菁和葛浩文譯者的譯本,從詹姆斯譯本開始,翻譯風格逐漸放棄了對美國主流觀念的迎合。從葛浩文的譯文中可以清晰看到,譯本能夠貼近原著表達的中國文化特色及精神內涵。這四部《駱駝祥子》英譯作品在時間上橫跨了六十餘年。顯然,這樣的持續性外譯的過程和效果值得我們重視。最早的譯本降低了外國讀者瞭解作品的門檻,引發了他們的閱讀興趣。後續的譯本則逐漸提高了難度,讓外國讀者能夠逐漸走進中國文化的精神世界。
這種先佔據文學市場,再逐步滲透的持續性過程,為呈現立體的、多角度的中國文學文化打下了基礎。當我們將跨文化傳播的獨特性,與中國文學的文字內涵十分複雜的特點納入考量時,可以看到,在翻譯過程中,單個譯本難以兼顧讀者接受與對文字內隱含的所有精神核心、文化特點、意境呈現進行完整把握,而這樣持續性的外譯過程,恰恰能夠對此進行補足。因此,我們今天在傳播中國文化、講述中國故事時,也不妨將其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考慮。重點各異的譯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可以發揮其不同的作用,將其疊加起來,則可以呈現一個更為豐富完整的文字世界。
伊萬·金所翻譯的《駱駝祥子》的成功,為這部中國現代名著後續在美國、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翻譯和接受打下了基礎。法語、德語、日語等國家出版的《駱駝祥子》譯本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參考了英譯本。可以說,中國現代經典小說《駱駝祥子》的對外譯介之路,是中國現代文學走出去過程中的一種磨合正規化,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而不同時期的譯本所強調、凸顯的文化“共振”,及與不同時代讀者的精神“共情”,恰好是我國文學漸漸在世界文化之林中重塑文化標誌過程的寫照。從這個意義上看,對於外國《駱駝祥子》讀者的接受研究,不僅對文學作品翻譯研究有參考價值,對中國文學整體面貌的對外構建都具有研究價值。
(作者:馬宇晴,系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李宗剛,系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