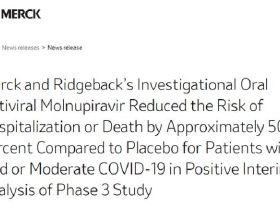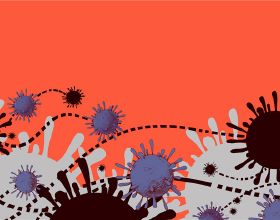人們常稱《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的第一部兵書,嚴格地說,這個描述是不正確的,在《孫子兵法》面世之前,古代中國已有兵書,而且還不止一部。但是,這些兵書典籍,由於思想相對淺薄,內容多已過時,尤其是文字不夠優雅,大浪淘沙,在歷史的長河中,已經散佚殆盡了,而《孫子兵法》則是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第一部系統完整的兵書。明代茅元儀說:“前孫子者,孫子不遺。”意謂《孫子兵法》之前兵書中的精華部分,已為孫子所擷取吸收,沒有任何的遺漏。這也表明,《孫子兵法》的兵學成就乃是在傳承前人兵學思想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而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考察前《孫子》時代的兵學文化,我們不能不迴歸“古司馬兵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指出:“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顯而易見,“古司馬兵法”才是中國古代兵學的總源頭,是兵家文化最早的系統載體。西周時期,文獻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當時的兵學典籍由官方統一編纂,專職傳授。這類文獻泛稱為“司馬兵法”,也即司馬之官治軍用兵法典法令的總稱,作為類名,它不是某部軍事典籍的專指。先秦時期一切官方軍事文書(法規、條令、條例)都屬於“古司馬兵法”的組成部分,像《左傳》所徵引的《軍志》、《孫子兵法》所徵引的《軍政》,則為“古司馬兵法”類別下的兵學專著。在兩漢時期,人們還能看到其中一部分零散材料,併為它所包含的軍事理論原則、陣法戰法要領、訓練編制綱目之豐富和深刻而讚歎不已:“餘讀《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今本《司馬法》,當為“古司馬兵法”相關軍事思想的彙集輯要。“古司馬兵法”最顯著的特徵是集中體現了西周禮樂文明中的“軍禮”傳統,即所謂的“競於道德”。用漢代班固的話說,就是:“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漢書·藝文志》)
這反映在戰爭宗旨上是強調規則意識、底線意識,“爭義不爭利”。如不得已動用戰爭這個最後手段,也必須遵循一定的道德倫理原則,光明正大、公平合理進行交鋒,即所謂“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強調“弔民伐罪”“征討不義”,行所謂的“九伐之法”:“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參見《周禮·夏官·大司馬》《司馬法·仁本》)並且將這原則提升到“仁義”的高度來予以肯定:“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發動戰爭,多有道德上的禁忌,這包括不能夠乘人之危,不允許違農時,讓民眾遭受苦難,不能夠在嚴冬或酷暑這樣的季節興師打仗,等等:“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
在具體的戰場交鋒過程中,必須尊重對手,奉行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原則,進退有節制,廝殺講禮儀,杜絕詭詐狡譎的行為,擯棄唯利是圖的做法:“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義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司馬法·仁本》)同書《天子之義》篇,也有相似的主張:“古者,逐奔不遠,縱緩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逾列……遲速不過誡命。”而《榖梁傳·隱公五年》則簡潔概括為:“伐不逾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同時,禁止在戰場交鋒時實施偷襲一類的陰損毒招,如《司馬法》逸文就強調:“無干車,無自後射。”(《周禮·士師》鄭玄注引)即不準冒犯敵國國君乘的車,也不允許從背後攻擊敵人。《左傳·文公十二年》亦云:“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四年》)
戰場紀律要體現一定的人文關懷,優待俘虜,救死扶傷,禁止報復是執行戰場紀律中的必有之義:“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司馬法·仁本》)
在戰爭善後問題上,勝利一方對敵手也不許趕盡殺絕,除惡務盡,而是在確保勝利的前提下,保留對手的生存機會,讓其維繫自己的血胤:“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司馬法·仁本》)武王伐紂成功後,乃冊立紂王之子武庚,繼續奉殷商之血祀,就是例子。周公東征平息武庚與“三監”之亂後,還是要借重紂王庶兄微子,封建為諸侯,國號宋,以繼續保持殷商的血胤相傳。宋國的情況不是個案,鄭莊公復許,楚國恢復陳、蔡兩國的獨立,皆相類似。參之以《左傳》,信而有徵。如魯昭公十三年(前529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大子吳歸於陳,禮也”。
“古司馬法”這種“競於道德”的屬性,決定了宋襄公那種後人眼中的“蠢豬式的仁義”會受到推崇,甚至誇張到“文王之戰”的地步:《公羊傳》言:“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公羊傳·僖公四年》)司馬遷也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中同出一轍的讚賞宋襄公:“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宋襄之有禮讓也。”
當然,對“古司馬兵法”的“競於道德”的屬性,我們也不能作過度的誇大。這種現象的存在,首先是由戰爭本身物質條件所決定的,是受到現實的制約,而非出於道德的高尚追求。例如《易·師卦》“六四”雲:“師左次,無咎。”這是合乎作戰實踐規律的單兵戰術動作而已。其原始含義為:在戰場上,位於左側或駐紮在左方,則安全。道理很簡單,手的功能,一般人都是右手為主,左手為輔,左撇子畢竟是少數,在冷兵器時代,士兵通常左手執盾用以防守,右手執刃用於攻擊。因此,當與敵生死相搏,尤其是狹路相逢時,很自然應該靠近左側,迫敵位於自己的右側,便於右手執刃加以擊殺。很顯然,“師左次,無咎”這一原則的提出,完全是古代士兵對具體作戰經驗自覺或不自覺運用的理論總結與昇華。同樣的道理,在殷商、西周與春秋前期密集大方陣作戰背景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的戰法,決定了戰場行動只能是“逐奔不遠,縱綏不及”“徒不趨,車不馳”,只能是“成列而鼓”。其被賦予道德要素,應該屬於後人有意識的粉飾與附會。
其實,當時戰爭的殘酷才是歷史的最大真實,《禹鼎》有言:“無遺壽幼”,無論是白髮蒼蒼的老者,還是咿呀學語的幼童,均是屠戮殘殺的物件。而周公東征中的“踐奄”之舉,也同樣揭示了其殘酷慘烈的特徵,“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尚書大傳·成王政》)
可見“古司馬兵法”所體現的“軍禮”精神,只適用於中原諸夏列國,而不包括蠻夷。這就是所謂的“德以柔中國”。與之相反,那些四夷少數部族則不屬於“軍禮”的適用物件,故言“刑以威四夷”(《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左傳·昭公元年》)是役,晉國在夷狄擺好陣勢之前就攻打,大敗夷狄。“未陳而薄之”,這顯然有違軍禮“成列而鼓”的原則。
即使在中原諸夏列國,是否遵循“古司馬兵法”所倡導的“軍禮”原則,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在戰場上“傷國君有刑”是“軍禮”的準則之一,晉楚鄢陵之戰中,郤至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固然恪守了“軍禮”,但是,同為晉軍將領的呂錡卻汲汲於殺傷敵國國君為務,“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佔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左傳·成公十六年》)
不僅如此,在同一個人身上,他對“軍禮”的遵循也往往帶有選擇性,表現經常前後不一、判若兩人。如郤至其人,他在鄢陵之戰的戰場交鋒時固然對鄭伯、楚子等敵國國君竭盡恭敬尊重之能事。可是,在鄢陵之戰開戰前夕的戰略建言裡,卻是主張乘楚國還沒有擺好陣勢就攻打,這明顯違背了“無薄人於險”的“軍禮”要求。
理想與現實,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脫節與剝離的,兵學觀念是一回事,戰爭實踐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不能簡單地畫等號。“古司馬兵法”所倡導的軍禮原則,歸根到底,只是一種道德上的訴求,並非強制性的法則。因此,我們對“古司馬兵法”中“競於道德”的屬性,應該有辯證的認識,既不宜作輕易地否定,也不可讓後儒們牽著鼻子走,一味地加以信從。
(作者:黃樸民,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