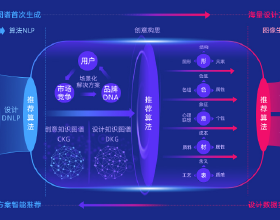我終是過不大慣街裡的生活。最近食不甘味,心裡空落落的,尋思著吃點什麼好呢?
白菜燉豆腐?白菜還好,鮮嫩翠綠的樣子;豆腐就差得遠了,顏色暗黃,像一個年老憔悴的老婆子。入口就覺著不好了,豆腐發硬不曾燉透,沒有又嫩又滑的口感不說,也沒有與白菜充分融合後的清香味道。自是落了筷子,不好吃!
酸菜燉大鵝?一落雪,這可是一道大菜,在東北。我想得倒是好,可看著那馬勺小小的,就犯難了——這,半棵酸菜切不上都,更放不上幾塊鵝肉了。何況,笨鵝肉質緊緻不易熟,用馬勺燉,那得猴年能吃上飯;用高壓鍋燉鵝,然後再加入酸菜用馬勺燉,然肉與酸菜燉得時間短融合不充分,味道就出不來!倘若想要吃得痛快,那就得到類似於“鐵鍋燉”“柴火燉菜”“農家樂”這樣的飯館去,麻煩不說還很貴很貴的,要緊的是味道不正宗。吃得不盡興!
“好吃不如餃子”,在北方過節了、來客了、出遠門了……總是要包頓餃子的。我家海力就怪呢,天天吃餃子也不嫌膩煩。於我們這般年紀的人而言,吃飯還是自己做的好。在家裡包餃子,剁餡是個問題——總是怕吵到鄰居。街里人起得晚,早晨往往不吃飯的,尤其是雙休日起無定時。人家美夢酣甜,這壁廂要是“叮哐叮哐”來一陣響動,那是要多煩有多煩呢。你瞧瞧,這飯吃得小心翼翼,伸不開手腳,其中再夾雜著些許埋怨之聲,著實不爽快。
前幾日,海力閒了,說回鄉下。我說,好。
趕得巧,村裡人殺豬,豬是自家養的。昔前,到了年下才會殺豬,而今入冬便陸續殺豬了。殺豬時,左鄰右舍親朋好友,會應邀前來吃“殺豬菜”,盡歡才去。
看吧,一會子功夫,小院子裡便熱鬧起來了。騰騰熱氣中,男人們在屋前拾掇豬,女人們在廚房忙著做“殺豬菜”。嫂子、嬸子們洗碗碟,切酸菜,灌血腸……她們嫌我躡手躡腳不行事,所以給我派個好活——添看柴火。
木頭已經劈成絆子整齊地摞在西側牆根之下,上面落了層薄雪,並不妨事。木頭絆子架在灶下燃起乎乎的火苗,不時發出“咔咔”地脆響,那才是“旺柴”呢,聽著溫暖而吉祥。
嫂子嬸子們說話響快,幹活也麻利。她們嘰嘰嘎嘎說笑著,手裡的活計也不曾耽誤半分。鍋裡添上半鍋水,下入大塊五花肉、骨頭和“燈籠掛”(全套下水)。水沸,撇出浮沫。再放入蔥、姜、蒜、大料瓣及酸菜、血腸,大火燉。二十來分鐘後,把血腸先撈出,否則老了吃著發硬。其餘食材繼續燉個把時辰,撈出五花肉、骨頭、“燈籠掛”,改刀後,把大片五花肉、拆骨肉、血腸片、肝片等鋪在酸菜上慢火再燉一會兒。
很快,殺豬菜上桌了。人多,東西屋都擺了桌子。大傢伙在火炕上盤腿圍桌而坐,沒有過多的客套,伸筷夾肉,蘸上蒜醬,香!一種清純的肉香,一點不膩,連菜面上的油花都是清亮亮的。我和海力只顧埋頭吃飯的樣子,讓大夥好頓嘲笑:
“看看這兩個人,在街裡可是餓了幾天了?”
“是不是還是家好?”
“別光吃菜,來來來,喝碗酒……”
說著,七叔把一碗紅高粱遞過來了。“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多麼痛快!可惜他得開車。大夥也不拼他,讓我們隨意。
幾碗白酒下肚,男人們的話就多了起來,起初彼此談論著今年的糧食價格,謀劃著來年承包多少畝地,買什麼樣的種子;後來,就天南海北地侃上了,東西屋相互應和著。女人們哪裡攔得住呢,隨他們去吧,都是自家人。
“一過山海關,都是趙本山”呵呵,這話是有些道理的。我和海力吃得安逸了,斜靠在牆上,眯著眼睛瞧著他們淳樸的臉上洋溢著燦爛的笑容,推杯換盞中沒忘了侃大山。他們說的俏皮話也是有些個意思,聽著心裡很是舒坦。這樣的時光是很好的。
天近傍晚了,我們不得不走了。大夥給拿了許多東西:豬肉、酸菜、白菜、蘿蔔、粘豆包、各種凍菜……塞了滿滿一後備箱,不拿不讓。臨了,囑咐:
“想吃啥,吱一聲,我們擱車捎去。”
回到街裡,望著那些菜,尋思著:鄉下的食材簡單,多半是自家種的,洗淨往大鍋裡一放,除了蔥薑蒜其餘調料很少放入,主要是大火燉。怪著呢,吃著就是香,是菜的本味。哪怕是灶下燒熟的土豆亦是異常的好吃……
怪著呢,街裡就做不出那樣的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