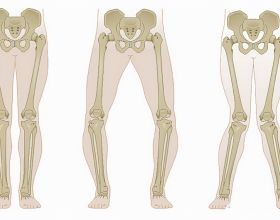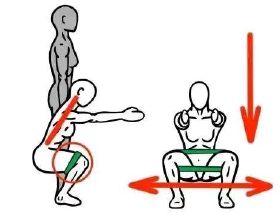《沙漠與餐桌》,[美]羅伯特·N.斯賓格勒三世著,陳陽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版。
15世紀,歐洲人的餐桌上有什麼?
隨著15世紀東亞香料的價格在西歐一路飛漲,為尋求黑胡椒和肉豆蔻而踏上旅程的富有進取精神的歐洲航海家駛向了未知的水域。受到葡萄牙國王“幸運兒”曼努埃爾一世的委託,瓦斯科·達·伽馬與兄弟保羅在1497年率領由4艘船組成的艦隊啟航,繞過好望角,穿越印度洋,最終到達卡利卡特。達·伽馬的航行與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旅程一樣,徹底改變了全球交流的本質。關於地理大發現之文化影響的研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亞洲的食材和香料引進到新世界之前,歐洲人的餐桌究竟是什麼樣的?
義大利美食似乎是歐洲特色飲食的集大成者,然而,義大利飲食的許多核心食材直到近代才傳入地中海地區。番茄在大約3000年前的南美洲被馴化,後來被西班牙探險家當作稀罕物帶到歐洲,又經過好幾個世紀才成為受大眾歡迎的食物。義大利麵以及在磚砌烤爐中烤制的比薩餅底,可能都是由中世紀的商人從阿拉伯世界帶入義大利的。將亞洲大部分地區用烤爐或饢坑烤出的薄面餅稍做改動,塗上黃油、香草和醬料,便成了比薩餅底。只需再加一些碾碎的番茄,義大利人便創造出了本國的代表菜品。與比薩類似,麵條也是在約1000年前跟隨阿拉伯商人傳入地中海地區的,它很可能起源於東亞。中世紀晚期或文藝復興初期的義大利人接觸到麵條之後,很快便將其納入自己的特色飲食中,後來也在麵條上點綴碾碎的番茄。
另一種義大利主食波倫塔只是對新石器時代以來歐洲普遍食用的穀物粥略加改動而已。不過,今天的波倫塔基本都以玉米為主要原料,而玉米是在墨西哥被馴化的農作物。義大利糰子(gnocchi)則對我們熟悉的餃子進行了有趣的改造。今天,義大利糰子基本都用馬鈴薯——也就是土豆——烹製而成,而馬鈴薯是在安第斯山脈高處被馴化的根莖類作物。就連義大利美食中用來調味的紅辣椒和提拉米蘇中的巧克力也是從新世界引進的物種,辣椒早在約6000年前便在墨西哥被人類馴化,而巧克力則發源於公元前二千紀便存在於中美洲的一種不加糖的飲料。
有些義大利人或許難以接受這一理念:他們的大多數特色飲食都是在殖民時代而不是古羅馬的宴席上發展而成的。不僅如此,另一個更令人驚訝的事實是,現代義大利的釀酒葡萄並非出自有數百年曆史的義大利葡萄藤,而是生長在從北美進口的砧木上。19世紀中葉席捲歐洲的“葡萄大瘟疫”摧毀了大多數歐洲國家的葡萄園,法國遭受的打擊最為沉重。這場葡萄病害的始作俑者可能是葡萄根瘤蚜,這種蚜蟲(很可能是學名Daktulosphaira vitifoliae的品種)摧毀了葡萄藤的根系。歐洲葡萄酒產業在20年裡幾乎完全停滯,直到兩位法國植物學家發現,將藤蔓嫁接到完全不同的北美葡萄品種砧木上(最初選用的是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夏葡萄的根)能夠提高植物對病害的免疫力。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歐洲葡萄園逐漸開始栽種嫁接到北美抗病砧木上的葡萄藤,慢慢恢復了生機;這樣說來,歐洲出產的所有葡萄酒都應該感謝得州葡萄。

1865年到1872年的錫爾河一帶,雙峰駝商隊載著商品前往市場,攝影師不詳,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圖片與攝影部,出版社供圖。
絲綢之路對各國美食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現代很多地方特色飲食中,外來食物都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沙俄帝國為中亞帶來了許多新式菜餚,比如蔬菜湯和羅宋湯,還有俄羅斯餡餅和薄煎餅。就連當今許多中亞菜餚的主要食材——稻米——在當地紮根的歷史也不過區區1500年或者更短。
《沙漠與餐桌》關注的重點是全球化如何影響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個文化的發展,以及今天全球化如何持續改變著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尼科洛、馬費奧和馬可·波羅的遠行,以及數以千計名不見經傳的祆教祭司、粟特人、波斯人、回鶻人、古吉拉特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旅程,都對當代人的食物清單產生了影響。當這些旅人途徑亞歷山大港、巴格達、貝魯特、布哈拉、君士坦丁堡、大馬士革,卡菲爾卡拉、麥加、馬斯喀特、片吉肯特、泉州、撒馬爾罕、塞薩洛尼基、吐魯番、烏蘭巴托和西安等城市時,他們一路撿拾起各種從未見過的植物和不同品種的農作物,最終將它們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一位作家曾寫道:“將我們稱為食用植物的僕人並不算誇大其詞,人類勤勤懇懇地將它們送往世界各地,像奴隸一樣在精心打理的果園和田地裡照料它們。將這些人類活動稱為種子的傳播,這完全不是誇大其詞。”
趕著大篷車的商隊和香料商販走遍四海,他們通常會說多種語言,具備久經磨鍊的社交技巧;他們善於開發新市場,將生意拓展到全球各地,而且擅長結交新的盟友。他們駕駛的大篷車不僅穿越了沙漠,還跨越了政治的壁壘。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攜帶各種傳奇植物的祖先一路同行,這些植物最終演化成了無可比擬的大馬士革杏、大名鼎鼎的哈密瓜和撒馬爾罕的金桃。史前中亞人還曾在阿拉木圖種植適合做蜜餞的小蘋果,在阿什哈巴德和撒馬爾罕栽種碩大多汁的甜瓜,在吐魯番培植外皮呈鮮黃色、能釀出甘美紅酒和製成深紫色葡萄乾的葡萄品種。
如今,東亞廚房的烹飪魔法也是數千年來各種異域食材——尤其是香料——透過貿易輸入當地的結果。吳芳思創作了數本關於絲綢之路的著作,她是一位頗受歡迎的作家,曾擔任大英圖書館中文部的負責人。她指出:“除了動物園裡的動物和奢侈品,食品便是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進口商品,因為它們大大拓展了中國特色飲食的潛力。”她還說:“可能讓很多中國廚師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的某些基本原料最初都是進口產品。芝麻、豌豆、洋蔥、芫荽以及黃瓜都是在漢代從西方傳入中國的。”
絲綢之路為世界各地的廚房帶來了新穎的食材,但它對人類歷史和農業還有更為深刻的影響。在各種農作物透過內亞進行早期遷移的過程中,隨之一同傳播的意義重大的創新之一便是農作物的輪作制度。在幼發拉底河上游伊斯蘭古代村落髮現的古代植物遺存年代在8世紀至13世紀,一位植物考古學家基於這些遺存指出,當時的農民已採用複雜的輪作制度。冬季作物包括二稜和六稜皮大麥、易脫粒小麥和有穎殼的小麥、黑麥、兵豆、豌豆、鷹嘴豆和蠶豆。夏季作物則有棉花、水稻、芝麻、黍和粟。這位學者還鑑定出一些果樹和葡萄植株,以及少量蔬菜和香草。
歷史文獻表明,在俄羅斯擴張之前,中亞已確立了複雜的農作物輪作制度。在1821年和1822年,探險家詹姆斯·弗雷澤在經由費爾干納重走絲綢之路時便注意到當地實行輪作制,而且指出這種輪作制與澤拉夫尚地區的耕作方式十分相似。他記錄了冬季作物和夏季作物相互替代,同時與果園和棉花田混合的情況。他還指出,在海拔更高的地帶,水果多種植在山麓丘陵,同樣的種植情況還有杏樹、胡桃樹和開心果樹。1873年,尤金·斯凱勒在穿越費爾干納和澤拉夫尚時,記載了當地冬小麥、大麥和玉米三年輪作、一年休耕,夏季種植水稻、高粱、棉花、亞麻和各類蔬菜的做法。

絲綢之路上的額弗剌昔牙卜古城遺址遠眺的景象,這座古城坐落在貿易路線的核心地帶,在公園一千紀中期便存在,後於1220年被蒙古騎兵摧毀,羅伯特·N.斯賓格勒三世攝影,出版社供圖。
在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中,冬天是農戶休養生息的時期,因為農作物不生長。這為進行手工藝品生產和發展社會紐帶等活動留出了時間。但是,經濟和人口壓力逐漸導致冬季和夏季作物輪流播種,從而促進了生產能力的提高。此外,灌溉工程的建設提高了土地的生產力,但也需要大量額外的人力。
向乾旱地區引入耐旱、生長迅速的夏季作物同樣引發了類似的程序。小麥向東亞的傳播、黍向西亞和歐洲的傳播,加之集中灌溉專案的建設,這些永遠改變了人類的歷史。正如內奧米·米勒及其同事所指出的,隨著大約2500年前灌溉系統的發展逐漸成熟,黍在西亞的重要性也日漸提高。有了灌溉,已經完成冬小麥收穫的田地裡便可以種植粟米。同樣,這種輪作制度也對土壤和農民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與之類似,小麥在公元前三千紀後期傳入中國,隨著漢代官府管理的大型水壩和灌溉專案建設而成為主要的冬季作物。同樣在漢代,有犁壁的犁投入使用,鑄鐵犁鏵首次實現大規模生產。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早在漢代以前便已有犁的存在,而且有可能是從西南亞經過中亞傳入的。自漢代之後,小麥便與夏季水稻搭配實行輪作。複種輪作的增加以及從中亞傳入的磨粉新技術可能是唐代小麥的普及程度提高的原因,尤其它可製作餃子、油餅和麵條。生活在唐代城市的中亞人烤制的燒餅就像縮小版的饢(中亞地區至今還在烤制這種叫作饢的薄面餅)。發酵乳製品在這一時期也越來越流行。
北宋(960—1126)滅亡時,集約型農業在中國達到了頂峰,南遷的難民將種植小麥的經驗也帶到了南方。此外,南宋(1127—1279)僅根據秋天的收成收取賦稅或地租;換言之,農民在春季或初夏的收成無須繳納賦稅。生長迅速的水稻品種傳播至南方,使偏遠的南方一年可以種植兩輪水稻。在中國西部的某些地區,大麥成了與蕎麥搭配輪作的冬季作物。
農業生產能力的提高是一把雙刃劍。第一代實行輪作的農民或許從中獲利頗豐,但輪作的長期影響是:糧食富餘而導致人口增加;糧食的價值下降(農民需要擴大收穫才能養家餬口);土壤肥力迅速耗盡。由此可見,農作物輪作帶來了生產能力的極大提高和糧食的過剩,最終使農民的負擔更加繁重,生活更受壓迫,環境也日益惡化。
與此同時,更加豐富的食物讓一部分人口從田間勞動中解放出來。空閒時間的增加讓人們得以專注於手工業生產或教育研究,從而使亞洲和歐洲都迎來了藝術與創新的黃金時代。過剩的糧食往往也會投入軍隊建設之中,這是整個舊世界實現農業密集化的結果。軍事化不可避免地擴大了衝突範圍,因為維持龐大常備軍的國家不可能不使用這支軍隊。就連強大國度的軍事力量也體現了以中亞為跳板的早期植物交流模式:羅馬軍隊以未發酵的粟米麵包和粟米稀飯為食,可汗麾下的蒙古鐵騎則以小麥麵粉製成的餃子為食。
絲綢之路不僅是一系列地理線路的集合,
也是歐亞大陸社會聯絡日益密切的發展過程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學界對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圍繞其對東亞、南亞和地中海的帝國及商業中心產生的影響展開。然而,隨著中亞地區科學考察活動的增加,如今學者們對絲綢之路本身的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進行了更加細緻的研究。隨著新考古方法的應用和多學科聯合發掘的開展,將中亞先民視為古代世界邊緣群體的老觀念已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淘汰。過去人們認為草原遊牧民族都是悍勇的戰士,在慶典上用敵人頭骨製成的酒杯豪飲(參見希羅多德的記載),這種印象現已被更加深入細膩的認知所取代。斯基泰文化、塞卡文化、烏孫文化和匈奴文化由一系列奉行混合經濟策略的人群融合而成,他們既放牧綿羊也放牧山羊,搭配種植好幾種不同的農作物。史書中斯基泰騎手穿越綿延數千公里的空曠草原的形象逐漸被取代,人們意識到,這些先民形成了由小型遊牧家庭構成的廣泛的社會網。
數千年來,這些長滿綠草的緩坡是駱駝商隊和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的食物來源;冰川融水匯成的河川流過水田和果園,中亞的野生林地出產各種水果、堅果和野味。進入20世紀後,這些樹林在經濟中仍持續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阿勒泰至帕米爾一帶。在中亞南部以及澤拉夫尚和費爾干納的河谷中,生長緩慢的灌木林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草原植被取代,儘管如此,植物考古學資料以及曾經生長在樹林中的樹木的馴化形態依然能夠體現這些灌木林的重要性,例如開心果樹、杏樹、沙棗樹、山楂樹和櫻桃樹等。在6000年的歷史中,人類一直在影響該地區的樹木品種和森林植被的構成。餐桌上的蘋果派和酥皮黃桃派不僅是絲綢之路貿易的結晶,也凝聚著整個內亞人類定居的歷史。
一位商販在烏茲別克布哈拉郊外的市場上兜售商品,羅伯特·N.斯賓格勒三世攝影,出版社供圖。
雖然一些歷史學家、古典學者、漢學家和考古學家仍然支援絲綢之路發源於公元前2世紀的觀點,但考古資料顯示,絲綢之路沿線的互易和互動似乎在此之前很久——公元前三千紀末——便已初現端倪。早期的交流模式看起來更像是自然的擴散而不是有組織的互動,但那仍然是絲綢之路貿易文化現象的一部分。理解中亞如何形成有組織的交流路線的關鍵在於從公元前四千紀開始專為向薩拉子目等高海拔礦業城鎮供應貨物的路線和方法。在公元前一千紀結束時,在政府靠稅收建立的軍事要塞的保護下,貿易商已經擁有相對成熟的、在中亞各地運送貨物的線路。
公元前一千紀,整個內亞發生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變化,結果是形成了尼科萊·克拉丁(Nikolay Kradin)口中的“複雜的牧業社會”,同時也導致了農業投資的增加和農作物新品種的引進。正如經濟學家和農學家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所指出的,人口的增長和社會複雜性的提高通常與農業新技術的開發或引進以及互易交流的加強緊密相關。因此,我們不僅可以將絲綢之路理解為一系列地理線路的集合,還可以將其視為整個歐亞大陸社會聯絡日益密切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最終推動了整個舊世界的變革和社會複雜性的日益提高。絲綢之路成了食物全球化重要的渠道之一,這條互易交流的走廊在過去5000年裡一直在影響和塑造歐亞大陸各地的文化。
最後,我將以歐文·拉鐵摩爾的話作為全文的結尾,在內燃機尚未發明、二戰尚未徹底顛覆絲綢之路貿易路線的20世紀20年代初,這位傳奇探險家和學者曾隨駱駝商隊一起沿絲綢之路而行。在1929年寫下的文字裡,拉鐵摩爾對他在中國西部多地觀察到的變化扼腕嘆息:
在我們的時代,蒙古和中國新疆一帶的商隊向外輸出的每一批貨物都有所不同,但商旅們始終採用亙古不變的古老運輸方式,彷彿白人從未在亞洲出現過一樣。然而,他們的末日已然降臨。時代不可避免地發生著變化(在中國,時間的流逝往往以半個世紀為單位),在這樣的時代,懂得師夷長技的人將修建起連通寧夏和蘭州的鐵路,沙漠商隊很快便會淪為在阿拉善的沙海與大草原之間飄蕩的販夫走卒。走進這些市場的感覺十分奇怪——感受到難以名狀的、走遍天涯海角的沙漠商隊昔日生活的脈動,同時意識到明日的陰影將讓他們的一切傳統和特色面目全非。在卸下小小的行囊之後,趕駱駝的人邁著蹣跚的步伐走出城市,似乎期望在半小時之內慢悠悠地走回家中;然而,他拖著沉重的腳步一直走到營地,大篷車組成的商隊正在山丘背後等待著他,駱駝正在吃草,等待再一次裝滿行囊。等到營地拆除,他將再次艱難跋涉,一路抵達中亞。對於幹這一行的人來說,只要離開家鄉、搭起帳篷,他們便能不慌不忙地遠離充斥著電報和報紙、刺刀和戒嚴的文明社會,走進一片神秘而遼遠、只有他們知道入口的土地。
原作者 | [美]羅伯特·N.斯賓格勒三世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青青子
導語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