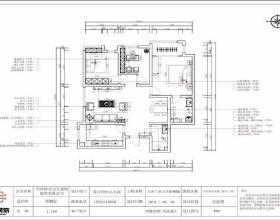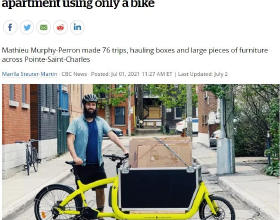小禾讀初中時,我發現手腕已經掰不過她了,自此,我對她就客氣很多,那個時候,她的想法是拯救世界和宇宙,有一天半夜,不知怎地坐在視窗啪嗒啪嗒掉眼淚。我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末了,她說了一句:“所有的思想,在提升之前,都要大哭一場的。”高中她去了上海,從此開始單飛,從杭州到上海,從香港到倫敦,兩人之間的話題話風,也是從現實走向魔幻。
一開始的畫風,總是和吃的有關係,在香港讀書的時候,她和同學排隊伍買了演唱會門票到深圳賣了,賺了幾千元錢,大吃了一頓海底撈。到倫敦後,有一次問我:”我們沒有錢哈,如果有錢,我在倫敦就可以買一隻烤鴨,現在不敢多買,只能買半隻。”我說:“什麼話麼,不就是一隻烤鴨嗎?這個鴨子總吃得起的,買買買。”小禾說:“半隻鴨子15英鎊,一隻鴨30英鎊,大概就是近300元人民幣。”我說:“你這個孩子,又不是趕馬車,吃一隻鴨幹嗎?要到海邊扛麻袋包嗎?半隻鴨足夠了,吃一隻鴨還不撐壞了。”
年三十我們各自一方,我問她:你在倫敦孤獨嗎,有沒有一種在異國他鄉漂泊的感覺?席慕蓉不就寫過:“從回家的夢裡醒來,布魯塞爾的燈火輝煌。我孤獨地投入人群中,人群投我以孤獨。”她說:“那都是你們大人的幼稚和矯情。”
這兩年,我們討論的話題有點像疫情時期的小區保安,問的都是直擊靈魂深處的終極哲學: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到哪裡去?有段時間,我發現自己走路發微信總會磕磕碰碰,我問小禾這是為什麼,她說因為我的智商是100分。我很高興,以為自己得了滿分。然後她說,100分就是正常及格的分數,這樣的智商一個時間段只能做一件事,走路不要發微信,同一個時間就思考一個問題。
有一陣子,各種事情紛至沓來,我和小禾說我肯定得了抑鬱症。她問我如果現在給我一個億,我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我說那肯定樂壞了。她說,那就不是抑鬱症,得抑鬱症的給一個億還是會不高興,你這是遇到問題了,就像渠道里的水被堵了,等困難解決就好了。我又問小禾,我覺得我的人生很悲涼,怎麼沒有遇見一個愛我的人。她說,愛情這個事情,是要看緣分的,是兩個人的事情,你不能強求別人,而且不能一天到晚把這事掛在嘴上,欲速則不達。我問她,你讀大學怎麼不談個戀愛呢?她說:“我們計算機和計算機的人,不會來電。不像你,幾首歌幾束花,爸爸當初就把你騙到手了,幼稚。”
我和她每次去日本,都喜歡去那些人煙寥寥的鄉間小路。清晨的路徑旁,逶迤著不著邊際的櫻樹,溫柔而靜謐,散發著古老的木質清香和恬淡的氣息,薄薄的花瓣上覆蓋著昨晚的露水或雨滴。一陣風過,櫻花如雪一樣在空中飛舞。一樹又一樹的櫻花,壓低的枝丫倒映在水面上,一時分不清這樹是長在水裡還是岸上。穿著婚紗的新娘倚靠在橋上的扶欄邊,和橋頭的新郎遙遙相望。真的應了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我很感慨:人到中年,韶華已逝,歲月苦短,這櫻花祭太讓人悲傷了。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那麼短暫和遺憾,當初的夢想,就像天涯的星星。我們在游泳,但是遊了一半,卻發現再也上不了岸。小禾卻不以為然:“凋零並不是意味著死亡,即使凋零後的櫻花,依然可以透過各種手法保留它的色、香、味,還是鮮豔美麗,楚楚動人。你們中老年人就是喜歡感慨,想做什麼事情,任何時候都不晚,野百合不也有春天麼。”
“今年我們是畢業季,別人問我們畢業了幹什麼,是工作還是考研,考研考哪裡,讀什麼專業,我真的回答不上來,我只知道,我們像一條船一樣,還沒有考慮好駛向哪裡,就暫時停泊在一個港口。”
小禾在港大讀了一年數學專業,後來又申請了帝國理工的計算機專業。因為疫情回國,本來研究生和本科連讀的學業,她自行選擇了本科先畢業,研究生再申請別的專業。我憂心忡忡地望著她,小禾開導我:“作為家長,你們真的不要為孩子去操心什麼,總能自食其力的。如果我像你們這樣考慮,當初我就會在港大讀完本科或研究生,拿個戶籍,我的孩子今後申請大陸名校就容易多了,為了下一代犧牲自己的想法,沒有意義,你們只要考慮過好自己的人生就行了。”
幾乎從初中開始,我們一直疲於奔命,總是忙著從一個車站奔到另一車站。讀了大學後,小禾三年年夜飯都是一個人在漢堡和水餃中度過的。大學四年,沒有穿過一次裙子,沒有談過一次戀愛,沒有好好地去看一段風景和旅程,一直像飛速旋轉的陀螺一樣,沒有時間去思考和停留。
但是,生活,畢竟是需要一些逗留和放空的。杭州最美的是秋季,斷橋的殘荷支稜著灰黑的身子,像是一把把扯斷絃的琵琶。北山路上飄落的法國梧桐葉,在地上翩躚起舞,跳的是春花秋月的曲子。小禾對我說,秋季你好好去看看西湖吧,那滿地的愛與哀愁,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邱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