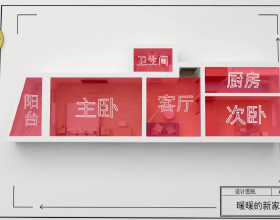戰火裡的人用火藥做煙花,照亮整個夜晚,他們流著淚雙手合十許願,願睜開眼是一個和平的明天。手術檯上的人在麻藥的作用下昏昏欲睡,手術前他提前換上了那件最喜歡的襯衫,在手術確認單上工工整整地留下自己的簽名和遺言。儀式感這東西,有時候就是能刺激人的多巴胺,不論在任何時候,都算得上一種安慰。或許它意味著結束,也有可能是一個嶄新的重生。
我保留自己的想念,隨著天上層出不窮的雲變換成懷念。
今年是特別有意思的一年。更多的驚喜和數不盡的意外,東拼西湊地填滿了這三百六十多天。我在三月頂著東北極寒的風形單影隻拖著行李到處走,六月的時候在悶熱的杭州,淋著淅瀝小雨到靈隱寺祈福,在剛剛好的八月重遊昆明,在每個凌晨和黑夜中徘徊,疲憊裡夾帶著無奈和心酸。在寒風剛起的九月飄在貴州,在每個九點後舉起一杯酒,怨言都變成沉默,變成蒙在被子裡的難以呼吸。
……
在很多時候都感到疲憊,從被子裡睜開眼的時候只覺得不真實。然後又把自己藏在被子裡,躲在暗處,不敢窺探外面的空氣和聲音。
慾望積壓成懊悔,把所有崇高的願景打散成一地破碎的現實。那些敏感和不安摧殘著自己變成一個愈發逃避現實的人。不想面對現實裡一無是處的自己,不想面對糟糕但又沒能力改變的現狀,不想面對隨時都可能突然崩壞的感情,不想面對未來還要活不知道多少年的時間。
安樂倉的發明成了最美好的嚮往。發明者說,每個人都有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力。活著和死了,只是不同的存在方式罷了,安樂倉是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
惶恐之中又是一年的尾聲。越長大越不敢回頭,不敢回看過去的那些年,過去發生的那些事。除了不敢回頭,還有不敢往前。
莫名其妙的,就是越來越邁不開腳。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給絆住的,但是不知道那個鎖釦怎麼開啟。
你說愉快,也不愉快。你說心安,但願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