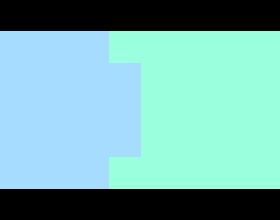老 彭
文/汪開宏
他說:和你在一起工作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
他還說:我們要生活得高貴一點。
他曾經給我發過一條簡訊: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我們相遇時,我三十六歲,他四十六歲。
而今天,他已經離開我們十年了。我撫摸著五十四歲的華髮,默默地想我們的人生故事。
我習慣叫他老彭,喝酒高興時叫他彭大將軍,他父親是湖南人,母親是四川人,都是支邊到我們這裡來的。後來在和他一次交談中知道他們老彭家原是個革命家族,大約和一位元帥有關係,他的叔叔姑姑都是老革命。他的母親我是見過的,七十多歲的人,穿長裙吸香菸划拳喝酒,因為以前不認識,我很驚奇她的行為,現在老了都這樣,可以想象年輕時她在我們那個小地方是多麼與眾不同。
老彭兄妹二人,妹妹從小聰慧過人,名牌大學讀研究生,國外博士畢業。老彭沒有上過大學,很早就參加了工作。他愛好文學,性格豪爽,對人真誠,有過遠大的理想,在我們這個偏僻的西部小鎮,是一個典型的文藝青年。他搞過文學創作,下海經過商。到和我一起工作時,搞了多年文學創作沒有作品發表,在商海闖蕩一番也沒有成功,便一心撲在工作上。
三十六歲那年,我出人意料地被派到西營當領導,老彭成了我的搭檔。那時,我心中揣著一團火,想著把自己管理的地方治理成為一個理想國。水利文化周、價值觀、讀書會、西營水韻、站段建設、三支隊伍建設、農民期盼已久安全衛生的自來水,搞得風風火火,我們一起相濡以沫地工作了六年,我們曾為工作而發生過爭執,也曾為某個問題而爭得面紅耳赤,對於我工作的完美主義理想主義他提醒過我,我也曾為他的自我控制管理差說過他,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因此而耿耿於懷,反而因為這些使我們真正走進了對方的心裡,這些年來,我們身邊盡是些很聰明的人,察言觀色的本領不小,說些你喜歡聽的話,市場經濟培養了功利性社會,也馴養了不少見風使舵的人,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成為了社會精英,而像他那種隨性生活,追求生活本質的人被淘汰為失敗者,想想看,身邊有他那樣一位朋友是多麼幸福的人啊,有些時候我在想,一個人的生命長度不能簡單地以年齡大小來衡量,生命的寬度和厚度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如果是簡單地重複過去,這樣的長度有什麼意義呢?
當他不幸早逝以後,我時常想起他;當我心情不好寂寞無助的時候,我總還會想起他。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期時,互相理解、互相支援,後來我因為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賦閒在家。他專門跑來安慰我,一個人一輩子哪能一直順呢,只要有一段時間心情舒暢地工作,那便是一個人的幸福,他說這些話的樣子,至今我還記得。為了來看我,他特意理了發,精心修剪過的小平頭,一件大紅襯衣,五十五歲的他看上去年輕了許多,他還給我女兒精心做了一盒麻辣牛肉。我知道他是在無聲地告訴我,要勇敢的度過這一段時光,同時我也能真切的感受到他的牽掛和擔憂。而不像有些人,大街上看到我就遠遠地避開,生怕因為我牽連到自己。我知道他也不去單位上班時,我隱隱有點擔心,並告訴他長期在家,可千萬不能徹夜地看書和通宵達旦地與電腦為伴,那對身體健康可是極大地傷害。誰也沒有想到,六月的一個早晨,他一聲不吭地永遠離開了我們。
關於他的早逝,有各種各樣的說法。那天是禮拜六早上,他又一次幾乎通宵達旦地熬夜之後,起床上廁所,然後跌倒在地上便再也沒有醒來。高血壓腦溢血且腦幹出血量很大,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有生命體徵了。他的早逝在我們周圍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因為在人們印象中他的身體是很健康的。這一點我與他共事近六年是最有發言權的,他的精力很好,中午從不休息,晚上整夜整夜熬夜,如果工作忙可以連續好長時間不休息。
我記得有一年發生洪災,我們夜以繼日搶險救災,他晝夜不停地在現場指揮,硬是不讓我連續工作。人們說他身體好是從他連續多年喝酒的原故,他的喝酒我是最清楚的。據他說,他小時候,父親喝酒的時候總要給小小的他一杯,慢慢地他也體會到了酒的神奇,工作以後他便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我發現他從來不拒絕酒,他告訴我喝酒是在追求喝酒帶給他的快樂,他一直把喝酒當成一件快樂的事在做。
有他在場,氣氛濃烈,只要別人給他酒他從來不拒絕,就是即將要醉了,也一概不拒絕,他用手端起一飲而盡,那姿勢很優美。我們喝酒必須要吃大塊的肉,用我們的話來說肉是用來滲酒的,可以多喝點酒,而且喝了就不難受。他喝酒幾乎不吃東西,我們是狼吞虎嚥,他總是細嚼慢嚥。有時候,我驚詫於他的身體素質那麼好,猜想原因也許是他那細嚼慢嚥的功勞。湖南人的辣四川人的麻在他的飲食習慣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愛吃米飯,我親眼看見他在蒸熟的米飯中加入用油潑的紅辣椒,美滋滋地吃下去,他的豪爽與對酒的熱愛一樣出名,所以許多人一聽到他的離世都馬上聯想到是因為酒的緣故。因為這些年由於喝酒出現的不幸事件也太多了,但是,這一次卻不是因為酒的緣故,因為他已經幾乎不怎麼喝酒了,是因為高血壓導致腦溢血。他有高血壓?讓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大吃一驚。
人到中年,對於世事已經有些看得清楚了,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榮辱得失,每天都在眼前浮現。特別是我在家那些年,更加有了切身的體會。但聽到他離去的訊息還是讓我久久不能平靜,好長一段時間,我的世界裡陰雨綿綿泥濘不堪。身體第一,以前只是說說,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對他的身體我也做過一些研究,他的長期喝酒,他的細嚼慢嚥,這些良好的飲食習慣也許是他的身體比別人好的原故。但他的醉酒、他的熬夜、他的不運動,這些都是健康的殺手。他自己有高血壓幾乎一年時間了,他沒有向任何人說。他去世時,我在外地為他寫了一副輓聯,“坦坦蕩蕩浩氣長存真性情,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好哥們”。
我從外地回來後,看見他的遺像禁不住淚如雨下,還是大紅的襯衣,一頭短髮,一副帥氣的眼晴,飽滿的笑容。這個人,永遠那麼真實、純粹,一直不隱藏任何東西的,怎麼把自己的病情隱藏得這麼隱蔽。在我們那裡,一個熱鬧的葬禮似乎代表著生前的榮耀,這些東西他是不喜歡的,他走後一些人勸家裡人要到單位去鬧。因為那時候他還不時去單位工作,社會的潛規則是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我不贊成這種庸俗無聊的處世哲學。他曾經給我說過,走到人群中,我們是默默無聞的一個小人物,一點不起眼,可是把自己活得高貴一點,卻也不是誰也做得到的。看到社會上的一些現象,他憂心忡忡又無可奈何,儘管無力改變但至少做到不同流合汙,所以我們常常會有失敗感。他這個人太單純,沒有心機,對人從不設防,這些可貴的優秀品質時常有挫敗感,在他身上一直儲存著一份知識分子的自尊與獨立。所以靜靜地走,更符合他的人生哲學。如果為了一點小小的利益而撕下顏面大吵大鬧,那是對他的侮辱極端的不尊重,他的母親妻子決定讓他有尊嚴地靜靜離去。他的葬禮樸素而簡單,他去時著西裝皮鞋,面容沉靜安詳。
他不在後,兒子還在外地上學。彭嫂每天靠回憶生活,他們的相識也是羅曼蒂克的。在一列開往春天的列車上他們第一次相遇,之後便是一場馬拉松式的戀愛,然後一起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以前老彭在的時候,她幾乎是不做飯的,家裡關於吃的一切都是老彭來打理的,他始終把做飯當成一件很神聖的事來做,可以說達到了酷愛的程度。經常研究食材的搭配,他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幾種色香味俱佳的菜品來,他曾經給我講過東坡肘子、白斬雞以及各種粥的做法以及要領。他講得津津有味,原來讓我恐懼並且望而卻步的廚房裡竟是那麼地引人入勝生機盎然。他吃飯也是充滿儀式感,即使是兩個人的晚餐,他也要炒五六個菜,然後把燈關了,點個蠟燭,兩人一頓飯耗時幾個小時。因為對廚藝的熱愛,越發使彭嫂進入廚房的機會減少,即使進入也只是做些打雜輔助性的事情,比如擇菜洗菜洗碗之類的事,後來從廚房的事延伸到了家庭的大小事幾乎都由老彭事無鉅細的包攬了。
那時彭嫂生活在明媚的陽光下。當時我們住在一個大院裡互相不認識,我透過窗子經常看見彭嫂騎著一個當時很時髦的摩托車進進出出,雍容典雅、氣質不凡。不久看見她和老彭手挽著手進出,心裡想著可能他們倆是夫妻,從他們的衣著打扮,氣質神態上判斷這是一對神仙伴侶,當我們互相熟悉後,發現他們還是一對精神伴侶。
又是一個六月,鶯飛草長,我和彭嫂一起去看他,這期間我幫助她處理完一些難事,並且幫助她走出了生活的陰影,兒子也成家立業,澎嫂向我表示感謝,我告訴她,如果是老澎,他會做得比我好,澎嫂也釋然了,新建的墓園在我們以前工作的地方,宏偉壯觀,功能完備。望著他的遺像,我們無語凝噎,想想人生無常,命運時常捉弄人,他在高處,好像沒有留下什麼,但又留給了我們太多的東西。他走了,把我們對於人生美好的嚮往都帶走了。我在想,一個人一生到底需要幾個真正的朋友。也許一個,也許兩三個,或者只有一個就足夠了。沒有了他這樣的良師益友,我們都得面對自己的生活。他是我的一把尺子,時刻丈量校正我的腳下的路,他是我的一面鏡子,隨時照亮我的言行,我們紀念他,不如說是我們向我們的過去告別;我們悼念他,更多的是尋找我們明天的方向;我們懷念他,其實是懷念我們曾經的自己。他的優點,是我們的高度,他的缺點,同樣是我們的高度。
茲別西營無來去,人道蒼茫又十年。這些年,我在異地他鄉,經常面對人生中的誘惑與挑戰,時常想起他的告誡,我們要活得高貴些,想起他大紅色的襯衣,那些燦爛的目光,那些我們一起工作最幸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