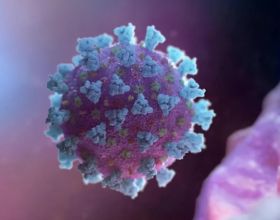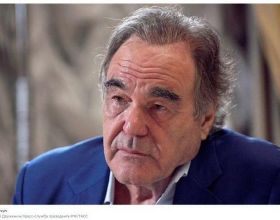談及古代數學成就,很多人言必談古希臘,言必稱歐洲,但實際上中國古代數學不僅不遜色,整體反而還要超出西方。天文學是推動古代數學進步的關鍵動力,與古希臘以及西方天文學莫名其妙地突然發達不同,中國古代天文學一步一個腳印,早在帝堯時就有“觀象授時”,最遲商代時已有曆法,元代時在南海、北海分別測出北極星角度,在開封與西域分別測出月食出現時間,由此確定經度差與緯度差,如此發達的天文學焉能沒有高深的數學與之匹配?
宋元時期中國數學非常發達,但對於明朝數學,流傳這麼一個觀點,即“近史期算學,自明初至清初約當公元1367年迄1750年,前後約400年……民間算學大師又繼起無人,是稱中算沉寂時期”,“明代中葉以後,出版了很多商人所寫的珠算讀本,對比較高深的宋元數學只能付之闕如,中國古代傳統數學到明代幾乎失傳”。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明朝還有一位鮮為人知的大師,此人叫王文素。
明朝時期,出現了一位大數學家——王文素,留下一本50萬字的數學專著——《算學寶鑑》,其中成就讓人目眩神迷:
解高次方程的方法,比英國的霍納、義大利的魯非尼早200多年。
在解代數方程上,走在牛頓、拉夫森的前面140多年。
對於17世紀微積分創立時期出現的導數,他在16世紀已率先發現並使用。
《算學寶鑑》中的“開方本源圖”獨具中國古代數學傳統特色,國外類似的圖首見於法國數學家斯蒂非爾1544年著的《整數算術》一書,比《算學寶鑑》遲20年且不夠完備。
直至清朝,《算學寶鑑》在中國古典數學書中也是獨一無二的,可稱之為中國算史之最。
作為明清數學第一人,世界級的數學大師,王文素與明朝晚期的數學大師程大位(世界捲尺之父)一樣,都是經商世家,區別在於一個是晉商,一個是徽商。
王文素是山西汾陽人,大約出生於明朝成化年間,少時跟隨父親王林到河北饒陽經商,之後就定居在了河北。或許,由於商人需要經常計算的原因,讓王文素自幼對數學就頗感興趣。
明朝時期,重科舉、重功名,習文尚武,獨輕數學,專攻數學的文人少之又少,基本上是“能詩文而不獵取功名者”才學之。對於這種現象,王文素痛心疾首,他指出數學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間,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於是在書中對當時社會現狀進行了批評,“上古聖賢猶且重之,況今之常人豈可以為六藝之末而忽之乎?”又賦詩曰:“若無先聖傳流此,自古模糊直到今!”可惜,王文素只是塵世中的一粒塵埃,根本撼動不了世人的想法。於是,王文素只能“陋室半間尋妙理,靈臺一點悟玄機”,苦中作樂又樂在其中,甘守寂寞三十年後,完成50萬字的前無古人的鴻篇鉅製《算學寶鑑》。
由於社會不重視數學,加之王文素商人身份,導致王文素鮮為人知,史書上對他幾乎沒有記載,現存的《算學寶鑑》“四百年間未見各收藏家及公私書目著錄,民國年間由北京圖書館於舊書肆中發現一蘭格抄本而得以入藏”。不幸中的萬幸,否則我們後人根本不知道明朝曾經有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數學大師存在過。
《算學寶鑑》中王文素的數學成就,可以從國內與國際兩個方面來看:
從國內來看,王文素站在賈憲、楊輝、秦九韶、朱世傑等巨人的肩膀上,將很多傳統數學問題進一步深入,即“歷將諸籍所載題術,逐一測深探遠,細論研推,其所當者述之,誤者改之,繁者刪之,缺者補之,亂者理之,斷者續之。復增乘除圖草,定位式樣,開方演段,捷徑成術,編為拙歌,注以俗解”。
其中,對研究數字排列組合的縱橫圖(現也稱為幻方)的研究,比如連環圖、纓絡圖、三同六變圖等等,複雜程度遠遠高於宋朝楊輝、明朝程大位,甚至在直至清朝,在我們所知的中國古典數學書中也是獨一無二的,可稱之為中國算史之最。
透過《算學寶鑑》一書,可以看到數學界流傳的觀點並不準確,宋元的天元術等在明朝並未失傳,宋元時代高度發展的中國數學也沒有完全中斷,同時明朝也有繼往開來的數學大師,在世界數學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頁。
從國際來看,王文素在解高次方程、代數方程、發明微積分導數等上面,遠遠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中王文素髮明的導數,比歐洲早了100多年。
微積分是古代中國與歐洲數學差距的分界線,但微積分產生的兩個前提是極限概念和積分與微分的互理關係,其中極限概念春秋戰國時已經出現,戰國惠施說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因此,對於王文素髮現了導數,一些現代學者不無遺憾地指出,“中國古代數學有了微積分前兩階段的出色工作,其中許多都是微積分得以創立的關鍵,中國已具備了17世紀發明微積分前夕的全部內在條件,已經接近微積分的大門”,可惜由於明清大環境的原因,導致歐洲人走在了前面。
可惜的是,這樣一位大數學家,卻被淹沒在歷史的煙雲之中,以至《算學寶鑑》“四百年間未見各收藏家及公私書目著錄”,直到民國時期,有人才在舊書市場上發現一手抄本,如此《算學寶鑑》才重現天日,王文素的成就才為世人知道。往事已矣,如今民間不乏大才鉅著,我們只能思考如何不讓這種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