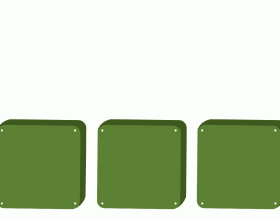我叫吳大柱,90後,出生在廣西馬山縣。我家被縣裡評定為特困戶,從我記事起,家裡就一貧如洗。
我父親叫吳有糧,我還有個小我6歲的弟弟,叫吳二柱。母親在生完弟弟後不久,得了重病,花光了家中為數不多的積蓄,還欠了一屁股債,最後也沒能把人留住。父親一個人辛苦把我和弟弟拉扯大,一直沒再娶。
從小隻喝了幾天奶的弟弟是被父親用米湯水灌大的,身子弱,一直很瘦。可窮人家的孩子,能保住性命就已經用盡全力了。我和弟弟上完初中後,便先後紛紛回了家,幫忙幹活掙口糧。
前幾年光景好,我家慢慢把欠債還了一部分,此時我和鄰村的小英開始談婚論嫁。父親見我年紀也不小了,就湊了點錢蓋了間小廂房,幫我把婚事辦了。
二柱也進鎮上最大的汽修廠當了學徒,日子有了盼頭,父親開始有了微笑,佝僂的腰好像都挺直了些。
好景不長,2016年5月,剛轉正不久的二柱,在幫大貨車補胎的時候出了事。巨大的輪胎剛一落地就炸了,一聲巨響,幾百米外都能清楚聽見,像放炮一樣,驚得街對面的飯店玻璃都顫抖起來。
二柱直接被炸飛了,重重跌下撞在一旁的鐵塊上,頭蓋骨破裂,血不停往外噴湧。縣醫院不收,直接送往市醫院,住進了ICU,一直沒醒過來。
重症病房一天的花費要好幾千,家裡本來沒什麼積蓄,而現在能借的,都借了個遍。汽修廠的王老闆安排人把弟弟送進醫院後,再不露面,打他電話死活不接,想推卸責任。父親老實了一輩子,不知如何是好,只知捶胸嘆氣。我把醫院的弟弟交給父親守著,買了一壺汽油,提了把菜刀,去找王老闆理論。
跑到汽修廠,卻沒看到王老闆,我知道他肯定躲了起來,便在門口大罵:“天殺的老王,你給我出來,我弟弟在你這出了事,你就得管,再不出來,我一把火把你這燒了信不信!”
我從揹包裡拿出提前準備好的汽油,舉在手上。許是員工告訴了他,王老闆臉色鐵青,很快從別處趕了過來,說有事好好商量,沒必要動武啊。
我倆拉扯吵嚷了半天,正要把王老闆拉去醫院的時候,警察來了。應該是有人報了警,但我不怕。
警察瞭解情況後繳了我的刀和汽油,狠狠地教育了我一番。鑑於事出有因,就不追究了,然後又勸王老闆直面問題,躲不是辦法,從法律上講,他確實需要承擔責任,王老闆連連點頭。
當天晚上,醫院就下了病危通知書,再不搶救,回天乏術。
02
全家人都來了,在影片監控上,我們看到病床上的二柱躺得平成了一片紙,纏滿繃帶的頭因為顱內出血而變得腫脹,像一顆隨時要爆炸的氣球。
王老闆也看到了這一慕,就去補交了一些醫藥費,回來後把醫院開的收據給我看了下。
小英挺著大肚子在一旁偷偷抹淚,我知道她心裡急,還有幾天就是預產期了,結果卻出了這天大的事。
二柱的主治醫生把我們叫到辦公室,王老闆也跟了進來。
醫生直截了當地說:“病人情況不太樂觀,傷到了中樞神經,但他的求生慾望很強烈,呼吸和心臟的跳動還算平穩,監測的各項體徵保持得還算不錯,如果全力搶救的話,有希望保住性命,但極有可能成為植物人。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現在就是跟時間賽跑,你們早做決定,是否繼續搶救。”
全家人都沉默不語,齊刷刷將目光投向了王老闆。
王老闆被我們看得有些尷尬,退到走廊外打電話。醫生再次問我們做決定了沒,我說我們再商量一下。父親很焦急,來回走動,家裡真的一分錢都拿不出來了。
我出門找王老闆,在轉角處聽到他跟別人打電話:“如果全力搶救,那也是一個植物人,我得負擔他一輩子的養護費用,那跟供了個祖宗有什麼區別?加上搶救費,也是一個不菲的數目,還不如一次性買斷,無論結果如何,都與我無關了。”
我怒火中燒,衝上去就想扇他兩耳光。最後,舉在半空的手還是沒能揮下去,這個時候除了他,我們還能指望誰?王老闆提出回去籌錢,我狠狠地威脅他:“我明白地告訴你,你最好不要耍花招,你的命可比我的值錢!”
因為我要照顧即將臨盆的小英,所以父親留在醫院守著二柱。弟弟出事後,他一直愁眉不展,臉上的溝壑越發深沉,老了許多。
小英肚子已經很大,彎腰都變得困難,我幫她洗了把臉。她突然說:“你心裡咋想的,倒是說個話,爹爹拿不定主意,你現在就是家裡的頂樑柱,這事還是得你決定,弟弟情況危急,拖不得。”
小英說得對,不能再等了。我馬上打電話給王老闆,開門見山:“你籌到錢了沒?打算出多少?”
王老闆說:“五十萬,這已經是我的最大限度了,仁至義盡,從此我與此事無關,你也不要來我這生事,如果不同意,那去走法律程式好了。”
他這是拿準了我們的軟肋,如果上法院的話,一時半會根本不會有結果,弟弟的治療費從哪來?救弟弟要緊,我跟父親打電話商量了此事後,只有同意。
第二天上午,王老闆把錢打了過來,併到我家面簽了諒解協議。由於我要趕著去醫院簽字交費搶救弟弟,胡亂扒了幾口飯正要出去,小英一把拉住我說:“先別急,我有事要說。”
03
弟弟出事後,她也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一直無暇過問,便停下了腳步。
小英說:“昨兒醫生的話你也聽到了,二柱現在的情況就算搶救過來,也是個植物人,命是撿回來了,但以後呢?他的生活怎麼辦,誰來照顧他?你爹一輩子辛苦,沒過上一天好日子,難道末了還要他來受這罪?
“另外,說句你不愛聽的,爹年紀也大了,還能活幾年?他百年歸西之後,二柱這個擔子還不得你來挑?我們的孩子馬上就要出生了,一家老小指著你吃飯,你有多大能耐,扛得住?”
我不吭聲,小英說得確實有道理。
小英繼續說:“吳大柱,你看你家裡窮成啥樣,當初我決定跟你,是看你真心待我好,人又本份,盼著會有苦盡甘來的一天,我爹孃罵我傻,說我這是往火坑裡跳,我不信。可如今這事情發展下去,你真是要把我往火坑裡推啊!”
小英越說越激動,眼睛蓄了淚,紅了臉,呼吸急促起來。
我無奈地說:“那你要我咋辦?那可是我親弟弟,從小穿一條褲子長大的親人啊。”
小英咬咬嘴唇說:“我知道,可總要面對現實,老天註定二柱要受此劫難,你救得了他的命,但沒有魂,這命還不一定救得下來,到時候錢花了,人沒留下,或者留下了,也拖累你一輩子。你想過我和肚子裡的孩子嗎?放棄治療,把錢留下來,好好孝敬咱爹吧!”
聽了小英的話,我心裡煩得很,腦子也亂糟糟,不知道如何是好,便想抽菸。我跑到父親屋子裡找煙桿,看到隔壁弟弟的屋,毛巾牙刷和床被枕頭等,雖然破舊,可都疊放得非常整齊。
弟弟一向比我愛整潔,家裡窮是窮點,但他自己的東西,都歸置的特別好。他在鎮上當學徒,有吃有住,走時還把自己的窩打理好,想必盼著再回家時,可以舒服地直接住。可現在,弟弟能有回來的那一天嗎?
弟弟五六歲時,像個跟屁蟲,死活要我帶他一起玩。我嫌他小,玩不到一起,趕都趕不走,有時煩了,直接劈頭就甩他一巴掌。他就算被打哭了,也還要跟著我。
我上初中時住讀,父親帶著他一起給我送錢送棉被時,趁父親上廁所,他解開我穿小後留給他的破棉襖,從貼身的衣服口袋裡掏出兩個雞蛋,說是父親早上煮給他吃的,他沒捨得,要我趁熱快點吃。
弟弟性格活潑,家裡再窮,也沒見他喪氣過。我當年結婚時,他把自己當學徒時拿到的一點微薄的補貼,全都給了我,說錢很少,但可以給嫂子多買身新衣服,不能讓她覺得嫁過來委屈。
為什麼以前我就沒想過這些呢?為什麼我以前沒有意識到他的好呢?為什麼當我想要對他好的時候,他卻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一點機會都不給我。想到這裡,我的心像被鞭子在抽,一陣陣生疼。
不行,我要救他!我承認,我承擔不起日後要照顧一個植物人的擔子,可他是我的弟弟,我不能放棄。小英知道我的決定後,又急又氣,一邊跺腳一邊哭。突然,她捂著肚子喊起來,見她疼得站不直身,我心裡一驚,趕緊把她送到縣醫院,醫生檢視情況後,立馬進行生產準備。
我心裡牽掛著等我送救命錢的弟弟,趕緊打電話通知了岳父岳母,給小英的住院賬戶充了5000塊錢後,又立馬趕往了市醫院。
04
去往市醫院的路上,我想起小英對我說的那些話,想到我那即將要出世的孩子,想到父親年紀這麼大,也沒享過福……我突然陷入了深深的糾結之中,心裡猶如百爪撓心。
剛奔波到市醫院,岳父打來電話,說小英順產產下一子,5斤2兩,母子平安。
我懸著的心總算落了地,要岳父把電話給小英,我想要親口對她說辛苦了。小英卻虛弱地在電話對我說:“給你生了個帶把兒的,為了以後的日子著想,你去和爹說說吧。”
我無力地在電話裡“嗯”了一聲。趁告訴父親這個喜訊的機會,我把放棄弟弟治療的想法跟他提了。他立馬跳起來,大罵了一聲:“畜生!”抬手就要扇過來,最後卻一巴掌重重地拍在自己大腿上:“你這孩子,咋能這麼狠心,你弟弟才二十二歲啊,他的人生才剛開了個頭啊!我兒的命怎麼就這麼苦……”
我流著淚把小英的話講了一遍給他聽,“爸,你說沒了魂的二柱,活著能快樂嗎?”父親梗著脖子說:“沒了魂我也要救他!王老闆賠的那50萬是給你弟弟的,你別打什麼主意!”
“好,好,你去救!醫生都說了,救過來最好的情況也是植物人,到時你老了,我除了管你,還要管植物人弟弟,還要養孩子,你說,我承擔得起嗎?我承擔得起嗎?我又沒什麼本事……”說完這些,我號啕大哭。一方面,我知道我自私,可我又沒有兩全的選擇,另一方面,我也內疚也心疼,各種情緒摻雜在一起,讓我痛苦得恨不得一頭撞死算了。
這時,醫生又來要我們做決定了,說再耽誤下去就沒救了。父親沉默了。最後,他提出想進重症病房,想要近距離去看一眼弟弟,出來後,他給出最後的決定。
ICU本來也有探視時間,醫生同意了。我和父親穿上無菌服,在護士的帶領下,進了ICU。父親來到弟弟病床前,看著弟弟的頭被包紮得嚴嚴實實,還上著呼吸機,一下就站不穩了,我連忙架住了他。
“兒啊…兒啊…”父親低聲喃喃,我的眼淚也流了出來。“我心疼吶,從小到大,你跟著我這個窮漢子吃了那麼多苦,別人家孩子穿新衣服,你只能眼巴巴地望著,在外受的委屈也從不跟我說。日子剛有了奔頭又出了這檔子事,前面是手上沒錢為難,現在王老闆賠了一點錢,我又怕……我又怕像當年你媽那樣,折騰了一圈,還是人財兩空,我好為難啊,兒啊……”父親有些控制不住,越說越激動。
護士聞聲連忙過來阻止,沒想到,此時弟弟床頭的儀器開始發出聲音。父親呆立了2秒,對護士說:“他,他聽到了?”護士連忙請我倆出去,並呼叫主治醫生。
醫生重新從ICU出來後,對我們搖了搖頭說:“病人的情況變糟了,血壓忽高忽低,顱內水腫更加嚴重,監護儀記錄的心率資料也不平穩,各項體徵都顯示他沒有搶救的必要了。護士說,你們剛才對著病人說話了?”
“我兒聽到我說的話了嗎?醫生,你不是說他是昏迷的嗎?”父親懷疑是自己的話刺激到了弟弟,慌忙問道。“這說不好,你們之前沒有明確要全力搶救,我們也只是進行最低限度的藥物保守治療。就他身體的表徵來看,他確實是一直處於意識模糊狀態。不過,也說不準。你們準備一下後事吧。”醫生無奈地搖搖頭。
父親癱坐在椅子上哭了起,對著我說:“大柱啊,你弟弟這是自己要走了,他一定是知道我難,知道這個家難,知道他的這些親人難,不想再拖累我們,他是自己放棄了呀。他從小到大都那麼懂事,懂事得讓人心都不知道該往哪疼……”
05
二柱最終還是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在等待殯儀館的人前來拉人時,父親坐在二柱床前,拉著他的手撫摸自己的臉。突然間,父親拿著二柱的手不停抽打自己,口中不停喊著“兒啊,爹對不起你!爹承認有私心,爹真不應該對你說那些話的啊,兒啊!”
我急忙上前拉住,和父親一起伏在床邊哭起來。
二柱出殯那天,我買來了全套的正版阿迪達斯衣服和鞋子,弟弟生前一直想要,但沒錢買,也捨不得。我幫他穿上新衣服,看了最後一眼,天人永隔。
葬禮上,嶄新的棺木被高高託舉,鑼鼓喧天,鞭炮放個不停,二柱的葬禮辦得熱鬧而隆重,按村裡的最高規格進行。送弟弟的骨灰盒入土時,父親哭得暈倒在地。
弟弟走後,我們用王老闆賠的錢,蓋起了小樓房,紅磚綠瓦。父親特意留了一個大房間,裡面都是二柱生前的東西,還有一張鋪了席夢思的大床。
為了紀念弟弟,我為兒子取名“小狗子”。二柱生前的小名是二狗子。隨著小狗子的慢慢長大,開始咿呀學語,父親偶爾會抱著他去二柱的墳前坐坐,對著孩子說:“現在的好日子,都是你二叔給的,以後要多來看看他。”
父親隔三岔五會跑到二柱的床上休息,上面的物件都收拾得整整齊齊,我知道他老人家想二柱了。
有一次,岳父母來家裡串門,小英炒了幾個菜,我陪著一塊喝酒。
酒喝到大半,父親拍著岳父的肩膀說:“親家,小英以前跟著我們大柱吃了不少苦,但現在日子越過越好了,他倆開的夫妻店的生意也不錯。你不用擔心,我現在還幹得動,能幫他們,等我老得動不了了,也不給他們添麻煩,會自己了結的,去找二柱和他娘。”
我看父親話說得越來越不對勁,趕忙搭話:“爹,你沒喝多吧,都說些什麼呢?”
父親把一杯酒乾了,說:“我現在天天做夢,夢見二柱揹著豬草往回走,他那小身板背那麼大個簍子,我心疼,我後悔啊,怎麼就讓他走了呢……”
有一次,我正在切菜,轉身看到父親拿著個碗,掀開煮飯的鍋蓋,正用勺子舀米湯。我問他:“爹,你在幹什麼呢?”
父親邊舀邊說:“小狗子餓了,我弄米湯給他喝呀。”
我有些詫異,小狗子都1歲多了,早就吃乾飯了呀。父親恍然大悟,說:“哦,我給記錯了,我剛才把小狗子當成了二柱小時候。”
我看著他失望的背影,不禁鼻子一酸,他心裡對二柱的牽掛從未減少半分。晚上,我對小英說:“以後讓小狗子多陪陪他爺爺,二柱走了,他很孤單。”
小英點頭同意,我們的新生活在慢慢展開,二柱的影子卻從未離開過這個家。埋在心底的痛和內疚,有時壓得我會喘不過氣。沒人的時候,我也會在二柱墳前使勁哭一場。
父親對此也心知肚明,只是誰也不會再主動去提。命如螻蟻,貧賤如斯。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我們活得好好的,才是對弟弟最大的告慰。我想,他也會希望我們能快樂的活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