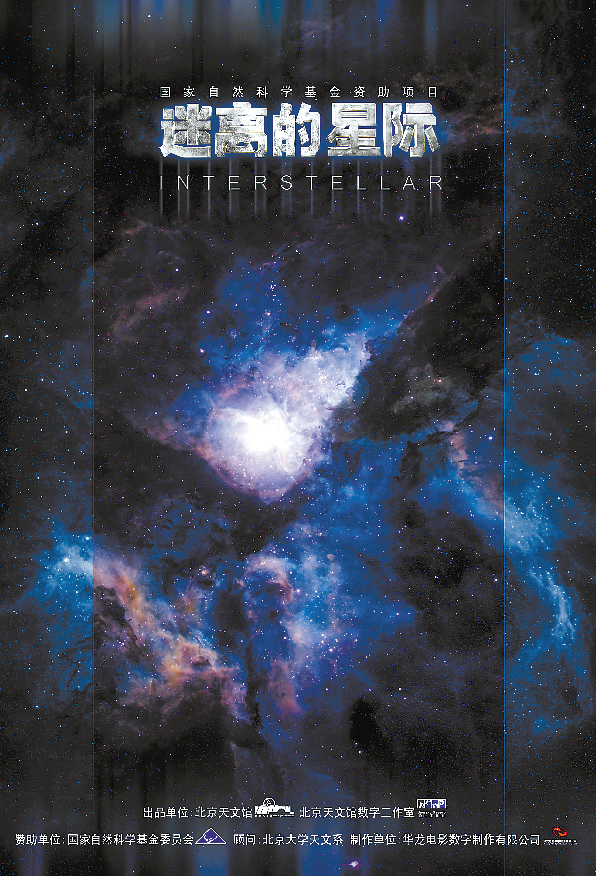世界浩瀚,宇宙無垠。
面對頭頂上的這片蒼穹,人類毫不吝嗇地傾注深情與想象,從未停止過夢想和渴求;然而,真正有機會遨遊其中的人卻是少之又少。球幕影片的橫空出世,讓宇宙星系不再遙不可及;置身於高畫質晰度的超大穹形畫面中,萬里之外的璀璨光芒照亮人們好奇的雙眼。
讓人遺憾的是,這曾經是個被國外壟斷的領域。
北京天文館數字工作室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局面。這支製作特種科普影片的專業團隊一路“較勁”,只為打造中國人自己的天象大片,用中國元素講述天文故事。
打造中國人自己的天象大片,吳薇製圖
是精打細磨的藝術呈現,也是孜孜不倦的技術創新。由其打造的十幾部原創影片中,《迷離的星際》榮獲2016年度北京科學技術獎三等獎,《天上的宮殿》榮獲2020年度北京市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數字工作室主任宋宇瑩將這一過程形容為“做翻譯”,透過球幕、影像、解說、音樂等種種手段,把天文學高深的理論與發現帶給尋常人,播撒下好奇的種子。他堅信,終有一天,小小的種子會生根發芽,成長為鬱鬱蔥蔥的大樹。
2004年,北京天文館新館落成,天象廳、宇宙劇場、4D劇場、3D劇場為天文科普提供了一方嶄新天地。
“有劇場就得有節目,就像一個電影院,沒有片子是不行的,所以那時,我們策劃成立了北京天文館數字工作室。”天文館黨委副書記、科普影片主創景海榮見證了數字工作室的從無到有,“說實在的,剛成立的時候,我們是兩眼一抹黑,對球幕,甚至3D、4D都不是特別瞭解。”當時,即便在國際上,這類影片也還是個新鮮事物。
不過,再難也要自己做,這一點是初創成員的共識。
“不同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受眾,其思維模式、精神核心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能只靠引進,而是要講自己的天文故事。”在景海榮看來,製作原創影片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打破國外片源的壟斷,“沒有創作權,就沒有議價權,最初引入的片子都是按年收取租金,價格十分昂貴。”
討論之後,首部片子的主題瞄向了人們熟悉的“天空中最亮的星”。主幹有了,如何讓它枝繁葉茂,靠的是數字工作室成員紮實的案頭工作和嚴謹的科學精神。
“無論什麼主題,最開始都要先蒐集素材。”北京天文館研究員、科普影片撰稿人劉茜介紹,支撐起一部節目的素材是多元化的。比如,科學類的素材,也就是從天文學專業的角度,挑選出易於呈現給觀眾的內容;影象圖形類的素材,團隊要對與該主題相關的畫面、影像進行儲備。此外,主創還要在科學視覺化上進行技術儲備。
而技術上的儲備是最難的。一切都要摸著石頭過河。
新館落成時,宇宙劇場引進的是世界一流的天象演示裝置,然而,由於版權問題,天文館無權使用此裝置生成的畫面來創作屬於自己獨立版權的節目。為此,數字工作室攻克大量技術難關,從零開始,自主研發了一套星空天象系統,“這是我們所有影片製作的基礎。”宋宇瑩說。不僅如此,團隊還要依據影片的主題,對相關的天文觀測和數值模擬結果進行三維重建和科學資料視覺化等。
“對於觀看球幕影片的觀眾來說,沒有看普通平面影視的距離感,觀眾跟螢幕場景結合的緊密度更強,因此,在場景變換和處理上都要更加精巧。鏡頭的任何異動都有可能給觀影帶來直接的影響。”有天文學和英國文學專業背景的劉茜,如今已經是個“球幕專家”。球幕製作零起點的她,如今已經練就了敏感的“球幕思維”:眼睛掃到平面構圖,腦海中會自動反映出構圖在球幕上的效果。
“這個本事是一個個大夜熬出來的。”劉茜笑言,在最初製作影片的時候,白天劇場有演出,工作室的同事們只能靠晚上的時間來熟悉球幕場景。
2007年初,22分鐘的《迷離的星際》首次亮相。在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中,觀眾們目睹著恆星的“生老病死”,在星辰間穿梭旅行,直呼“過癮”。景海榮緊繃的神經鬆了下來。這第一炮算是打響了。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觀眾是否認可的問題,因為影片出來,要直接跟國外的片子PK;而在當時,只有國外最好的場館才在做片子,質量都是很過硬的。”
作為一部純粹的入門級影片,《迷離的星際》無疑是合格的,甚至是出色的。十幾年過去,這部片子依然是天文館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但是景海榮內心卻有一絲遺憾,“為了給觀眾帶來視覺上的衝擊,我們當時把很多震撼的畫面都融了進去,現在想來其實有點兒用力過猛了,也有點兒過於討好觀眾的意思,還是因為心裡面沒底,有點兒心虛。”
在劉茜看來,這部片子少了些“內在的深層的東西”,知識點有了,但是知識網路和知識體系沒有架構起來。好在,天文館同時舉辦了各種配套的活動和展覽,使得影片成為教育體系的一部分,主創團隊心中的“意難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紓解。
在2016年度北京科學技術獎評選中,該影片榮獲三等獎。“這一成果填補了我國大型數字天象節目的空白,打破了國外數字球幕片商的壟斷,突破了傳統天象節目在表現手段上的侷限。”評委們如是說。
用中國元素講述天文故事
仰視穹幕,星空對映成一幅巨大的地圖:城市村莊、山川原野、亭臺樓閣……璀璨星辰呼應著世間的萬事萬物;天帝居住的“紫微垣”、天庭官員辦公的“太微垣”、天界貿易市場“天市垣”……人間的煙火氣在星星點點中生動再現。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曾經有一套自己的星座系統;和西方的星座不同,在中國的星座體系中,從宮殿到糧倉、從兵營到集市,都事無鉅細地被古代的中國人搬到了天上。
“在世界天文學歷史中,中國古代天文的發展曾經處於絕對領先的地位。然而,讓我們引以為豪的這些歷史在現代的科普特效影片中鮮有涉及。”景海榮說,當時,世界上所有球幕影片的選題和呈現方式都是全西式的,從未有具備中國元素的影片問世。
“我們就想較這個勁。”團隊覺得有這個責任。
古代天文知識浩如煙海,故事該從何講起?經過反覆論證,工作室將主題定在了古代“三垣二十八宿”星座系統上:一方面,這是一個大家會感興趣的話題,觀眾可以在觀影中對比,既可以進行古今的對比,也可以進行中西的對比;另一方面,古代星座系統是古代科學技術、傳統文化、哲學思想等的集中體現,是我國“天人合一”理念的代表。此外,團隊還為影片賦予了“闢謠”的使命,“古代天文學常被迷信誤讀和利用,我們覺得有必要為觀眾提供詳細介紹其科學性的科普影片。”宋宇瑩說。
於是,便有了《天上的宮殿》。
作為再次開先河的嘗試,團隊面臨著很多暫無他人開拓的新領域。比如,國內外現有的各種數字天象儀、數字宇宙系統都只包含了西洋星座的連線和亮星;只有少數系統中有少量亮星帶有中文名字標識,但顯然也不能應用於中國古代天文學主題。為此,工作室在自行研發的數字天球系統中,依據伊世同《中國古典星圖》等資料考證,整理加入了中國古代星官連線及星名,完成了1000餘個星官在三維繫統中的構建和定位,使中國古代星座系統成為數字宇宙系統的一部分。正是由於該數字宇宙系統的應用,才使影片實現了觀眾在古代星空中穿梭的視覺效果。
大的基礎有了,每一幀都需要細細打磨。這背後,有無數的爭吵、妥協退讓,也有“頑固”的堅守。比如,在最初的版本里,劉茜堅持整部影片“零臺詞”,她認為,對中國傳統文化而言,說得多了,反而會侷限觀眾的思維和想象。景海榮卻表示反對,“零臺詞的方式對故事片或許可行,但對科普片是很難的。”反覆的溝通、討論甚至爭吵後,劉茜慢慢放棄了這個想法,她後來意識到,大部分觀眾對古代天文的瞭解是有限的,零臺詞無疑為觀眾觀影設定了一個很高的門檻,“我們不能一味地給觀眾灌輸什麼,只要觀眾看完覺得這個東西有意思,就夠了。”
有時候,有些好的創意和想法也不得不因難以實現而放棄。影片一開始設計了日月五行乘坐馬車在“賽道”前進的畫面,以表現不同天體的執行速度。然而,要如何科學地體現出天體執行的快慢?快慢背後又有著怎樣的科學原理?看似一個簡單的畫面,要完全讓觀眾看明白卻並不容易。“全部靠解說就沒意思了,但是不說清楚,這樣的一個畫面設定又是沒有意義的。”最終,這個想法被“折衷”了,影片只展現了月亮沿著二十八宿執行的情況。再比如,為了充分體現“天人合一”的理念,影片最初想為代表地面上宮城、皇城、市場的三垣設計更多的人物互動,最後受影片時長所限,這個想法也只能作罷。
而科學性是團隊堅守的毫不退讓的底線。一次,半夜審片的劉茜發現,其合作的動畫製作方搞錯了某個場景下星空轉動的方向,非專業背景的人可能根本看不出其中的差別,但在團隊看來,這種科學上的偏離絲毫不能容忍。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室經過大量的資料蒐集與考證、美工繪圖、圖片處理等,對於影片中涉及的100餘個星座,採用工筆花鳥、工筆人物、小寫意樓閣、小寫意山水等手法進行了形象設計與繪製;首次把國畫工筆重彩、淡彩暈染、水墨烘托等特色技法全面呈現在球幕上,透過對鏡頭運動、場景設定和模型擺放等諸多相關因素的計算和變形,將平面的國畫手繪素材體現到球面、魚眼、三維的鏡頭中,在技術上解決了國畫手繪效果在魚眼鏡頭的實現。“我們想做一個從裡到外、從上到下都是中國味道的產品。”宋宇瑩說。
讓團隊特別振奮的是,該影片還成功地推廣至國外天文館,在墨西哥境內觀看已超15萬人次,實現了文化輸出,為“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將全景實拍融入特效影片
在宋宇瑩看來,獨闢蹊徑的十幾年裡,團隊更像是在無人之境中探路,“有時候探完路就走通了,有時也會碰到各種‘坑坑窪窪’,這時,我們就得原路折返。”
比如,團隊曾試圖在球幕影片中打造角色IP,以形成品牌效應。但是後來發現,在球幕觀影體驗中,最大的主角是觀眾自己;如果強行再在螢幕上加入更多主角,短短的20多分鐘時間裡,觀眾根本來不及深入地瞭解角色。
在業內,宋宇瑩還曾被冠以“8K先生”的稱號,這背後也有一段曲折的探索。當時,為了追求更加極致的視覺清晰度,團隊在一部影片中創造性地採用了8K×8K的世界最高解析度。“畫面解析度提高了,對創作中各個環節的要求都變高了,而現有的工具並不能滿足這種創作要求,使得整個創作的效率反而變低。所以雖然在技術上取得了突破,但是最終呈現出的效果卻並不是最理想的。”因此,在接下來的影片中,團隊繼續迴歸了4K製作。
儘管道路並不平坦,但是團隊卻從不氣餒,從未止步。
最新上映的《宇宙大爆炸》則是團隊一次成功的嘗試。影片在將抽象的“宇宙大爆炸”視覺化的同時,還採用實地拍攝的方式,把科學家瞭解宇宙的有力工具——郭守敬望遠鏡、“中國天眼”(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等“國之重器”搬上了螢幕。
把這一切呈現出來並非易事。
1分鐘左右的實景鏡頭,團隊準備了一年多,實地拍攝花了將近一個月。宋宇瑩解釋,為了匹配球幕劇場的高解析度,團隊成員第一次嘗試用超高解析度進行全景航拍,需要解決很多軟體和硬體上的技術問題。“一方面,我們要等射電望遠鏡的非工作時間去拍;另一方面,還要等個好天兒,而在‘天眼’所在的喀斯特地貌地區,碰上個晴朗的豔陽天還真不是件容易事。”
所有的探索都是為了讓觀眾獲得更加直接的視覺化體驗。隨著公眾科普素養的提高,觀眾有了更高的期待。經常去觀影的天文愛好者們,面對排片表上的節目,總覺得更新太慢,數字工作室時常要面對被“催更”的壓力。
“一部片子要成為精品,需要反覆的打磨,這勢必拉長製作週期。”景海榮說,為了提高影片的上映效率,工作室一般從未立項之前就開始策劃和準備。對於團隊成員們來說,每一次創作都是一次深度的學習。比如,《宇宙大爆炸》從有想法到真正實現,花了將近10年的時間;在漫長的醞釀期,團隊成員時刻關注著國內外宇宙學研究的進展,關注著最新的理論,不停充電。
“天文學是個相對來說比較抽象的學科,我們的目標是找到一些接地氣的點,讓公眾瞭解到天文學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儘量將遙遠的科學翻譯成日常的影象和文字,為大家推開一扇望向太空的大門。”景海榮說。
天文小課堂
★天文館起初是個“電影院”
天文館的英文單詞Planetarium,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天象儀”,所以最早的天文館通常是利用光學天象儀,給觀眾在室內演示天體執行、天象變換,讓大家在白天也能欣賞到燦爛的星空。隨著計算機技術和數字顯示技術的飛速發展,利用計算機陣列對星空進行模擬,同時結合數字投影機的投射,進行模擬星空的演示,越來越受到歡迎。除此之外,由於與天文相關的一些場景展示,通常具有超大場景、寬幅面的特點,為了達到更高的觀看和體驗要求,天文館裡的劇場通常具有多種特效,來模擬宇宙間的多種特殊場景,以達到更好的科普效果。
★三垣二十八宿
中國古人為了認識星辰和觀測天象,將天上的恆星幾個分成一組,每個組合定一個名稱,這樣的恆星組合稱為星官。星官分屬於31個天區,這些天區中的每一個又可看作是一個巨大的複合星座,這就是三垣二十八宿。其中,三垣指的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包括東方青龍七星宿、北方玄武七星宿、西方白虎七星宿、南方朱雀七星宿。
★魚眼鏡頭
球幕影片製作過程中,通常使用等距角魚眼投影方式來實現均勻變形的畫面覆蓋整個球幕,這種畫面稱為魚眼鏡頭。
來源 北京日報 | 記者 牛偉坤
編輯 王瓊
流程編輯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