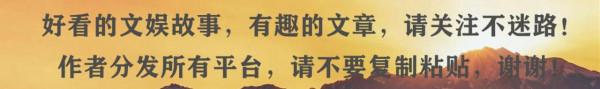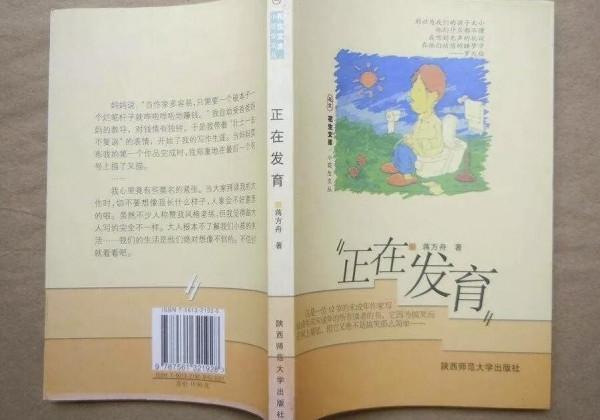文/文刀貳
2021年6月8日,日本外務省官網上,公佈了一份“國際交流基金會”的業務實際評估報告。
報告顯示,在2008年到2016年期間,該基金會曾推出過一個專案,
邀請國內73名個人和71名團體成員赴日考察。
蔣方舟的名字赫然在列,她拿著每個月2萬的資助,在日本旅居一年,並出版了書籍《東京一年》。
她曾經大言不慚表示:“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有人指出,這難道不是拿著日本的錢,替日本寫的“洗白”軟文?
此訊息一出, 瞬間引起軒然大波,蔣方舟也被掛上熱搜,貼上“賣國”、“漢奸”的標籤。
即使她迅速做出回應,表示只是“正常的文化交流”。
無奈,如此蒼白無力的解釋,網友們根本不買賬。
昔日“天才少女”淪落至此,難道真的只是人設崩塌這麼簡單?
這一切的背後又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醜惡?
一、“神童”誕生記
蔣方舟,是個名副其實的“鐵路子弟”。
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樊鐵路醫院,父親是鐵路乘警,母親是鐵路中學的老師。
從小生長在鐵路家屬大院,本該過著平淡生活的她,卻從7歲那年開始走向不平凡的人生。
當同齡人還在享受無憂無慮的童年時,蔣方舟卻開啟了寫作之路。
小學時的她,生活已經變得格外忙碌。
每天放學後到母親任教的學校,去圖書館找一本書,邊等母親下班,邊看完一半。
待到母親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她還要坐在母親的腳踏車後座上接著看完剩餘的部分。
除此之外,她還要每天寫上大約五百字,遇到不認識的字只能查字典,不許用拼音代替。
功夫不負有心人,9歲那年,她終於寫出了散文集《開啟天窗》,此書被湖南省教委定為素質教育推薦讀本。
從此,蔣方舟成了人口中的“天才少女作家”。
也是從這時開始,她便早早失去了放寒暑假的權利。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蔣方舟馬不停蹄地開始籌備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說。
每天凌晨4點起床,眼都沒來得及睜開,便要開始在鍵盤上敲敲打打。
那時,她家裡的條件並不好,三口人擠在30幾平米的一室一廳。
蔣方舟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房間,活動沙發就是她的床,飯桌就是她的書桌。
屋裡隔音不好,外面環境嘈雜,她也只能靠強大的自覺性遮蔽。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只用了4個月時間,蔣方舟便寫出了《正在發育》一書。
書中不乏關於生理期、戀愛、婚姻的內容。
很難想象,一個年僅12歲的小女生,竟然能毫不避諱地談論如此“大尺度”的話題。
於是,蔣方舟被扣上了“早熟”、“叛逆”的帽子。
但這並沒能阻止她繼續前進,一年後蔣方舟接連出了《青春前期》和《都往我這兒看》兩本書。
當時《南方都市報》的副刊編輯給後者寫了序:
“自己努力多年才能稍微領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個十三歲的女生輕易掌握,甚至比自己做得更好,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沮喪的呢?
從2002年開始,蔣方舟成了各大報刊爭搶的香餑餑。
《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海峽都市報》、《足球報》等先後為她開設了專欄。
此時的她已經順利進入湖北襄樊一中,成了一名初中生。
愈發繁重的學業,加上彷彿永遠也寫不完的稿件,讓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為了不耽誤寫作,她甚至想過退學。
好在母親跟老師協調後,讓她獲得了“不用寫作業”的特權。
初中畢業後,蔣方舟進入了湖北最好的中學——華師一附中。
為了讓她能夠更好地創作,學校甚至專門給她配備了一間單人宿舍,還把這裡命名為“蔣方舟創作室”。
不久後,蔣方舟當選為中國少年作家協會主席。
同樣,高中時期的蔣方舟仍然可以不寫作業,一直到高三,她不停地地積累、輸出、變現……不是在寫稿,就是在寫稿的路上。
18歲之前,她接連出版了9本書,包括《正在發育》、《青春前期》、《都往我這兒看》、《邪童正史》等等。
2008年,19歲的蔣方舟被清華大學降60分破格錄取。
同年,廣州《新週刊》向她丟擲橄欖枝,邀請她擔任特約記者。
2010年,蔣方舟升職為該雜誌主筆。
上大學後,蔣方舟開始頻繁出現在各類節目之中。
從訪談類節目《天下女人》,到成為《快樂男生》的跨界評委。
再到近幾年的《圓桌派》、《奇葩說》……
可在這期間,蔣方舟的寫作生涯,卻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
她的作品停留在那本引發爭議的《東京一年》。
隨著時間的推移,“天才”的光環似乎在悄然褪色。
有人開始質疑“神童”的稱號是否摻水,有人預言年少成名的她早晚會跌下神壇。
二、淪為“工具人”
不得不說,幾乎所有能夠被稱為“天才少年”、“天才少女”的孩子背後,都站著一位足夠狠心的“虎媽”或者“狼爸”。
他們兢兢業業培養孩子,對孩子寄予厚望,期待孩子能替自己完成沒來得及實現的夢想。
蔣方舟的母親尚愛蘭便是其中一員。
當初蔣方舟剛剛降臨到這個世界不久,收到的第一份禮物便是來自於母親的嫌棄。
“我媽對我的要求很高,她本來想給我起名叫‘蔣美麗’,但生下我之後,很嫌棄地看了一眼,就放在一旁了。”
以至於每次出門,還要給她臉上蓋塊布來遮“醜”。
從蔣方舟出生開始,母親就擔心她智力有問題。
曾經把她和同一個產房的小孩放在一起,測試他們的反應能力。
結果,別的孩子都挺正常,唯獨蔣方舟“兩眼望天,不動不哭”。
母親頓時心生一股不祥的預感,直到蔣方舟1歲她都在隨時隨地觀察女兒的智力。
身為語文老師的母親,曾經用10分鐘的課間時間,讓蔣方舟做了一套試卷。
還好蔣方舟得了滿分,她瞬間對女兒燃起信心。
為了不讓女兒驕傲,她堅持在別人面前說:“我家孩子笨”。
這樣的打擊式教育,讓蔣方舟在未來很長的時間裡,始終陷入自卑、焦慮中無法脫身。
她曾經自曝“自己是討好型人格”,小時候母親每天會給她2塊錢吃早餐。
但她卻從來不花錢,餓了就去撿教室地上的東西吃。
從同學吃剩的零食,到掉在地上的尺子、橡皮,都成了她充飢的“寶貝”。
就這樣到了小學五年級,有一天她又將別人吐掉的棗核撿起來。
準備吃掉的瞬間,她才意識到“這也太噁心了”。
而她之所以這麼做,不過是為了把早餐錢攢起來,然後得到母親的一句表揚。
年輕時的母親,曾經夢想著成為一名作家,雖然也曾參賽拿過獎,最終卻沒有堅持走下去。
於是,她便想著把女兒培養出作家,來延續自己沒完成的夢想。
在別人家的小朋友還在看卡通繪本的年紀,5歲的蔣方舟便在母親的“精心安排”下,讀起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蔣方舟7歲那年的夏天,尚母親神情嚴肅地給她傳達任務:
每個小學生畢業前,必須出版一本書,不然就會被警察抓走。
擔心言語上的刺激不夠,身為乘警的父親立刻掏出工作時用的手銬,將女兒稚嫩的雙手拷住。
夫妻倆一唱一和,小小的蔣方舟哪裡見過這種仗勢,很快就在恐慌之中信以為真。
在這之後,蔣方舟花了整整8個小時,寫完了一篇600字的文章。
看著不知是害怕還是寫文太難,而哭得淚眼婆娑的女兒,母親輕飄飄吐出一句:“你是天才”。
短短四個字,對於那時的蔣方舟來說,卻彷彿有千斤重。
以至於之後的人生,她都在與“文字”糾纏不清。
後來,蔣方舟出了散文集、小說,積攢了不少人氣,母親則打心底認為寫作比學業重要。
畢竟,僅僅10歲出頭的蔣方舟,光是給《南方都市報》供稿,每個月就能拿到4000元的稿費。
母親總是告訴她,這些錢先幫她存起來。
可慢慢地,她發現這些稿費會時不時變成家裡的某個物件,或許是一部手機,或許是一輛摩托車,甚至是一套新房。
有一段時間,父母甚至雙雙辭職,完全靠蔣方舟的稿費養家。
某天,她聽到父母聊天說:“女兒可不能生病啊。”
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聽到接下來的後半句:“還得還房貸呢……”
上大學後,蔣方舟離開家鄉,獨自來到北京。
但這樣也無法阻止母親對她的“操控”。
兩人每天必須打兩個小時的電話,或者影片三個小時。
對於她和母親這樣的相處模式,蔣方舟是這樣形容的:
“仍然感覺有一個漫長的臍帶,將我們聯絡著,變成一種很討人嫌的依賴的關係。”
大學畢業後,蔣方舟因為工作變得越來越忙,經常需要去外面應酬。
有次回家晚了,母親竟然把自己比作一隻狗:
“一直四腳趴在地上,用頭頂著門,這樣就能第一時間感覺到主人回家了。”
蔣方舟聽完這番話,心疼母親又感到滿滿的無力。
從那之後,她每天都回家吃晚飯,哪怕不知道和母親說什麼,也不再把她一個人留在家裡。
每天早上六七點,母親就會起床,她趁著這段時間去檢視蔣方舟的手機。
每一條訊息、每一個朋友圈都不放過。
彷彿被檢視的不是她的親生女兒,而是正在被審問的罪犯。
從小到大,沒有界限感地干涉和操控,讓蔣方舟成了只需完成母親指令的工具人。
沒有主見、唯唯諾諾,甚至無法抵抗外界的誘惑。
即使成年後,她的內心仍然是個沒長大的孩子;
即使有“天才少女”的光環加持,也難免走上錯誤的道路。
三、人設崩塌
大學四年期間,蔣方舟沒有寫出過一本小說。
只是把一些散文、雜文、時評、書評,集結成《我承認我不曾歷盡滄桑》。
究其原因,她把之歸結為“無法真正地去體驗生活”。
為了擺脫所謂母愛束縛,蔣方舟每天早上8點就去咖啡館,一呆就是一整天。
畢業一年後,她嘗試著寫了一本小說——《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
結果評分慘淡,沒能激起一點水花。
甚至某位出版社主編直言:“放棄吧,你沒有寫小說的天賦。”
消沉了一段時間後,她決定暫時離開這個煩惱之地,去東京旅行一年。
在這期間,她獨自來陌生的國度、陌生的城市,用心欣賞風景、感受生活、思考人生。
一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
有生以來,她終於把自己還給自己,第一次感受到真真實實的生活。
回國後,蔣方舟將在日本的經歷、見聞等等記錄下來,出了一本名為《東京一年》的書。
故事到這裡,女主角“成功擺脫母親操控,走向新生”,美好的結局似乎馬上就要到來。
如果不是那份寫著“蔣方舟”名字的“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名單。
網上一片譁然,等待蔣方舟的則是鋪天蓋地的謾罵。
“拿著日本人的錢,替日本人辦事,還寫了一本吹捧日本的書。”
與此同時,那本《東京一年》的內容,也讓蔣方舟的真實寫作水平再度遭到質疑。
有人說她:“文筆稚嫩,無病呻吟”。
有人說她:“用一年的流水賬賣錢,思考太廉價”。
而真正惹怒眾人,讓蔣方舟陷入“惡評”漩渦的遠不止這些!
還是《東京一年》這本書裡,她描述脫衣舞女的一些不雅行為,
甚至稱讚這是“一種極其嚴肅而又孩童般的行為”,沒有任何淫蕩的意味,而是對女性器官的崇拜。
除卻對“日本興文化”的肆意鼓吹,書中還有這樣一段描述:
在東京的廁所中,馬桶上會有個叫“音姬”的按鈕,在女性方便時可以按下播放流水聲,以此掩蓋尷尬的如廁聲響。
對此,蔣方舟得出的結論是:“東京對單身女性比北京更友好”。
這樣捧一踩一的“精日”言論,想必難逃眾人法眼。
尤其是“網際網路擁有記憶”的今天,即使日後做再多解釋,也無法掩蓋已經發生過的劣行。
輿論愈演愈烈,蔣方舟的黑料也被扒了個徹底。
早在2011年,她還曾在社交平臺涉嫌詆譭軍人。(內容太過不貼完整的)
疫·情期間,一部日本紀錄片中,談及中國的疫·情管控制度,
雖然她沒有明確表明立場,言語間仍然不難讀出她對國內抗疫方式的不滿。
抹黑國內的抗議方式。
稱:“用一種非常時期(指疫·情)的狀態去判斷哪種(制度)好哪種不好,這種思維的武斷本身就是一個挺危險的事情”。
如此模稜兩可的態度,如此明顯的捧殺,蔣方舟的人設算是徹底崩塌。
先不談她是否真的天賦異稟,光是這一點就足夠昔日“才女”跌下神壇。
如果不能明白自己的根在哪裡,自己從哪來成長起來的。
無論什麼天才,都會走向毀滅。
看完記得關注@文刀貳 圖片來源網路 侵刪
往期精彩:“東北醜王”潘長江,再也回不去踏上春晚的風光日子
娛樂圈“四大才子”,誰與爭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