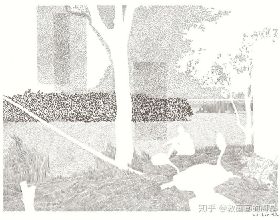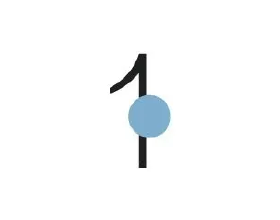托馬斯·莫爾(約1478—1535年)一生中最為傑出的著作《烏托邦》於1516年12月在魯汶印製第一版,次年在巴黎印製第二版。這部著作的成功,確立了莫爾作為人文主義著作家的地位,他也因此被稱為“政治哲學家”。
“烏托邦”(Utopia)是莫爾創造的一個詞語,意為“烏有之地”。《烏托邦》一書的全稱“關於一個最好的國度,關於新發現的烏托邦島嶼”,也表達了“烏托邦”作為“幸福與幸運之地”的寓意。莫爾將烏托邦的地理位置設定在“新世界”的一個島嶼,這是大航海行動衍生的概念。莫爾還塑造了一位大航海時代的傳奇人物拉斐爾·希斯洛德——烏托邦的資訊來源與講述者。拉斐爾出生在大航海行動的發起之地葡萄牙,“為了前往遙遠的國度增長見識,跟隨亞美利哥·韋斯普奇三次航海遠遊”,訪問過烏托邦所在島嶼。雖然拉斐爾·希斯洛德是虛構的人物,《烏托邦》表達的思想卻是莫爾的政治意向與治國理念的真實呈現。
廣義的哲學理念與普遍的哲學教育
烏托邦是一個經歷過民智開啟的文明之地:征服阿布拉克薩島並且將之更名為“烏托邦”的國王烏託帕斯,將島上“粗暴、野蠻的居民改變成為具有良好教養、懂人文學術、待人彬彬有禮的優秀完美之人”。開啟民智的手段是教育,把讀書學習納入烏托邦人的生活方式。
烏托邦的教育分為全民教育與精英教育。普通民眾接受普及型的知識教育,精英階層接受研究型的學術教育,由此形成體力勞作者與智識精英兩個社會等級。
智識精英經歷過“選士養士”制度的篩選與修煉,是智力超群、學養深厚之人。一部分“專注力強、才智超群、天資適宜學術之人”,在孩童時期被甄選出來,作為有潛力的智識精英施以學術教育。成年男女中的優秀者,經過薦舉之後亦有機會增補進入智識精英的行列。烏托邦對智識精英在學術與道德方面有強制要求,未達到預期標準的候選人,淘汰之後退回到體力勞作者行列。在智識與道德方面始終表現優秀之人,“免除一切體力勞動,專注於學術”,傳承烏托邦的價值觀與學術水準,並且承擔起為公眾服務的責任。
烏托邦人對傳統學術存有濃厚興趣,學習“音樂、邏輯、算術、幾何,在這些領域的造詣幾乎趕得上古代哲學家”。烏托邦人“對於星辰的軌跡、天體的執行極為熟悉。他們巧於設計各式儀器,用於精確地觀測太陽和月亮,以及目力所及一切星象的執行與位置”。關於“潮漲潮落,大海的含鹽量,天體與世界的起源和性質”,烏托邦人的某些觀點與古代哲學家相同,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釋。
烏托邦人“收藏有普魯塔克的作品,也欣賞琉善的快樂詼諧”。烏托邦人吟誦詩詞歌賦,阿里斯多芬、荷馬、歐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都儲存有“阿爾都斯小字印刷文字”。烏托邦人閱讀歷史,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撰寫的史學著作都存書在冊。烏托邦人學習醫學,希波克拉底、伽倫的著作都在他們的閱讀範圍之內。拉斐爾在第四次航海遠行時,為烏托邦人帶去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還有泰奧弗拉斯托斯的植物學著作、赫利奧斯與斯科裡德斯編寫的辭典。
莫爾推崇古典希臘哲學,認為優秀的哲學思想存在於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著述之中。對於希臘哲學的熱愛,也傳導給了《烏托邦》塑造的人物。拉斐爾並非僅僅是“帕利努魯斯式的水手”,還是《荷馬史詩》中“英勇善戰、足智多謀的奧德修斯國王”,是“哲學家柏拉圖這位古代智慧的化身”。希臘語是學習古典哲學的必備語言,拉斐爾“雖然學會了拉丁語言,但是在希臘語言的造詣方面更加淵博精深……因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學的學習之中”。烏托邦人“輕而易舉學會了希臘字母,詞語發音清晰,背誦記憶迅速,並且能夠準確無誤地複述”。“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他們掌握了希臘語言,可以流暢地閱讀名家作品”。莫爾並不否定羅馬文明的價值,成就於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與詩人也得到了他的讚許。然而在莫爾心目中,希臘著述的重要性佔據第一位,拉丁著述的重要性位列第二。
莫爾奉行廣義的“哲學”理念,將一切學術都納入“哲學”的範疇,不同學術之間只有自然哲學、政治哲學、倫理哲學之類的區分。依照莫爾的理念,烏托邦是一個哲學的國度,烏托邦的成員都是哲學家。烏託帕斯在“烏托邦”建立伊始將一個“沒有哲學”的蠻荒之地,發展成為“哲學之城”。哲學不僅用來提升烏托邦人的智識與道德水準,塑造正直善良的人格,而且提供治國之道。莫爾持有“哲學治國”的理念:如果哲學家成為國王,或者國王致力於哲學研習,“由此可以帶來完美的幸福快樂”。
烏托邦價值體系的核心:理性
在烏托邦社會執行規則的縱深之處,是以“理性”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理性”的思想動力來自古典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烏托邦是人工設計的社會,“接受什麼、拒絕什麼,都是遵循理性的尺度,理性極大地點燃了人們內心對於神的熱愛與崇拜”。莫爾在哲學的理性之中加入了“從宗教中提取”的原則,堪稱“哲學宗教”。“沒有這些原則,……理性既軟弱又不完善”。宗教原則的基本內容是“靈魂不死”:如果在塵世生活中踐行美德與善行,就可以在未來獲得“用理性加以驗證”的酬報。
私有財產作為傳統社會賴以存在的基本支撐,是烏托邦首先拒絕的因素。“在無島之地建立了一個島嶼”的烏託帕斯國王,“極為厭惡世間的財富”,因而“任何地方都沒有一樣東西是私產,他們每隔十年用抽籤方式調換居家房屋”。烏托邦實行財產共有制度,一切物質與設施在居民中間按需分配。與私有財產一起拒絕的是門閥世族的社會地位,烏托邦不存在財富與門第的世襲繼承。
消滅了私有財產之後,法律對於社會的規範作用微乎其微。在烏托邦,“一切物質由公共享有,每個人都獲得充裕的生活所需”。“賢明並且以聖潔自律的烏托邦人,無須法律就可以使一切充足有序,唯有美德是無價之寶。”當法律的強制作用失去效力以後,人的行為依靠理性加以規範。烏托邦人的生活完美地詮釋了莫爾的理念,相信美好的生活由理性主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友誼、和平之類的美德作為行動準則,人們之間互利互惠互愛,構建起密切和諧的家庭關係與社會關係,管理者無須採取強制手段即可以使各類組織形成有機體。
理想與現實之間:關於“圈地”的批判
莫爾關於理想社會的建構並非憑空設想,而是以現實的關懷為前提。《烏托邦》對圈地引發的社會弊端展開激烈批判:貪婪的土地所有者渴望從羊毛產業中獲取超額收入,透過圈佔土地而實現從糧食種植向牧羊業的轉換,從而剝奪了農民的生計。“貴族、鄉紳、聖潔的修道院長們,不再滿足於一年一次的歲入,……也不再滿足於無利可圖的閒散生活”。他們“把土地全都圈佔成為牧場,推倒房屋、拆毀村鎮,除了用作羊圈的教堂之外沒有留下任何站立的建築”。失去衣食來源的農民由此陷入赤貧狀態,除卻乞討與盜竊之外別無生路。“你們的羊不再是溫順的小型食獸,……而是變成了大型的吞食者。它們是如此狂野,吃光吞盡種田人。它們消耗、摧毀、侵佔成片的田地、房屋、村鎮”。世代耕種土地的農民“被驅趕出熟悉的祖屋,難以找到歇息的地方,……只能以偷盜為生,卻因此而被處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發生在英格蘭的“圈地”界定為資本原始積累的方式之一,莫爾也因為《資本論》關於“羊吃人”言論的引用而成為資本原始積累最初的批判者。作為人文主義學者,莫爾的批判停留在悲天憫人的現象層面,並未達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理論高度。
面對圈地引發的流離失所人口,莫爾認為政府的舉措不僅於事無補,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法庭以絞刑懲治偷盜者,“超越了法律的公正性,對共同體造成了傷害”。“如此恐怖的死刑懲治,難以阻止那些無以為食之人從事偷盜”。“如若擁有其他的謀生辦法,沒有人無奈之下鋌而走險,先是偷盜然後赴死”。莫爾提出:應對圈地弊端的有效辦法不是嚴刑峻法,而是根除私有財產制度。“只要私有財產制度存續,大多數人就難以避免陷入赤貧的悲慘境地”。正是在批判私有財產制度的基礎之上,莫爾為烏托邦設計出“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產品”的經濟制度,藉此實現哲學治國的理想。然而莫爾關於共有經濟只是提出了簡單的設想,缺少系統的理論構建。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之後,研究者回望歷史,將莫爾的設想定義為“烏托邦社會主義”,以此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之一。
莫爾在《烏托邦》中表達的哲學治國理念,借鑑了柏拉圖“公民教育的理性目標”,更是16世紀時代的產物。大航海行動的探險精神,造就了新世界的烏托邦島嶼。文藝復興的人文環境,促成了將廣義的哲學理念用於社會執行的規劃。資本原始積累引發的社會弊端,成就了以共有經濟作為哲學國度物質基礎的思考。莫爾以新時代的思想風貌嘗試“託古改制”,對於烏托邦的社會結構與日常生活“有細緻入微的描述,有巧妙的構圖呈現,閱讀者對此有親臨其境、眼見為實的感覺”。
(作者:劉城,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