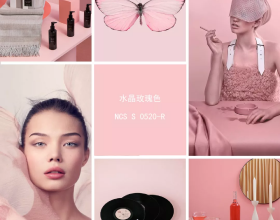秋天,農民用汗水裡演出的一幕劇,天上白雲為幕,“秋老虎”的光線是幕燈,廣闊原野上的大舞臺,風兒伴奏,大豆搖鈴,穀子暢懷,高粱仰嘯,鄉村裡春夏秋冬的音樂劇,秋是最高潮浪漫的樂章。
父親早上起來就給我磨那把打柴火用的舊鐮刀,磨了一會兒後,不時地用刀刃刮一刮小腿肚子的汗毛,試一試刀的鋒刃程度,總是搖著頭。
老隊長又在房後的街上,高一聲低一聲低地上工。父親把鐮刀扔在我面前:“我年輕的時候,割黃豆,後背上放塊磨石,到地頭磨石都一動不動。”
我知道父親在用特有的語言鼓勵我。
這是我中學畢業後,第一次參加生產隊乾的農活:割黃豆。割黃豆的地塊是南大崗子,這塊地黃豆成熟早,長得壯,怕“炸豆”(黃豆收晚了,豆夾自己開裂),男女社員都參加收割。
打頭的領幹活的是個年輕的老莊稼人,外號叫“高粱馬”,是高我幾屆的同學,在學校玩殺“高粱馬”出了名堂,落下這麼一個外號,他沒有念幾年書就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人家是幹莊稼活的料,沒有幾年就當上了“打頭的”了。
一大溜的人陸陸續續來到南大崗子。“高粱馬”哈腰伸鐮刀了。男女社員呼啦啦一字型排開,彎下腰,邁一步,伸一下鐮刀,往後一扯,身後丟下一鋪子黃豆。五百多米長的一節地,挨我壟的“馮大煙袋”一袋煙還沒有抽完,他就先到地頭,落下我有幾鋤槓遠。我也挺不服氣,緊忙火,呼哧帶喘,也割到了地頭。“馮大煙袋”一點也看不出累的樣子,好像剛做了舒筋活血的運動,舒服極了。我的腰抬不起來了,喊腰疼,他邊往鞋底上磕菸袋灰,邊諷刺我:“這麼點小歲數就長腰芽了?”
地頭上,男女社員一片笑聲,跟大豆搖鈴一樣。“高粱馬”又往回拿第二壟,大家還是蜂擁而跟著,好像有獎金一樣。女社員沒有一個跟不上趟的,特別是那位俊模樣的婦女隊長“耿五丫子”,割地跟她在屯裡宣傳隊唱歌跳舞一樣,隨隨便便、輕輕鬆鬆、自由自在,活潑、飄逸。
男女搭配幹活不累,不知道“高粱馬”今天非常興奮,有意讓女社員見見他的陽剛之氣,竟然忘記了歇氣。氣得爛眼邊的二舅媽喊了起來:“‘高粱馬’你想累死老孃啊,褲襠裡都抓蛤蟆了......”
終於到地頭了,開始歇氣。婦女們一溜煙兒地跑到大下坡,找個壕溝去方便。男人則背過臉去,擰開“水龍頭”放水。幾個小年輕的撿一根硬棍子,在地上畫棋盤,開始“下五道”,一幫“煙鬼”卷著葉子菸過煙癮。
不一會兒,婦女們吵吵巴火陸陸續續回來,她們把鐮刀扔給自家的老爺們或者父親、哥哥,讓他們幫磨刀。黃豆這莊稼有木材質地,費刀,割幾壟就需要磨刀。
頭一次割地,沒有經驗,連磨石都忘記帶了。我湊到“馮大煙袋”跟前:“姐夫,幫我磨磨唄!”
我和他有“八杆子可以扒拉到的親戚”,一聲姐夫叫著,他很高興,拿過我的鐮刀看了看,馬上撇在一邊:“你這不是扯蛋玩嗎?你這刀,騎八里地都不帶鏟屁股的,還割黃豆,我看看你的手......”
我才想起來,摘下被黃豆角扎破了手套:哇!握刀的手掌上起了幾個大血泡,另一隻手紅腫起來,開始有了疼痛感。
我沒有生氣,撿回鐮刀,“姐夫、姐夫”一個勁叫他,商量他幫我磨刀。我不能幹了一氣活就歇工啊,況且,工分是農民的小命根,下莊稼地,就得幹這種活。想起家裡每年分紅的時候都“漲肚”(分紅的時候,領不到錢,給生產隊倒找錢),低三下四求人給擔保的情景,又上了壟。
歇過氣,別人有了精神頭,如加了油一樣,我卻疲勞得厲害,沒有了之前的衝勁,不一會兒,就讓大家拉下幾十米。
割地跟運動會跑萬米一樣,幾個人飆著勁,不容易落下,而一旦落下了,就不好攆上。前面的人越隔越遠,我成了打“狼”的,這臉面真掛不住啊,光是男勞力還行,還有隊上姑娘媳婦、大姨二孃,多丟人。心想,那幫姑娘,看我幹活這個熊樣,說什麼也不會嫁給我的。越想越上火,倒黴的事也攤上了,一鐮刀下去,黃豆沒有割到,割到了自己的小腿。多虧,沒有用上勁,割破了外皮。
“高粱馬”和“馮大煙袋”到地頭了,我還在“長征”的路上。這個時候,恨不得有個地縫都能夠鑽進去,但沒有地縫,抬起頭來,看見一個人正在接我的壟,看清楚了:是婦女隊長“耿五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