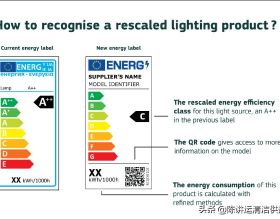他是一棵“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唐·李白《南軒松》)的大樹,但他又是一株“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宋·曾鞏《城南》)的小草。身為建立殊勳的偉岸大樹,甘做謙遜下士的平凡小草,他就是一生跨過三個朝代的傳奇人物程思遠。
說他是大樹,因為被譽為“國共兩黨關係史的風雲人物”的程思遠,以其參加北伐和抗日戰爭、尤其在臺兒莊血戰中立下汗馬功勞;以及遵周恩來總理之重託,從香港五上北京、兩赴瑞士,促使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回國。程老譜寫了百年傳奇,締造了一生偉業。
還在中學時代時,沒有任何背景的賓陽農家子弟程思遠,聽說北伐軍李宗仁部招考文書,便揹著一袋米趕去應考,並因文筆優美“狀元及第”。從此他投筆從戎,追隨李宗仁鞍前馬後,親歷了許多歷史事件,逐步成為桂系的核心人物。他捭闔縱橫於蔣介石、李宗仁之間,參與籌劃了反蔣助李競選“副總統”、逼蔣下野、與共產黨和談等大事。在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間,經他牽線搭橋,在周總理的周密安排下,巧妙地避開一切艱難險阻,又與李宗仁一起從海外歸來。
說他是小草,因為曾連任三屆副國級的政界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活動家程思遠,一以貫之把自己看做一介平民。他一生拒配秘書,警衛也是後來勉強接受的,寧願讓備受周總理讚譽的傑出女性、他的賢內助石泓脫產做助手(據我所知,還有兩位不要秘書的副國級領導人是王崑崙、雷潔瓊),而且凡應他信任的朋友之邀參加活動,只需一個電話,就在石泓陪伴下悄然前往,甚至離京外出也不驚動國務院事務管理局。
我是在1989年剛接任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總經理時認識程老的,當時我正在考慮聘請幾位德高望重、深孚眾望的統戰、外事、文化界的前輩作顧問,支援和指導我的工作,恰好在一次活動中與程老及石泓見面共餐。初次結識程老,留下的印象是感動和震撼:一位在當年叱詫風雲、今天依然位居高位的傳奇人物,竟是如此質樸、平和、親切和熱情,而石泓也是那麼平易近人。
我也因此少了許多顧忌,得寸進尺地邀請他們參加我們公司的活動。一回生兩回熟,我不禁萌生了請程老擔任公司總顧問的想法。同事們聽了我的想法都啞然失笑:一座簡陋的小廟,怎麼能請得動大菩薩?這豈非異想天開。然而結果使所有人都跌破眼鏡,程老居然答應了!程老的答覆是由石泓轉告我的,我在接電話的時候,心裡充滿了激動和感謝,程老和石泓真不愧是出版工作者的知音。
有了一位高名重的程老任總顧問,公司的知名度提高了,也使我們接待來訪的港臺和海外貴賓,多了一棵拔地參天的大樹作靠山。程老的作風敦本務實,應諾的事從不虛與委蛇,儘管身兼許多要職的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滿而又滿,但對我們小社之事卻是甚為關切和注重,只要可能就一定慨然接受我的邀請,滿臉春風地以總顧問的身份出席活動。每逢我們的涉外活動和書刊出版發行、書畫展覽盛事,程老尤為重視,總是推辭了其他邀請,偕同石泓準時前來參加,使我們的活動蓬蓽生輝。
一次四位著名的美籍華人教授潘毓剛、聶華桐、吳京生、李天和來公司訪問,我請程老前來與他們見面,不巧與他必須參加的另一個重要活動撞了車。然而令我沒有想到的是,正當四位教授在會議室與我們座談時,程老高聲地打著招呼進來了。原來老人家是提前離開了那個活動,特地趕到我們公司來的。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與香港星島報業集團合資創辦《星光》月刊,是我國新聞出版界中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空前絕後的)中外合資專案。對於這件大事,程老予以特別關注和熱情支援,參加了歡迎星島集團董事長鬍仙率團訪華的宴會以及雙方簽約等一系列重要活動。賴有“總顧問”程老的出面,使傲慢的“報業大王”胡仙也不由得對我們公司刮目相看。
我和程老、石泓很快成了忘年交,不管他們家在東單11條還是搬到東總布衚衕,我一直是他們家的熟人常客,他們的家也成了程老會見應我邀請來京的海內外客人的貴賓室。他們從來沒有從我們公司取得分文回報,但有時還要自己破費來招待我帶去造訪的客人。
一次石泓問我:“謝總,你受不少人所託請程老題詞,怎麼沒請程老為你自己題詞留念呢?”我答道:“我覺得受人所託是光明磊落,為自己提要求好像是出於私心了。”石泓說:“我看你也不必多慮了,趁現在程老身體還健,寫字靈便,我叫他抓緊給你寫一幅吧。”石泓的關心令我十分感動,也正是這次問話後,使我留下了程思遠的一幅珍貴題詞。
為傳奇人物程思遠出一本傳記,一直是我的願望。當我向程老披露心聲時,程老、石泓都一致贊同,並表示將《程思遠傳》的中文簡體字、繁體字的版權無償地給我。程老希望這本傳記由我自己執筆,他說能否趁他們去北戴河休假的機會,我可以與他們住在一起,朝夕相處以便了解他複雜曲折的人生經歷。然而因工作太忙而席不暇暖的我,哪裡能外出個把月的時間呢?我只好惋惜地辭謝了程老的好意,推薦新華社我的朋友薛建華來完成這部傳記作品。
令我十分感動和一生引以為榮的是,程老在《程思遠傳》的“序”中寫道:“至友謝善驍兄久欲我寫一本自傳,將自身經驗,公於世人……”。一位長者、國家領導人,對我這個學生、小民、晚輩稱為“至友”,不僅使我深感愧不敢當,連我的朋友也都很驚訝。然而,只有真正瞭解程老的人方能理解,他是被載於史冊的一棵大樹,卻把自己看做人間的一株小草——這就是程老的為人!
在《程思遠傳》簡體字版出版後,雲南省領導希望將首發式放到昆明舉行,並邀請程老到他的兒女親家、國民黨雲南省主席龍雲的當年領地故地重遊,程老和石泓均表同意。程思遠、石泓夫婦在我陪同下去雲南昆明參加《程思遠傳》首發式。這是程老又一次“私出皇城”的行為。前一次是應紹興市政府透過我邀請,程老在紹興駐京辦主任李春林陪同下前去我家鄉訪問,石泓因事沒有同行,連我自己也因走不開而沒有隨行。程老並不認為他是“國家領導人”,又因是我私人邀請,離京外出總是輕車簡從,自由自在,無需按“規定”麻煩有關部門安排一群人“保駕護送”。
首發式當天早上,石泓告訴我,程老因高原反應而頭暈,無法到會了。對此大家都很緊張,因為程老是未經請示私自外出的,一旦身體出點差錯,我和有關方面都罪莫大焉,因此請石泓回賓館多加照顧。首發式正待開始,人們驚奇地發現程老在石泓的攙扶下步入會場。那天程老不僅抱病準時到會,而且按預定的議程在會上講了話。
1999年3月26日,與程老相濡以沫半世紀的石泓,在北京協和醫院與世長逝。在其後的一段日子裡,程老浸沉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正好此時深圳一家公司透過我邀請他為當地第一高樓落成剪綵,經我與其小女兒程華商量,認為與其在家裡睹物生情懷念老伴,莫如暫離北京到外地散心。經程老同意後,這次出行不得不上報國務院事務管理局批准,國管局遂派出一群工作人員隨行,這支連家屬在內的隊伍人數多達十七八人。對此程老皺起了眉頭,他覺得那麼多人,光是機票就要一筆不菲的費用,因此堅持不乘飛機改坐火車,國管局陪行人員最後也不得不遵從他的要求。其實這種排場是不得已而為之,非程老本人的意願。
香港迴歸前夕,我準備在我任社長的香港中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為《程思遠傳》出繁體字版,董事長曾守雄也完全贊同。我擬以我的名義為此書海外版寫一篇“前言”,就請教程老,應從哪一角度做這篇文章,沒想到得到程老的回答是:讓我給你起草吧!程老真的做了一次我的“秘書”,代我寫了這篇“前言”,以我的名字發表在繁體字版《程思遠傳》上。
我一直珍藏著的另一篇程思遠親筆寫的手稿,是他在1999年8月4日從北戴河寫給我的一封長信,並特地叫工作人員小楊送交到我手上。老人家在信中以其慣有的謙虛口吻向我表達了一個強烈的願望:
弟現在北戴河休息,除下海游泳外,正在寫一部《世紀風雲錄》或《百年大事記》,特請教於老友之前,乞予以協助,指示如何出版。竊以當此世紀之交,吾人應當回眸百年,加以總結……我寫此書,實為晚年逢盛世,不能漠然無動於衷,執筆直書,悉本存真求實。下月中返京時,擬將已寫的草稿請您看了,徵求尊見,以求完善。
當我讀完這封信後,不禁潸然淚下。一位為國立下大功的耄耋老人,念念不忘的是在世紀之交之際,總結百年曆史,對照新舊時代,敘述親身經歷,教育年輕一代。的確,這篇大文章,也只有程思遠這位20世紀的風雲人物,才有資格、有資本來做。我給程思遠回了信,一定支援和協助他寫好出好這本世紀寶書。但此後我再無接到他的迴音,後來我才知道,他被送進了北京醫院,這也許是程老生前寫的最後一封信了。
程老住院期間,我已預感到老人家可能很難再返回到東總布衚衕的家了,因此多次要求去醫院看望,以表達十餘年來他給予我無比關懷和支援的感謝之情。工作人員小楊也知道我希冀與程老訣別的心情,但遵照醫囑,還是客氣地予以婉辭。
2005年7月的一天晚上,當我開啟央視的新聞聯播時,看到電視畫面上出現了十分熟悉的程老像,同時聽到播音員那沉重的聲調:“著名的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第八、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程思遠同志,因病於2005年7月28日19時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聽到這裡,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當晚我和淚在燈下寫下一首悼詩:
百年傳奇一生偉,忠魂直上封神臺。
北伐征途抗日路,時代精英黨國才。
五上北京傳佳話,兩赴瑞士留豐碑。
但憾不見九州同,殷殷遺願託後輩。
程老沒有等到《世紀風雲錄》完成和出版的那一天,沒有等到親自飛赴臺灣的那一天。
然而程老不應該感到遺憾了,回首往事,“五上北京傳佳話,兩赴瑞士留豐碑”,他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重大使命;無怨無悔,“北伐征途抗日路,時代精英黨國才”,他以自己傳奇的一生向祖國母親交出了一篇完美的答卷。
身為大樹卻終生不忘小草的初心,在當今經濟大潮的席捲中,這樣的弄潮兒不要說在黨外,在黨內還剩幾何?
在參加八寶山殯儀館的追悼會上,我深深地向程老遺體三鞠躬,默默地祝願老人家一路走好。我喃喃地對程老說:“程老!晚輩、學生謝善驍永遠懷念您!您是我一生的師長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