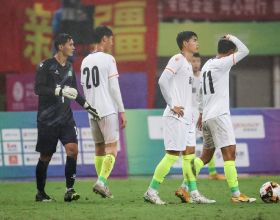顧命大臣的設立本是為了輔佐新帝處理朝政、維護政局穩定。但新君即位伊始,顧命大臣甫一擺脫先皇威壓,往往一改往日謹慎之態,他們仗著前朝重臣、新朝顧命的身份,擴張權利、行為張狂肆意,對皇權產生威脅,“鹹有輕新主之意,甚有朋黨之嫌”。
前廢帝朝,執政大臣劉義恭等人與皇帝發生權力鬥爭的首要原因是執政大臣大肆攬權對皇權產生了威脅。
孝武帝去世後,從這3方面來看執政大臣對皇權的威脅有多大?
- 首先,前廢帝初登基,處於“諒闇”期,不能親自理政。
古代先皇駕崩、新帝繼位後,須有一段時間的“諒闇”期。《論語》記載子張問孔子:“書雲:‘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回答說:“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高宗即商王武丁,“諒陰”即上文中的“亮陰”,也同“諒闇”,孔子進一步解釋新帝“諒闇”期“三年不言”,是指委政於冢宰。
由於三年時間過長,在後世發展中,“諒闇”時間逐漸縮短,但並沒有取消。在“諒闇”期內新帝不能正式親政,而是委政宰輔。
劉宋立國後,新帝“諒闇”期不親政的例子依然存在。
永初三年五月,宋武帝劉裕駕崩,皇太子劉義符即日繼位,他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未親政事。景平元年四月,顧命大臣徐羨之等在上呈少帝的奏表中稱“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元嘉七年劉宋發兵北討,統帥長沙王劉義欣釋出的檄書中也回顧了武帝劉裕去世後“中葉諒闇,委政冢宰”的事實;景平二年範泰上書時仍說:“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
這些記載表明:第一,新帝諒闇期不親政事;第二,新帝不親政期間委政宰輔,具體到少帝時期則是委政於顧命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前廢帝繼位後,同樣處於諒闇期且遵循不親政之制,前廢帝始繼位,就下詔“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將朝政大事交給劉義恭、柳元景處理。
蔡興宗也曾在朝廷直言:“主上諒闇,不親萬機。”可見,前廢帝不親政事在朝中是公開的,為朝臣所共知;前廢帝誅殺戴法興後,敕巢尚之曰:“吾今自親攬萬機,留心庶事”。可知從戴法興被殺開始,前廢帝才有機會開始親政。“(前)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顏)師伯為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
前廢帝取締顏師伯尚書僕射之職,又以王景文為尚書右僕射分割其權力,這說明由於尚書僕射顏師伯的掣肘,前廢帝殺掉戴法興後依然不能完全控制朝政大權,進一步證明在此之前前廢帝的確沒有親政。因此那些對於顧命大臣的調任決定應當不是前廢帝親自做出的。
此外,即便前廢帝有機會親政,他也應當不會做出這些調任的決定。
一方面,孝武帝以遺詔形式任命顧命大臣,這是先皇下給新帝的詔書,新帝如果輕易將顧命大臣改任,是違背孝武帝旨意的行為,有違孝道。另一方面,改任顧命大臣的舉措並不符合前廢帝的利益需求。
首先,自東晉以來錄尚書事權力極大,劉宋元嘉時期,劉義康任錄尚書事,幾乎能夠代替皇帝決定朝政大事。劉義康的勢力逐漸威脅到皇權,與宋文帝發生權力衝突最終被宋文帝殺害,此後皇帝開始限制錄尚書事的權力。到孝建元年,錄尚書事一職被孝武帝廢除,徹底清除這一威脅皇權的心腹大患。因此,劉子業斷不會恢復這樣一個可能會威脅到自己權力的職位。
其二,以顏師伯為尚書僕射,同樣不符合前廢帝的利益。按照孝武帝的安排,尚書右僕射顏師伯主要負責尚書中事,其權力相當之大,但因職位低於尚書令柳元景與尚書左僕射劉遵考,受到此二人的制衡可以避免其專權。此時將顏師伯任命為尚書僕射,破壞了孝武帝分置二僕射分權制衡的安排,使顏師伯的權力進一步擴大,這對皇帝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其三,以領軍將軍王玄謨出任青、冀二州刺史,對前廢帝而言依然沒有益處。領軍將軍是護衛皇帝安全的最高禁衛武官,而王玄謨曾多年在外征戰,有相當豐富的一線作戰經驗,是擔任此職位的極好人選。同時,王玄謨性格嚴直,又曾與柳元景有過矛盾,在柳元景、劉義恭、顏師伯業已結黨的情況下,王玄謨是可以牽制他們的重要力量,前廢帝怎麼會主動將這樣一個助力推開呢?
綜上可以推斷,對劉義恭、顏師伯的升任命令應當不是前廢帝作出的,而是來自新帝諒闇期間執政的宰輔之臣劉義恭、柳元景和顏師伯。劉義恭等人不僅透過遷職增進自己的權力,還拉攏了孝武帝倖臣戴法興與他們合作,極大地威脅到了前廢帝的權力。
前廢帝親政後,“欲有所為,(戴)法興每相禁制”,戴法興敢於制止甚至控制前廢帝,除了其長期以來作為孝武帝舊臣對前廢帝形成的習慣性威壓外,還有執政大臣劉義恭等人在背後的支援。執政大臣權力擴大,甚至還有新帝身邊的戴法興這樣既諳熟朝政大事處理又能對前廢帝進行掣肘的皇帝近臣作為幫手,怎麼能不讓前廢帝感到威脅進而與執政大臣產生矛盾呢?
- 除了執政大臣權力擴張本身對皇權帶來的威脅外,執政大臣行事張狂、肆無忌憚的作風也使前廢帝的危機感加重。
孝武帝在世時,大臣們畏其嚴暴,莫不戰戰兢兢,不敢私自交往,唯恐被本性猜忌的孝武帝懷疑。但是大臣們的畏服只是他們為了保住身家性命、高官厚祿的措施,未必是真心忠誠於孝武帝,從劉義恭等執政大臣對孝武帝的態度及在孝武帝去世後的行為來看,他們對孝武帝的畏懼顯然大於對他的忠誠。
孝武帝個性嚴暴多疑,不僅權不外假、對大臣們多加提防,而且用侮辱臣下的方式壓制他們。
“孝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顏師伯缺少牙齒,被孝武帝稱為“齴”;王玄謨因晚渡北人身份被稱為“老傖”;孝武帝不僅私下這樣稱呼他們,“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在公開場合也以帶有侮辱性的外號稱呼,這對臣子來說是極大的侮辱。
此外,孝武帝還讓侍從杖擊大臣,群臣自柳元景以下都受過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酷刑。蔡興宗個性方嚴,不接受孝武帝的戲辱,顏師伯羨慕地說:“蔡尚書常免暱戲,去人實遠”。顏師伯自嘆不及蔡興宗,從側面說明顏師伯雖然迫於孝武帝權威不敢有怨言,但也對孝武帝的侮辱行為多有不滿。
孝武帝去世後,劉義恭、柳元景等激動地說:“今日始免橫死”,他們一改在孝武帝時期小心恭謹的態度,與顏師伯等朝臣遊玩作樂、歡飲達旦,表現出與孝武帝時期完全不同的放肆作風,這一方面說明他們擺脫孝武帝壓制後本性暴露,同時也證明權勢的滋長讓他們並不將新君放在眼中。此時的執政大臣們不僅行為作風肆意張狂,還在朝政大事上背棄孝武帝的旨意。
- 除了提到的違背孝武帝的心意、重置錄尚書事,他們還全面推翻了孝武帝時期的諸多政令。
大明八年(464 年)七月,“罷南北二馳道。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此時距離孝武帝駕崩僅一個多月,執政大臣們就將孝武帝的政令通通廢黜,以至於吏部尚書蔡興宗慨嘆:“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可見在當時朝臣的眼中,執政大臣們這種不論是非完全廢黜先帝政令的做法也是極其令人側目的。
執政大臣還公然與孝武帝的政敵來往,“(劉)義恭與義陽等諸王,(柳)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義陽”即義陽王劉昶,是宋文帝第九子,孝武帝在位時,劉昶就因“不能祗事世祖”,常常受到孝武帝的責難和猜疑。
作為顧命大臣,劉義恭等本該是孝武帝的代言人,此時卻與對孝武帝一向不敬的劉昶密切往來、毫不避諱,可見他們行事之張狂無忌。劉義恭等執政大臣們在先帝新喪時就迫不及待地罷黜孝武帝諸多施政舉措,公然與孝武帝政敵密切往來,這對孝武帝來說是極大的不尊重。
執政大臣這種肆無忌憚的行為顯示出他們“踐冰之慮已除”後再無後顧之憂的張狂,也是他們掌握朝政大權後目中無人的表徵。景和元年八月前廢帝誅殺劉義恭等人當月,又“復立南北二馳道”、以沈慶之為太尉、恢復王玄謨領軍將軍之職。可知前廢帝部分地恢復了孝武帝的政令,顯然他對執政大臣全然推翻孝武帝的政令也有所不滿。
執政大臣們侵犯先帝權威、輕視新帝,他們張狂的態度和做法使前廢帝的危機感進一步加重。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執政大臣是否真的有意圖侵奪新帝的權力,都會引起前廢帝的警覺、進而引起前廢帝與執政大臣的權力之爭。
前廢帝經常讓他的親信宦官華願兒出入民間“查聽風謠”,華願兒回稟稱:“外間雲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戴)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等語,“帝遂發怒”。不久戴法興被殺,劉義恭、柳元景、顏師伯等密謀廢立,前廢帝與執政大臣的權力鬥爭達到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