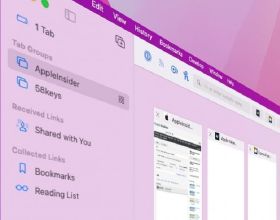五叔去世三十年了,他住的老屋還在,只不過滿目荒蕪。每次回鄉,我都要到五叔的老屋去看看,回憶五叔在世時的一幕一幕。
我記事兒時,五叔身材矮小,說話卻大嗓門。每天都穿著草綠色的軍裝,扛著一杆獵槍。五叔是村裡的民兵連長。
這個民兵連長當時在我幼小的心裡感覺就像小兵張嘎中的羅金寶那麼威風。
五叔平時很少有時間呆在家裡,他不是在大隊部待著就是帶著我去野外轉悠打野鴨子,每次都能打到三隻五隻。他從來不吃打到的獵物,都是送到大隊部。
我10歲那年秋天,生產隊幾十畝地的玉米被野豬拱的天翻地覆,玉米棒子都被野豬啃食乾淨。
五叔自告奮勇去值夜班看護玉米,他問我敢不敢去?我倔強地說男子漢怕什麼!
我爹和娘誰也不讓去,後來我爹說他也去。就這樣這天傍晚,我們三個人帶著我家大黃和黑子,就來到了村西5裡外的山根地。那裡有個小土房裡面有個小火炕能睡下三個人。
五叔和爹把被子放在土炕上,弄來燒柴點著火炕,以便晚上冷。
我則在炕上開啟收音機,聽劉蘭芳講岳家將。
我爹抽著紙菸和五叔聊著天,他們聊了好久。
我聽過小說後有些困頓,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睡夢中我就隱約聽到大黃和黑子的狂咬聲,我一摸爹和五叔都不在。我馬上意識到野豬來了。
我急忙穿上鞋子,拿著手電出去順著聲音和亮光跑過去。
只見不遠處月光下,爹拿著大斧子蹲在地上,五叔正端著槍朝著黑乎乎來回亂竄的動物射擊。
我剛想用手電照,我爹急忙按下我,把手電關掉。
突然一團黑乎乎的東西滾動過來,爹拿手電一照,是一頭大野豬挺著獠牙瞪著綠瑩瑩的眼珠子衝了過來。大黃和黑子也跟著跑過來圍著這隻野豬瘋狂的進攻。
五叔急忙掉過槍口看準大黃和黑子躲閃的空檔,連續幾個點射,這個大野豬一下子四爪側翻倒在地上,不遠處滾滾而動的幾團黑影向遠處逃竄,大黃和黑子奔跑過去追,被五叔吆喝一聲,都跑了回來。
過了不大一會村裡不少人拿著手電跑了過來,都對五叔豎起大拇指,五叔咧著嘴樂。
大夥兒用繩子捆好已經斃命的野豬,抬著回了村。我和爹也跟村裡人一起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們班級都沸騰了,都圍著我讓我講五叔打野豬的故事。我很自豪地跟他們講,好像那野豬是我打死的。不久我就敢跟著五叔進山打獵了。
我十五歲那年冬天,我和五叔遭遇奇獵,五叔突然瘋掉,被自己家一把大火,結束了打獵的一生。
那年冬天,我剛放完寒假的第二天,雪下得好大好大,走在村裡,雪都到了膝蓋。雪停了以後,颳起了冒煙炮。
這時候,也是黑龍江最冷的時候。
五叔帶上乾糧扛著槍,要去山上打獵。我哭著也要去,爹拗不過我,就問五叔去哪裡?遠不遠?五叔說,不遠到西大崗。爹說那行,幾里地你們去去就回來。
娘給我穿好棉衣棉鞋戴好棉帽子,又找了一雙棉烏拉鞋,給我和五叔烙了幾張蔥花餅。
我和五叔就上路了,往山裡的路越來越不好走。起初還有車轍印,雪還淺些,越往山裡走,雪越厚。我和五叔氣喘吁吁地轉過一個山灣,就看不到村子了。
我倆進到樹林,看到灌木叢裡有一溜動物蹚出的腳印。五叔告訴我這個趟子印兒是兔子雪下大了沒吃得出來覓食了。
我說咱跟著打嗎?
五叔樂了,你得有點格局,這麼小的東西咱們不打,留著你大山哥下套子吧。咱們往前走,不遠就能看到大傢伙。
我的眼光一下子就亮起來,渾身就打了雞血。
我們繼續往前走,我們在山裡的雪地裡艱難地行走著。可以說用連滾帶爬來形容了。因為用力從雪地裡拔出這隻腳,那隻腳又深深地扎進齊腰深的雪地中。我們走過的地方拖出來的,就像一條彎彎扭扭的戰壕。
我身上開始出汗了,貼在我胸口的白麵蔥花餅還熱乎著。我感覺有娘真好,五叔沒有娘,帶的肯定就是玉米麵窩窩頭。
我倆走著走著,日頭有點偏西了。
五叔在一棵白樺樹下停下來,用腳清理樹下積雪,弄出一塊空地,在樹上折一些樹枝,又去樹林扛回幾棵楊木枯樹。在白樺樹上揭下一塊樹皮,他用火機點著後,放在堆好的柴垛中,接著熊熊火苗隨著風勢越來越高。
樹下溫暖起來,我知道要吃飯了。我把蔥油餅從懷裡取出來遞給五叔。
他搖搖腦袋,拿出玉米窩窩頭就往嘴裡塞。
我一把搶過窩窩頭,把手中的餅塞給他,說,餅是我娘給咱倆烙的,就得咱倆吃。
五叔知道我的倔強,他把用塑膠袋包著的芥菜鹹疙瘩,遞給我一個。我一口餅一口鹹菜吃得很香。那一頓飯沒成想成了我和五叔最後一頓飯。
吃飽後我抓過幾把雪按在嘴裡,一會兒就化成水,涼涼的嚥下,潤進肚子裡很是愜意。
五叔看著我吃飽後,他也站起身來,把沒有吃的窩窩頭放在包裹裡纏在了腰間。
五叔彎腰拿起槍。我聽到對面的樹林中有響聲,抬頭看是一隻馬鹿正站在不遠處的雪地裡,向我們這個方向張望。
遠遠看去,黃色的脊背,脖子下還有一團團的白毛,它沒有犄角。
五叔做了個噤聲的手勢。他慢慢地舉起獵槍瞄準,就在馬鹿察覺到要遭遇不測要跑的時刻,槍聲響了,對面雪地的馬鹿卻不見了蹤影。
我看了看五叔。只見五叔背上槍,對我說快過去看看。
等我倆跑過去看的時候,幾十米外的雪地上有一趟馬鹿的腳印外,還有幾處鮮紅的血跡,順著馬鹿的走過的印跡一直灑下遠處。
五叔說追!我跟在五叔的後面順著那個血跡往前方追趕。
我們追出去很遠。我覺得很累。五叔說到前邊休息下。等我們走到前邊,一看那個白樺樹就是我們吃中午飯的地方。
我疑惑地問五叔,我們又回來了?
五叔沒有說話,休息時候五叔抽了三袋煙的功夫。我們又起身去追,等累了要休息時,又回到中午吃飯時的白樺樹下。
五叔說壞了,咱爺倆迷路了。我忐忑地問咋辦?
五叔沒回答我,而是用拳頭使勁在一棵粗大的柞樹上擂了三拳,喊道,山神爺老把頭,是俺多有得罪,放俺侄子一條生路,來日定殺豬宰羊厚謝!五叔喊完,趴在地上磕了三個頭。隨後站起身擺了個手勢。
我跟在五叔身後轉了好大一圈,隱隱約約地看到遠處冒著裊裊炊煙的村子,我的心頭一下子就亮堂起來,回到村子後,五叔沒有到我家而是回了自己的家。
第二天早上五叔叫來好幾個村裡號稱山仙的劉大爺,還有幾個棒小夥子。說是去山裡找昨天受傷的鹿,我說我也去。五叔沒有反對,爹孃也沒有阻攔。
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進到山裡,走了好長時間。在大山狹長的溝叉子裡石頭叢林一個石洞前找到了躺在草地上的那隻鹿,睜著的眼睛已經沒了光澤,看來這隻鹿因為傷勢過重而死亡了。
五叔沒有說話,幾個人圍在死鹿的周圍準備抬走。只見在不遠處站著一隻小鹿,往這邊看。
劉大爺讓大家都退開,只見小鹿亦步亦趨的走到大鹿的跟前,用嘴去拱,然後在大鹿的身邊來回轉悠咩咩的叫著,聲音像極了孩子的哭聲。
這時五叔從雪地裡一躍而起猛然摘掉頭上的棉帽子,脫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去脫自己的棉褲,哈哈哈哈地笑著,那笑聲比哭聲還慘。
劉大爺急忙過去按住五叔,其他人七手八腳的把五叔的棉衣服給他套上。劉大爺就把那根用來抬鹿用的繩子給五叔綁上,眾人沒有顧上那隻死去的大鹿。把突然瘋掉的五叔抬了回來,抬到我家我爹急忙去找村醫。
村醫看過說是受了刺激精神錯亂了。
同村小夥伴有的說五叔撞了山神,有的說五叔打的那隻鹿已經成精來報復,有的說五叔殺生太多遭到報應。
五叔本來很乾淨的屋子到處是破爛的衣服,屋子的角落裡到處是垃圾,爛掉的白菜葉子和土豆圍在黑漆漆的灶鍋一圈。
五叔每天懷裡抱著一個木頭棍子,有時蹲在牆角嘿嘿傻笑,有時端著木棍當槍瞄準。
臘月小年二十三那天夜裡,五叔家的房子衝起漫天大火,當鄉親拎著水桶鍋碗瓢盆把火就滅後,五叔的家房子已經只剩四堵牆壁了,五叔也被燒成了黑炭,蜷縮在角落裡。
五叔去世不長時間,我問我爹,五叔為什麼會得瘋病,爹告訴我,五叔曾經有過老婆和孩子。孩子還沒滿一歲時,五嬸因為第二胎難產死在家裡炕上,大孩子不知道媽媽死了,還拱在媽媽懷裡要奶吃,大孩子吃不到奶就爬,爬到火炕邊上,頭朝下摔到地上也跟他媽媽一起走了。
爹說,你五叔一輩子殺孽太重,弄得一家人都不得善終。
五叔離開的三十年,爹的話在我耳邊縈繞了三十年。今天我更加覺得眾生平等,誰也沒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利,動物也一樣。
和諧相處,珍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