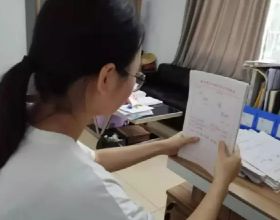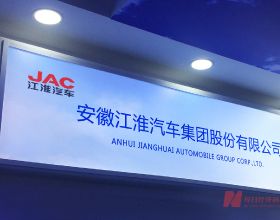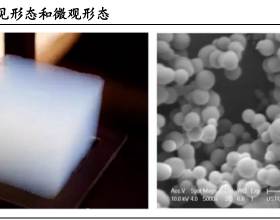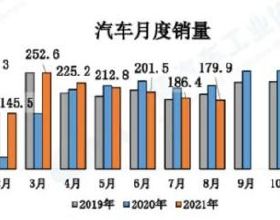作者:周繼志
養豬吃肉。周家埡的肉食來源,通常靠自家餵養年豬來解決。一般一戶人家養兩頭豬,一隻賣掉換錢,另一隻殺了做年豬。
養兩頭豬的習慣,可能與計劃經濟年代每家每戶要交一頭派購豬有關。那時候,只要是單獨一戶在生產隊分口糧的人家,都要養一隻豬交給國家,但不是白交,也有賣的成分,不過價格由國家說了算,並且只能賣給國家。
這樣,每家每戶就得養兩隻豬,一隻派購,一隻肉豬。後來,國家取消牲豬統購政策之後,周家埡人家,基本上還是沿襲計劃經濟時代的套路,只不過是派購豬賣給豬販子,不再非得賣給國家了。
想想那時候,養豬沒有豬飼料一說,廚房的湯湯水水加上地裡的野菜嫩草,養肥兩隻豬,殊是不易,因此,派購豬大都只有一百多斤就出欄了,年豬的毛重會稍微重一些,但也與派購豬相差無幾。
這種豬即現時城裡人推崇的土豬肉。但其實,真正的土豬肉並不存在。即使是農村,即使是自家養來做年豬的豬,也會吃糧食,玉米、紅薯,吃野菜吃草長大的已經很少了。不過,這樣養大的豬,絕少含激素,說是土豬,假使只是與養豬場吃了種種新增劑長大的豬相比,也是可以的。農村人與城裡人相比,有諸多的不易與不幸,但從肉食的放心程度上來看,農村人顯然佔了優勢。
但周家埡養豬的人家並不是所謂的家家戶戶了:城裡住一半鄉下住一半的人家,不會養豬;年紀太大兒女又不在身邊,也無法養豬。真正養豬的人家,是為數不多的以農村為主要居住地的人家。或者,男人在外打工,女人留守在農村的人家。
堂妹兩口子常年住在周家埡, 他們家算得上是周家埡養豬人家的代表:不僅養豬,還養了兩頭,一頭已經賣掉換錢,另一頭,留住,準備做年豬用。
前不久我到堂妹家去,堂妹說,哥,過些日子殺年,來吃殺豬飯啊。吃殺豬飯是周家埡不變的習俗,殺年豬的當天,取新殺的豬肉,做一桌飯,招待殺豬匠、家族中的長輩、鄰里。一般少不了新鮮豬肝、回鍋肉。我離開周家埡三十多年了,趕上可以在老家吃一回殺豬飯,還是很誘惑我的,我當然不會拒絕。
吃殺豬飯這天,我早起就去了堂妹家。殺豬匠還沒到,另一戶人家也在今天殺豬,殺豬匠要把那邊忙活完了才會過來。我和堂妹開玩笑,說:“潤香啊,你辛辛苦苦養了一年的豬,要殺了 ,捨得啊?”堂妹樂呵呵地回答我:“有什麼捨不得的?我還嫌殺晚了,多吃好多糧食。”說著,她開啟豬屋門,給豬喂最後一餐食。這是一個儀式性的動作,豬都要殺了,還餵食,其實是浪費時間。但沒有誰會捨不得這一餐豬食。
堂妹家的年豬是一頭大白豬,估摸著有兩、三百斤重。堂妹一進屋,它就昂起頭,朝堂妹“哼”一聲,從豬欄的一角走向豬槽。堂妹將滿滿一桶豬食倒進豬槽,放下豬食桶,看豬吃食。一會,她拎起豬食桶,神情有些肅穆地對大白豬說:“畜生畜生你莫怪,你是主家一道菜”。之後,開始張羅燒開水。豬欄屋裡,傳來大白豬吧嗒吧嗒吃食的聲音。
這樣的場景,小時候家裡殺年豬時自然是見識過的,“畜生畜生你莫怪,你是主家一道菜”應該是一道心理安慰的符咒,養豬的人、殺豬的人、看殺豬的人、吃豬肉的人因此可以平靜地接受一條生命在眼前滅失而不會有所謂的血腥和恐怖。
一個家庭主婦,辛辛苦苦養肥一頭豬,你說她對豬沒有感情,我不大相信。跟隨堂妹去給豬喂這最後的一餐豬食,讓我體味到,它對於堂妹心理慰藉上的意義。我也很感謝讓我重溫了這一場景,意識到小時候為什麼看殺豬並不感到害怕的原因了。
“畜生畜生你莫怪,你是主家一道菜”,這是懵懂歲月裡極其難得的心理教育。生命中,有些場面是需要正視的。一個從來沒有見識過殺豬的城裡人和一個從小就就接受養豬是為了吃肉這種教育長大的農家孩子相比,未必一個是心善的另一個就是心硬的,不過是誰受到或者沒有受到良好的自然法則的教育之區別而已。否則,這個世界,可能會有人養豬,但絕不會有人願意自己養的豬被殺掉,也就更不會有人去做殺豬匠了。
只有融入這種群體意識,諸如堂妹這樣的家庭主婦,才不會在生活面前產生疑惑。她們心安理得地養豬,然後,盼望年豬長大長肥,一到冬月,則自然地盤算著哪一天請了殺豬匠來,將豬殺了,做臘肉、灌香腸、蒸血膃,做她們應該做的事情。
殺豬匠是本家大哥,叫周明亞。他的父親,我叫他克定伯。克定伯是周家埡兩個殺豬匠中掌作的一個,他操刀,放血、褪毛、開邊、分塊,這些工作都屬於他。他的搭檔姓陳,負責扯腿、給豬吹氣、清理下水等。明亞哥至少在他青年時代還不是殺豬匠,他接克定伯的班不知道始於何時。我問明亞哥,你殺豬跟克定伯學過沒有?他說當然學過。子承父業很好理解 ,但陳姓殺豬匠並沒有將他的手藝傳承下去 。與明亞哥做搭檔的,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中年人。
殺豬是一件技術活,不是誰膽子大就當得了殺豬匠的。放血,一刀下去,不僅要準確地刺中頸部動脈,刀尖還要直達心臟,這樣才會很快讓豬失去意識,減少豬的痛苦,保證血液儘快流出。另外,刀口的大小也很有講究,捅口太大,血液會四處飛濺,不利於豬血的收集。
須知,豬血在年貨中往往派有大用場,它和豬大腸、蕎麥麵合在一起做成血膃,是湘西北特具風味的一道菜,和臘肉一起燻幹,可以儲存很久。吃的時候,要用水泡軟,切片,慢火煎熟 ,其味美雜有臘大腸的油香,又有豬血浸透蕎麥麵後的鬆軟、油膩,是難得的下飯菜 。
如果豬血濺出血盆之外太多,主家就會對殺豬匠有意見。捅口的深淺還關係到豬是否殺得利落。如果一刀下去,豬血出不來,再補一刀 ,是特別犯忌的事。據說,會對主家不利。但我認為是人類對動物的一種善意關懷。一刀斃命 ,叫早死早託生;補刀,則有虐殺動物的嫌疑。
殺豬的技術,還體現在褪毛上。褪毛乾淨而不傷面板,訣竅就在水溫的控制和燙毛時間的長短上。這一道程式,有經驗的殺豬匠調好水溫之後,將豬置於專用的腰盆內,輕輕晃盪幾下 ,即迅速刮除豬毛,節奏很快。三下五除二之後,腰盆內的豬露出白白的面板,基本看不見什麼豬毛了。但這只是初步的整理。接下來的工作,是殺豬過程中耗時最長、最需要耐性的工作,踢出細毛。
首先,要在豬的後腿上各割開一道小口,然後將一根拇指粗細的鐵釺插入豬的體內,在表皮下形成兩道通氣道,然後用嘴吹氣,將豬身整體吹成渾圓的形狀,這樣,豬的表皮完全撐開,任何細毛都會挺直起來,便於刮刀刮除。克定伯時代吹氣是人工進行的,他的搭檔,那個陳姓師傅鼓起腮幫,一口下去,豬的後半身鼓起了;再一口氣下去 ,前半身又鼓起來了。兩口氣,沒點功夫是做不到的。陳姓師傅兩眼發直、滿臉憋得通紅的樣子,我至今記憶猶新。
現在,吹氣這一環節,明亞哥他們已經改良,不再人工吹氣了,而是用打氣筒一點一點地往裡充氣。有些殺豬匠甚至用上了電動充氣機,電門一開,豬身立即整體鼓脹開來,這種裝置不是太貴,明亞哥他們為什麼不用,我猜很大的一種可能是明亞哥他們不願意添置新的行頭了,能將就暫且將就著再說。
明亞哥已經75歲了,他揮動砍刀時,已明顯力不從心,這是我後來看他開邊和分塊時發現的。當時,我問他,明亞哥帶徒弟沒有?他疲憊地一笑,無可奈何地說,現在還哪有年輕人願意學殺豬?要是有,我也不會幹了,幹不動了。
我忽然發現,殺豬現場竟然沒有一個看熱鬧的小孩子。殺豬那天是星期六,不是孩子們上學的時間,孩子們呢?一問,才知道村子裡平時幾乎沒有小孩子在,要不然,這樣的場合,是斷然少不了孩子們圍觀的。
我想起了我小時候,聽說那戶人家要殺豬,都會莫名地興奮,一幫大大小小的孩子,圍在現場,等待搶豬尿脬或者豬腳殼。一般我們也有自知之明,不是自家殺豬,不會指望要到豬尿脬,但豬腳殼是有可能的。豬腳殼套在手指上,不知道好玩在哪裡,卻就是喜歡玩。
豬尿脬則當氣球用。第一步是在眾多小夥伴們的羨慕中將豬尿脬放在草木灰裡面不斷地搓揉,粘粘在尿脬上的油脂類物質就會慢慢脫落,最後變得富有彈性並且透亮,這時候就可以當氣球玩了。
吹氣,將尿脬吹大,扎進吹氣孔,原本小小的尿脬就變成一隻碩大無比的氣球了,大家你搶我追地將尿脬氣球在空中頂來頂去,都以頂到尿脬為驕傲。尿脬氣球皮實,不用銳利的物品刻意刺破它,它是不會自我炸裂的,因此能玩的時間長,但它乾枯之後就吹脹不開了,一般也就是隻能在殺豬的當天玩一下,所以,誰擁有誰不擁有,都只是佔有慾的一時滿足,真正快樂的是尿脬氣球在空中你追我搶的快樂。
終於,大人喊吃殺豬飯的叫聲傳來,一群歡天喜地的小傢伙們才停止這個遊戲,有資格去吃殺豬飯的跑到餐桌邊去搶肉吃,沒有資格吃殺豬飯的則悄無聲息地跑到一邊,免得被小夥伴們譏笑“守嘴”。
一個在殺豬場所看熱鬧、搶豬腳殼豬尿脬的孩子,對於該不該吃殺豬飯往往拿捏得十分準確,一般不會有讓主家為難的時候。當然,也有貪吃的小孩子真的會守嘴,他站在門口,兩眼直勾勾地望著一桌子人大吃大喝,但不會攏過去,主家看不過場,會盛了飯,夾幾塊肉遞給他,他卻扭頭就跑,不肯接了去吃。主家轉過背去,他又摸到門口,守起嘴來……如此幾個回合下來,吃殺豬飯的散席了,主家再招呼他,他可能會吃口菜,然後跑開不再回來,也可能堅持只守嘴不貪嘴,主家散席了,他也就走開了。不過,吃了這一口菜的,當被譏笑為“守嘴佬”時,他往往做聲不得,但沒有吃的,碰到被人譏笑,他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駁了:“我哪守嘴了?我是去看熱鬧的,未必熱鬧也看不得?”
刮淨細毛雖然很費時間,但比起克定伯時代 ,明亞哥他們還是顯得快當一些,因為他們使用了燒毛器,無法下刀的地方,或則刀刮不淨、的地方,主要是豬頭、豬腳、豬頸、豬胯等部位,用燒毛器燒一下,然後颳去燒糊的毛樁,就算完事了。
燒毛器其實就是一個高壓噴嘴,連著一個液化氣罐,火力硬,瞬時溫度高,其所過之處,細毛短樁,皆成炭屑,他們這樣刮除細毛,當然簡單省事。克定伯時代則完全憑一把刮刀慢慢解決,不僅慢,也會留下一些無法刮乾淨的地方。小時候吃豬蹄、吃豬頭肉,大人會找一把火鉗,在碳火中燒紅,然後烙去留在豬身上的細毛,這是見怪不怪的事。
卸去豬頭,然後拿出掛鉤,鉤進豬尾巴處,將豬倒掛起來,剩下的工作,就是開膛破肚,取出內臟,卸去四肢,然後將豬身分成兩邊 一邊一邊地分成小塊。這時候,殺豬匠會先割出殺豬飯需要的部位,豬肝半頁,圓尾肉半斤,豬肋骨數條,交給廚房去烹飪。
分成小塊的豬肉 ,殺豬匠用刀尖一塊塊刺出掛扣,用主人事先準備好的棕葉做成的掛環,套在肉塊上,主刀的工作就此結束。做搭檔的趁主刀師傅給肉分塊時,幫主家整理豬大腸、小腸、豬肚 ,打掃場地,清洗腰盆,刀具,之後,吃幾口殺豬飯,又到另一家去殺年豬。
這一天明亞哥倆搭檔要殺五頭年豬,一大早開始,到吃午飯,他們殺掉了三頭,下午還有兩頭。作為主刀師傅 ,明亞哥七十大幾了,可謂不易。望著明亞哥遠去的背影,我在想,他會是周家埡最後的殺豬匠嗎?
殺豬飯一般是女主人做,堂妹平時做飯手藝不錯,做一桌殺豬飯,拿得下火。但是,她請了建中哥來主廚。建中哥也是本家兄弟,早年在城裡開餐館,後來回村做鄉里廚子,主要是紅白喜事為別人包廚,偶爾也幫人做點上門炒菜的活兒。
雖然從小知道他比我大,但大多少我並沒個數。吃飯時,我坐在他身邊,問他大我多少?居然大我一輪多呢,都七十掛零了。不過,他實在顯得年輕,個兒不高,臉盤不大,面板白,粗粗看去,不過四五十歲的樣子。
他的包廚生意,是為有需求的人家辦酒席,對方提供原材料,他負責製作,收取工錢。他還置辦了流動大棚,桌椅板凳,出租給用家,餐具則是一次性的碗筷,主家花錢購買。
鄉里廚子是一直就活躍在鄉間的手藝人,周家埡有名的廚子,當屬克定伯。殺豬而主廚,是一種很好的手藝搭配。我們回憶克定伯幫人主廚的架勢,發現他做的酒席,幾乎全部是蒸菜和燉菜,蒸菜通常是珍珠丸子、蛋卷、虎皮扣肉,燉菜則五花八門,一溜爐鍋,一鍋一道菜,開席前大火煮開,盛出來就直接上桌,很適合農村裡賑流水席。
建中哥不是學的克定伯的手藝,是在城裡的廚師培訓學的,他辦酒席的方式與克定伯不大相同,缽子多、炒菜多,相比之下,廚師要累一些。他承認克定伯的方式適合賑酒,他的方式適合開餐館。
“年輕時,沒覺得廚子是個飯碗,沒想到找克定伯學,等到想學時,他老了,帶不了徒弟。”建中哥作為鄉里廚子,肯承認前輩廚子,除了他自身的謙恭外,克定伯是個好廚子,已然成為周家埡的口碑,那是一代人幾代人輕易抹不去的事實。
克定伯還做些食品加工的事,做麵條、擀餛飩皮、煮粉,他的日子,因此過得比一般人殷實。克定伯去世已經多年,他常常被人記起,與他多面手的手藝有關,無疑,他是周家埡的能人,周家埡也因為他的存在,得到過與其相稱的便利。可惜,隨著他的故去,周家埡而今已很難找到手藝如此全面的能人了。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致謝原創)
編輯: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