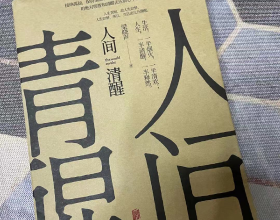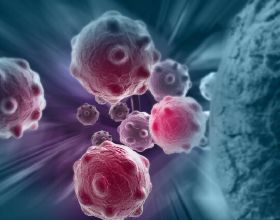今天是2021年12月23日,我想寫的這件事發生在2007年7月6號晚上11點半左右。
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呢?因為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搶劫,還是持械搶劫,也是我導遊生涯中第一次出三日遊。我是2005年從保定到石家莊上了一所不知名的民辦大學,專業是旅遊英語,06年的時候我就考了導遊證,記得領證是07年3月份吧,領完證我就自己找了一家旅行社開始實習了。
前十幾年的時候,旅遊業屬於朝陽行業,導遊也很忙。當然,像我這種沒有經驗的在校小白都是在旅行社給大哥大姐們打下手,或者在電腦前面打字敲行程,幫別人發發傳真,幫經理騎著腳踏車穿越半個石家莊去拿發票啊結算團費啊送行程啊領名單啊這類的活兒,不過依然樂此不疲!有時候也會在週末跟跟團,學習一下,幫老導遊點個數。記得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學校剛剛放了暑假,我還沒有回家。經理通知我可以跟團去趟五臺山,我特別開心,下午就從學校去了市裡,經理把一大筆團費支給了我,因為那次是經理帶隊,我負責結算一下各種費用。那個團都是個體戶還有大小老闆們,去五爺廟還願,當地會有地接導遊接待,經理屬於陪同領隊過去,可能覺得他親自跑前跑後跌份吧,帶了一個我這樣的實習生過去。那筆團費是多少呢?兩萬五千塊錢,當時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大筆錢,我一年學費4200,一個月生活費500。旅行社在中山路上,當時我老公在北二環和三莊街交叉口附近上班,他在三莊街那租了房子,辦完旅行社的事情我就去了老公那,那時候還是男朋友。
接團時間是晚上12:00,這個時間倒是沒什麼稀奇的。從2015年交通部才規定客運車輛凌晨2:00到5:00強制性就近進高速服務區停車休息。以前是沒有這樣的規定的,所以一般三天的行程發車時間都是週五晚上九點以後,走夜路直奔目的地。我跟經理說我在友誼大街和北二環交叉口南邊,華潤萬家超市上車。大概十點多的時候,我在出租房就開始整理我隨身背的一個挎包。因為我們帶團會有各種票據,所以一般以前的導遊都有一個風琴夾。我的風琴夾裡裝著我的學生證,導遊資格證(當時還沒有換導遊ic卡),兩萬五千塊錢,一張單子(記著到五臺山接團導遊電話、接團地點、團隊名單等),還有我自己的200多塊錢,和一張交話費的發票。一般情況下,所有第二天要用的東西我都會在風琴夾裝好,那天裝好之後,我把錢拿了出來,放到了挎包側兜裡。大概十一點二十,我就出門了,穿過華潤萬家那條街道,走到友誼大街上。我那天是自己走過去的,我老公沒有送我,他好像是在公司樓下吃飯去了。過了馬路我就在路邊的綠化帶裡找了一個凳子坐下等著,我身後三米吧,就是民心河。
夏天晚上11點半大街上人也不太多了。我正在那坐著,忽然有人從身後一隻手抱住我,另一隻手捂著我的嘴。我以為是我老公來找我了,當時一點沒有害怕,可是我用眼睛的餘光瞟了一下,卻看到了一條白色的褲子。我老公沒有白色的褲子,我立馬打起精神問他,:“你是誰,幹什麼?”那個男孩聽聲音很緊張,他說:“你不要喊,把包給我!”他還有一個同伴,站在我們身後,說往後面拽她,往後面一點。我還回頭看了一下,但是樹的陰影把他擋住了,沒看清楚。我扭動間,感覺後腰紮了一下,當時特別鎮定地說,“哎~你拿什麼扎我,鑰匙嗎?”現在想想,真不知道是不是梁靜茹給我的勇氣!說著我就反手摸了一下,對,我摸到了一個刀尖,說真的,心裡緊張了一下,心想,媽呀,遇到搶劫的了!抱著我的這個男孩一直在說要把包給我,快給我!我拿著包說,我給你開啟,我包裡就二百多塊錢,我給你拿出來了。我慢吞吞地拉開了拉鍊,他在我正後方,腦袋正好在我右肩膀上面伸著,我拉開挎包拉鍊的時候風琴夾先露了出來,他伸手拽出來兩個人就跑了,一個穿著一身白色的衣服,另一個比白衣男孩矮一些,穿著深色的褲子,上衣忘了什麼顏色。現在想想,最搞笑的就是接下來我喊的那句話,我沒有說搶劫啦,抓小偷啊~我朝著倆人追了兩步,喊他們:“把學生證給我啊,我回家買火車票還用呢!”追了兩步又覺得不對勁,我就掏出電話,給老公打了電話,不過三五分鐘他和兩個同事就來了,三個人往南追了過去。他們剛走了沒幾分鐘,我的電話響了。我接起電話,有個男孩的聲音說,你要你的學生證就來水上公園北門拿來吧。老公和同事三個人沒一會兒就回來了,我說別追了。同事小楊說,報警吧。可是我又珍惜我這個跟團的機會,時間馬上就到了,我說不用了,畢竟心裡也知道沒損失什麼。當時老公和同事去追搶劫的人,我心裡想得很多,看著那兩個男孩就像是高中生一樣,當時附近好多網咖。我猜測可能是出來玩的孩子吧,萬一我報警了抓住他們會不會毀了那兩個孩子呢?水上公園北門對面就是一個派出所,記得好像是三莊街派出所。這倆孩子一定不是慣犯,所以基於這兩個原因的考慮我並沒有報警,可能最主要還是因為我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損失。
老公讓我趕緊看看丟了什麼,我跟他說了一下,還嘟囔了一句,這下我回家怎麼買半價火車票,學生證在風琴夾裡面呢。他說別怕,回家的車票我給你買,不用買半價票了。也不知道該說我心大還是膽子大,就這樣經歷了一次持刀搶劫!大約半個小時以後,我就登上了去山西五臺山的大巴車。別的不麻煩,這個學生證可是真麻煩,後來去報社登報掛失,學校才能給補辦。直到現在想起來,還能感受到被“鑰匙”頂住後腰的感覺,不知道我的這次姑息,是救了還是害了那兩個大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