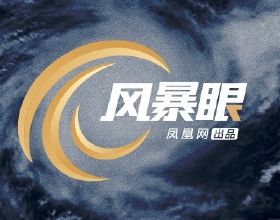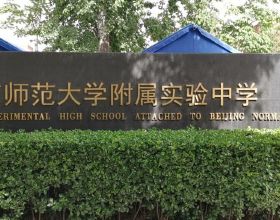談及古代科學史,很多人言必談古希臘,對中國卻不屑一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古代科技重應用、不重理論,重經驗、不重實驗,與古希臘注重理論總結、注重實驗相差甚遠。姑且不談所謂的古希臘文明來歷不明,以莫名其妙地違揹人類進化邏輯的方式出現,就說從客觀實驗出發,採用大規模的實驗方法去探索自然規律的科學實踐上,中國古代也有相應的科學大師,本文所講的這位科學巨匠叫趙友欽,在世界物理史上有一項開創性的成就,比後來的著名物理學家義大利伽利略海早了兩個世紀,同時他還科學論證了“地球是圓的”。
趙友欽是宋末元初人,或名敬,字子恭,自號緣督,因此別人就稱他為緣督先生。他是宋室漢王趙元佐十二世子孫,趙光義的十三世子孫,籍貫為江西鄱陽。宋朝滅亡後,為避免受到元朝的迫害,他浪跡江湖,隱逸道家。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即道教和科學的緊密聯絡,歷代都有對科學巨大貢獻的道教徒,其中如葛洪、陶弘景、孫思邈等人,足可在中國化學史、醫學史等領域佔一席之地。但與前人略有不同的是,趙友欽隱逸道門之後,他的興趣不在煉丹煉藥上,而是痴迷於物理光學領域。
中國古代光學有著許多輝煌的成就,其中之一是光學研究,對光的直線傳播、小孔成像等現象,《墨經》、《夢溪筆談》早有記載。然而,對光線直進、小孔成像與照明度最有研究,並最早進行大規模實驗的卻是趙友欽,他的這些實驗在世界物理學史上是首創的,被記載在《革象新書》的“小罅(xià)光景”(即小孔成像)這一部分中。
對於光線直進、小孔成像與照明度等諸多光學現象,儘管古人早有記載,但記載的畢竟比較簡略,很多問題並未描述清楚,趙友欽對“室有小罅雖不皆圓,而罅景所射未有不圓;罅雖寬窄不同,景卻周徑相等”等問題疑惑不解,於是開始長期觀察、實驗、分析。
透過長期觀察、實驗、分析,趙友欽得出不少論斷:小孔成像“隨日月之形皆圓”,而大孔成像與孔的形狀相同;孔變小時,像就會變得暗淡,物距孔越遠像越暗;孔變大時,距孔越遠,其像也越大,但明亮程度不變等。
為了進一步驗證由觀察自然現象得到的論斷的正確性,於是趙友欽就在浙江龍游雞鳴山築觀星臺,建造了“小孔成像”實驗樓。實驗樓是一棟兩層樓,上面是兩間房子,每間房子下面各挖一口4尺直徑的圓井,右井深4尺,左井深8尺,其中左井裡放一張4尺高的桌子。在井底有兩塊直徑4尺的圓板,上面各放置1000根蠟燭,用來模擬日月光源。井口地面上覆蓋兩塊直徑5尺的圓板,左邊開孔一寸左右,右邊開孔半寸左右,以樓頂天花板作為固定的相屏。如此大規模的物理實驗,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比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義大利的伽利略早了兩個世紀。
根據《革象新書》記載,趙友欽的實驗分為五步,主要驗證了五個光學問題。
其一,保持光源、小孔、像屏三者距離不變,改變小孔的大小,最終確認“小孔雖方,其像必圓”,但隨著照度不同,像會出現一濃一淡,“寬者濃而窄者淡”等,並對這種現象進行了科學分析。
其二,改變光源大小與強度,模擬日月食現象,將右邊蠟燭減少500支,剩下的集中放置在木板的一邊,最終觀測到“右間樓板缺其半於西,乃小景隨日月虧食之理”,這也表明小孔成像是倒像的道理。
其三,改變像距,調整小孔到螢幕的距離,得出“照度隨著光源強度增強而增強,隨著像距增大而減小”的粗淺定律。在400年之後,西方才由德國科學家來博託得出“照度與距離平方成反比”的定律。
其四,改變物距,調整光源到小孔的距離。在光源強度、小孔大小、像距都不變時,趙友欽發現物距愈大、像愈小,反之物距愈小、像愈大,“由是察之,燭也、光也、竅也、景也,四者消長勝負所當論者”,揭開“小孔成像”的基本原理。
其五,改變孔的大小與形狀,觀察大孔成像的情況。趙友欽觀察再次確認大小孔成像不同,小孔時“不睹一景之全,碎徹千燭之景”,但大孔時“大罅之景千數,比於沓紙重疊不散,張張無參差。(更)大則總是一井之景,似無千燭之分”。
在結束“小罅光景”篇時,趙友欽最後寫道:“是故小景隨光之形,大景隨空之象,斷乎無可疑者。”即大孔成像與大孔形狀相同,小孔成像與光源形狀相同,這一結論無疑非常正確。
除了上述光學實驗之外,趙友欽還有一些世界級的成就:
首先,科學論證了“地球是圓的”。18世紀之前,除了環球航行之外,論證“地圓說”最科學的辦法是確定經度差、緯度差,其他的或多或少不夠嚴謹。唐代與元代曾在南北、東西大規模天文觀測,發現北海與南海的北極星角度明顯不同而確定了緯度差,發現開封與西域的月食出現時間相差1更半而確定了經度差,由此趙友欽指出“測北極出地高下(即緯度差異),及東西各方月食之時刻早晚(即經度差異),皆地體渾圓,地度上應天度之證”,論證了“地球是圓的”,比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嚴謹的多。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認為觀測船隻桅杆可以論證“地圓說”,但趙友欽指出這種方式不可信,“地體雖渾圓,百里數十里不見其圓,人目直注,不能環曲。試泛舟江湖,但見舟所到之處隆起,而水之來不見其首,水之去不見其尾”,而他認為觀測遠處大山更為可信,“洞庭之廣,日月若出沒其中,遠山悉在環曲下,不為障也。”說到底,地球太大了,人的目力有限,基本不太可能看得清遠處桅杆,而遠處大山很大,“不為障也”,可以發現遠處大山“悉在環曲下”。
其次,趙友欽還闡述了“月體半明”的問題,為此他將一個黑球掛在屋簷下比作月球,反射太陽光,發現黑球總是半個球亮半個球暗,而從不同位置去看黑球,看到的黑球反光部分的形狀不一樣。最終,他透過這個模擬實驗,形象地解釋了月的盈虧現象。
除了天文、光學上的成就之外,趙友欽還有很多成就:數學上的割圓術,他將千寸直徑的圓周分割為正16384邊形,這一成果記錄在《革象新書·卷五·乾象周髀》中;曾經“東海上獨居十年”、“發前人所未言”注《周易》數萬言,還著有道家的《金丹正理》、《盟天錄》、《推步立成》等書。可惜的是,除《革象新書》外的其他著作,後世都已失傳了。
今人談及中國古代科學,簡單的“古代中國是實用技術”一句概括,似乎中國古代完全沒有實驗、沒有理論總結,這種說法無疑有失偏頗,趙友欽就是明證。其實,不僅僅是趙友欽,還有戰國石申、魏晉劉徽、南北朝祖沖之、宋代賈憲、元代郭守敬等等,都是當時世界上最頂級的大科學家。可以說,如果古代中國沒有科學,也就不可能創造出璀璨的文明,不可能數千年佔據世界第一,問題在於古代中國沒有形成科學傳統與傳承,比如趙友欽與他的《革象新書》就一直鮮為人知,這才是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