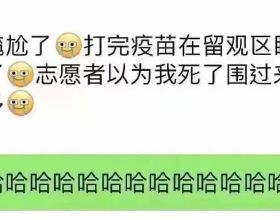我的這位悉尼朋友名字叫Emy,認識她是在十五年前。那時我兒子在悉尼讀預科,之後就讀悉尼大學。兒子初中開始就住校,高二就去了悉尼讀預科,是我的獨生子。因為自小離家,所以在我的內心深處對他有種深深的愧疚。他在悉尼讀書期間只要我有長假或年休假,我都會盡量的飛過去陪伴他。那時的機票也還便宜,從香港機場起飛到新加坡轉機往往來回雙程票5000多,運氣好的時候還可以買的3000多的,所以工資的一部分就貢獻給了航空公司了。我的朋友們經驗之談告訴我在兒子沒有女朋友或結婚之前儘量多點陪伴,到了他有女朋友或結婚之後就不需要你的陪伴了,如果“陪伴”太多反倒引起他的反感,也就是說其實跟兒女在一起的時光是短暫的。我確實也是深有體會,於是給航空公司打工就打工吧,錢財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不必太在意。我先生的哥哥弟弟都在悉尼開中醫骨傷科診所,那時兒子跟同學一起租房住,我也就住到二哥的診所了,早早晚晚或者沒有外出基本上也就在診所幫忙。我是學醫的,做了二十幾年醫生,雖然不太懂中醫,但互通還是可以的。診所的病人裡華人特別多,所以“結巴英語”的我也可以湊合。我除了國語外,潮州話、粵語、客家話都沒問題,而在悉尼這幾種話已經足夠應付了。診所以針灸為主,配合推拿,中藥膏貼等等。所以我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忙製作膏貼,陪客人聊天,解釋病情等等,還是挺受歡迎的。
有一位客人經常光顧診所,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她就是Emy。印象特別深的原因是她幾乎與所有的澳洲人不同。她與不管來自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澳洲居住者有著天壤之別的裝扮。一般澳洲人穿著都非常隨意,普通的體恤,牛仔褲或普通的毛衣和褲子。甚至是套頭衫加“孖煙囪”短褲,包括冬天都可以是套頭衫加“孖煙囪”短褲,外面再套件寬大的羽絨外套,男女都差不多。即使在CBD上班的高階白領也就是西裝領帶,手夾一個公文包。女孩子也只是一套幹練的上班服。只有傍晚時分在夜總會的門口才會看到穿著黑色晚禮服的高挑女郎手挽著肥胖的中年禿頭男士在街上款款而行。我曾經在下班高峰期很無聊的站在中央火車站出口一個多小時,目不轉睛的盯著從火車站出來的人流,觀察他們的服飾。很可惜的是幾乎沒有見到一例服飾漂亮得體的女士。而Emy當時五十多歲,中等個頭,大約有一米六多一點,不胖不瘦,身材恰到好處,尤其腰身還是不錯,沒有中年人的水桶腰。幾乎球形的臉龐圓乎乎的,臉蛋幾乎是完美的弧線,沒有任何稜角。眼睛大大的,不知道是不是假睫毛,看上去挺長的,眼睛經常半眯著,眼眸裡含著微笑。鼻樑略顯高聳,但不是西方人的高鼻樑,是典型的東方人種的高鼻樑。嘴裂稍長,嘴唇稍稍有點厚,但雖不是櫻桃小嘴,配在她圓圓的臉龐上還是非常合理的配搭。臉上塗著厚厚的一層胭脂,大紅的唇膏把這略顯肥厚的嘴唇弄的特別顯眼。尤其特別的是頭髮燙的非常蓬鬆,高高隆起,加著摩絲的固定,使透過頭髮的膨起可以增加人體的高度起碼8—10釐米,因此整個人顯得比較高挑。她幾乎每次來診所都穿著各種各樣的漂亮裙子。第一次見她穿的就是略露豐乳的低胸V領,上臂泡泡狀,前臂收緊,腰身緊縮,裙襬又是泡泡的長裙,上身白色為主帶點粉紅色小花,下襬略深的藍色,裙子的材質應該是絲綢的。大紅指甲的手裡拿著一個鑲嵌著黑色珠寶的小袋子。胸前的項鍊,大大的圓形耳環和無名指上的戒指都是由白金和鑽石為支撐,中間鑲嵌著一顆碩大珍珠的,看上去是一個系列套裝。這些首飾在陽光下特別的閃耀。當她從賓士650的小轎車下來,第一次出現在我的眼前時,我恍惚看到的是一位十八世紀的歐洲貴婦人款款而來,有點幻覺,有點神遊。她跟二哥很熟,經二哥的介紹我知道她是印尼籍的華人,是我們廣東的“客家妹”,於是在她做理療的過程中,我們開始攀談。她會講普通話和客家話,也能看懂大部分的中文字。她的父親是我們廣東客家地區的,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到了印尼。估計當年就是從鬆口古鎮出發下南洋的那一批,跟他信,英拉的爺爺,李光耀的父親這一類到南洋討生活的一樣。她的父親是有點文化的人,媽媽也是家鄉一起過來的。在印尼定居做生意,她是在雅加達出生的。從小除了學校的功課之外一直在補習學校學習中文,學習普通話,家裡堅持講客家話。所以她除了英語,印尼話還會中文,普通話和客家話。十八歲就結婚了,也是嫁給一個印尼籍的華人。夫家擁有印尼群島中的三個島嶼,全部都是種植珍珠的,是印尼的珍珠大戶。她生育了三個女孩,也許是印尼的自然環境,很奇怪,在印尼很難生出男孩的,而印尼的法律是一夫四妻制,雖然她沒有告訴我他的先生有幾位夫人,但我估計她是大太太,因為她的年齡跟他的先生一樣。她三十幾歲就到了印尼定居,帶著她的三個女兒。每年節假日也會回到雅加達居住。現在她五十多歲了,大女兒已經結婚,住在悉尼但離她家很遠,故很少回來。二女兒嫁在雅加達。三女兒在美國讀大學,所以她現在跟保姆一起住。也許是緣分,我這個從來不講究打扮,永遠都是襯衫長褲,從來不化妝,素面朝天的中年女人竟然跟這麼一位濃妝豔抹的貴婦人很談得來,真有點不可思議。她幾乎每隔一天就來診所一次,每次呆上兩小時,而只要我在診所,這兩小時幾乎就被她徵用,慢慢的我們成了好朋友。每次都是她主講,她幾乎告訴了我她這一生的所見所聞,說到開心時會不顧一切的哈哈大笑。也經常讓我告訴她爸爸老家的情況,我也如實的告訴她想要知道的一切。尤其是她說父親告訴她家鄉很窮,他們當時是怎樣為了擺脫貧窮漂洋過海,差點喪命海中和到了印尼怎樣的做苦力,做小生意等等艱苦奮鬥的歷史。我也告訴她我上山下鄉的經歷以及如何透過考大學改變命運和改革開放後高速發展的變化,邀請她到中國來玩等等。她很愛惜身體,於是我也就儘可能的給她聽診,檢查,講解身體健康和疾病的問題。還告訴她去醫院檢查哪些專案等等,儼然成了她的家庭醫生。
有一個週末她盛情的邀請我們一家到她家做客。她家住在悉尼的東區,東區歷來都是悉尼的富人區,房價是西區的N倍,是同樣被譽為富人區的北區的二到三倍。不過儘管東區的房子很貴,但進入東區的道路卻不是平坦筆直的大道,而是彎彎曲曲,起起伏伏的兩車道。對於習慣深圳平坦大道的我真的很不習慣。路旁的建築物雖然許多維多利亞式的歐洲風格,但也不少現代風格的 ,各種各樣,琳琅滿目,感覺有點“建築博物館”。我們的車行駛在這蜿蜒小道,途中經過庫克船長當年登入澳洲的登入點,登入點除了一塊大石頭寫著“庫克船長登入地”之外就是一座不大的白色燈塔,其他就沒什麼了。經過大約一小時的車程到達了Emy的房子門前。房子的大門沒什麼特別,也不是非常豪華,但進入大門之後卻是令我大為驚歎。大約有200多平方米的前花園種植著許許多多的花草,園林工正在認真的修剪枝葉。我認識的是玫瑰,好多的玫瑰花正以燦爛的笑容迎接我們這些遠方的客人,還有許許多多的花我叫不出名字。花圃中還有幾顆不大不小的樹木,有一處火山岩石構成的假山,假山上流水潺潺,假山和流水下面有一個十幾平方米的魚池,池中美麗的紅鯉魚自由自在,灌木叢籬笆將花圃隔開一條人行小道。我們沿著人行道進入大別墅。別墅也是維多利亞式的風格,許多羅馬柱和白色人體雕塑和花朵雕塑,蕾絲花邊的屋簷和欄杆清一色的白。客廳中央有一大半圓圈的布藝沙發,沙發墊是粉紅色的底色和深紅色的大花,一看就知道主人一定是女性的。沙發前面白色流線型的茶几上擺放著一瓶很鮮豔的玫瑰花,旁邊是水果盆。客廳的正中牆壁上是一個巨大的液晶電視。電視的下方是一個大的壁爐。牆壁的兩側一邊是中國式的國畫,也是花畫,有牡丹、紅梅、菊花等等,大約是四幅吧,因為這種畫太常見了,反倒不是很留意。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客廳右側的牆壁上鑲嵌著一塊有四平方米左右的陶瓷畫,畫中是福祿壽全圖。Emy看我眼睛直愣愣地注視著這幅陶瓷畫,她及時的解釋說這是她專門找人從中國定製的。真不簡單,在幾乎完全歐式的房間裡竟然如此和諧地擺放著這幅來自中國的陶瓷畫,而且是古人最信奉的福祿壽。此刻我內心非常激動,無論身在何方,無論接受什麼教育,骨子裡的東西還是與生俱來的,這就是根,是深埋的根!主人家很大,房間很多,餐廳裡擺放著一臺可以坐十幾個人的方形餐桌,餐桌上也是擺放著鮮花。餐廳的牆壁上掛著許多家庭生活照,其中許多是她和先生一起外出遊玩的合影,可以看得出她是很幸福的,丈夫對她也是很寵愛的。另外有一間是Emy的工作室。她一輩子都沒有外出參加工作,但她喜歡珠寶設計。設計臺上有許多圖紙,我隨手翻看了幾張。雖然我不懂珠寶設計,但也可以看得出設計很優美,很浪漫。她說她有固定的加工師傅,她設計完了就直接找這位師傅加工,然後賣給她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偶爾也放在悉尼CBD的一家珠寶店售賣,因為珍珠是自家產的,所以她選的都是最上乘的珍珠。那天她還送了我幾顆很珍貴的珍珠,因為我幾乎不帶首飾,所以後來我找深圳的師傅加工成耳環、項鍊、戒指一套轉送給了親家母,這也算是我這輩子能拿出來送給她最珍貴的禮物了。
Emy的別墅實在太大了,除了別墅本身,前花園很大,屋後更是嚇人。有一個兩條道的恆溫游泳池,桑拿房和一座涼亭。有一個可以比賽用的正規網球場,還有半個籃球場,還有後花園的許多樹木。這是我見過最大的私家別墅了。不過因為房子太大人太少,她正準備賣掉。
Emy的保姆是印尼當地人,咖啡色的面板,個頭不大,大約30來歲。她是拿著學生簽證過來的,Emy負責她的全部學費和生活費,她負責家務和打掃衛生。Emy說一個保姆從讀高中到大學畢業,大約七八年,全部費用她出。大學畢業後回去找工作,嫁人。每一個保姆最終都對她跟女兒差不多,就算是乾媽吧。這種模式的保姆也是我第一次見的。
後來Emy賣掉了這所大房子,到city的情人港旁邊買了個二百多平方米的公寓,270度海景房。有了微信以後我們的聊天就更多了,她常常發一些照片給我,告訴我她一家的生活。現在又在北區重新換了別墅,跟小女兒住在一起。看著她永遠都那麼漂亮,那麼開心,一家人融融樂樂真為她高興。疫情過後我如果再去澳洲,一定去她的新別墅做客。在異國他鄉有這麼一位美麗優雅的朋友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