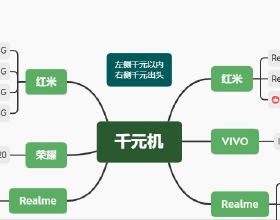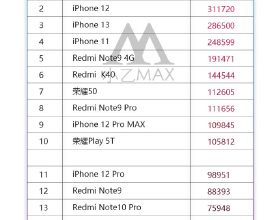【凡愷看天下】黑色的土地之一:
——生下來就心胸曠達的人,我想是沒有的,他必須經歷過幾次這樣的生死煎熬,才能真正地變得達觀和寬容,以平靜的心,去面對不平靜的生活。
死裡逃生是一種幸運,需要你去面對死亡的時候,你不苟活,則是另外的一種幸運。
人生就是一種旅行
· 周凡愷
我是個東北人,永遠都是。我22歲入關,在京津地區生活了多半輩子,至今鄉音未改。我收穫無多的耕耘,以及我青春的汗水,多一半都撒在了我的第二故鄉,對此,我沒有疑議,別人更不會有什麼疑議。我並不為此後悔。
我是一個活得很隨意的人,生來喜歡到荒僻的地方遊走或曰野逛,用現如今流行的詞彙來說,就是旅遊。所不同的是,旅遊多是扎堆兒,要去亂哄哄的景點兒打個卡,要住象樣一點兒的賓館享樂一下,要去品嚐品嚐當地的小吃與美味佳餚,當然還有就是常常要被旅行社宰上一刀。而我不會被宰,我好靜,啥地方沒人便往啥地方鑽,能有個草棚子住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從不否認,幾十年來,我的這種遊走,最多的還是我的東北——那片讓我深深眷戀與牽掛著的黑色的土地。
哈茲裡特在他的《談旅行》一文中曾說:旅行之妙在於思考和感受之自由——絕對自由,隨心所欲。他還說,在房間裡我能享受人的陪伴,但是到了戶外,大自然就足夠做我的伴侶了。這個外國佬講得十分精到。我以為哈茲裡特是一個真正的行動思想者,他在漫漫的長旅中悟出了很多道理,非吾輩所能企及,但有一點也許被他忽略了,那就是旅行中時刻面臨的窘境和危險,正像一個人在其生命旅途中肯定要遭受一些坎坷和失敗一樣,因而我可以斷言,哈茲裡特說到底也只不過是一個在城市中住膩了的人,他只看到了自然的優美而無視它的兇險。
我註定了只能是一個普通的旅行者而不是一個執著的探險家,就連一般的冒險也談不上。雖然我對這些事情有著濃烈的興趣、嚮往與尊重,可一旦牽涉到身家性命,我還是要轉一下心眼兒,在心裡敲上一陣小鼓兒。所以當年四川的堯茂書融入長江,河南的郎保洛命喪壺口,上海的餘純順魂斷大漠,等等等等諸如此類,我的心立刻一片黯然。我會為此沉默很久也思考很久。我知道我對大自然中隱藏的陷阱並非絕對的恐懼,我的沉默所包含的內容很散亂,我所想的問題也多一半還是有關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以及我自己的苟且和另一類人活著的無聊乃至令人作嘔的下作。
當然,統一的行為方式也十分地可怕。無論在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的美學論著中,所推崇的均為變化和創造,我所學專業,是中外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後來我有興趣一直持續研究的,卻是中國書法史、中外哲學史、思想史和美術史。所有的心得都會告訴我,千篇一律永遠是蒼白而沒有活力的。遙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朋友們在一起聚會時,所談的話題會很多,思想也是五花八門甚至發生強烈的碰撞,如今則大不相同了,除了談怎樣賺錢,至多再加上一點兒不雅的笑話,或者比比誰住得房子更大誰的兒孫更有出息。有人說這是一種進步,可這種進步讓我覺得很乏味。從我個人來講,我並不拒絕這些東西,但如果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就叫人覺得十分可怕十分恐怖。
許多年來,我始終沒有徹底地瞭解自己,也沒有搞清楚別人,但有一點我可以說,我這個人是缺少趨同心理的。我這樣講,並非美化自己。我的確在很多事物上極難與別人溝通並且達成一致,譬如在某些人為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拼得要死要活時,我更渴望的卻是出遊,花最少的錢,吃最便宜的農家飯菜,感受最下層人的生活,過最不受人羨慕的平常日子,然後再喝上一口小酒,寫一些我想寫的文字或者我想畫的畫。當然這得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必須以自己誠實的勞動,掙夠我足可以維持最基本生存水平的銀子。我的這種想法在如今這個年代,也許很落伍甚至有點兒可笑了,但我仍不會去聽從勸導,我不管別人說我什麼,我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曾經讀過我的老同事侯軍兄的一篇文章,他很清醒地告誡文化人,在深港澳大灣區,他們所面臨的價值觀挑戰以及由此帶來的心靈痛苦。我雖然不是文化人,但我想侯軍兄說得絕對是實話。
談到以往生活中的種種歷險,我不想就一些具體的細節糾纏過多,那樣會有人說我賣乖:你真的有過這樣的經歷麼?所以我還是閉嘴為好。但這篇小文要談的,只是我遇險之後的心情,說說心情總還是可以的。
近些年來我彷彿總是在不停地旅行。有時是在夢裡,有時是在真實的生活裡,有時走得遠有時走得近。旅行只要安全不出太大的問題,於家人於自己,總會讓人感到愉快的。我之所以旅行,並不是玩心太盛,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有點兒牽強。但我於潛意識中,似乎總是在為自己尋找一個更好的去處或曰歸處。實際上每個人都在為自己找一個更加滿意的地方,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卻始終找不到。
大概十幾年前,那天我搭乘一輛破爛骯髒的交通車穿梭於鄉間。那是魯西南的鄉間。我雖然生於東北的長白山下,可我的祖輩兒,卻都是純正的山東人,我父系的故土是臨沂,我母系的家鄉是青島。因而踏勘與尋訪祖輩兒的足跡與續寫家譜,也就成了我的業餘工作之一。在那輛車上,人們吐痰罵髒話,為了一個座位大打出手。車過一個無人看守的鐵路道口兒時,那輛破車竟一下子趴了窩,偏偏這時又有一列火車高速駛來。我記得自己的第一個反應是:完了。許多人想砸碎了車窗跳下去,但那是來不及的。我閉眼坐著沒動,腦子裡一片空白。好在司機是個恪盡職守的人,就像《泰坦尼克號》中的那個船長。他沒有丟下整車的人自己逃命,而是一直進行著最後的努力。在火車與汽車就要碰撞的一瞬間,車向前拱了一下,這一拱,全車的人就都得救了。不過在那一刻,大家都以為自己死了,車裡靜得嚇人。幾分鐘後,終於有了哭聲,人們才把丟了的魂兒從另一個世界找回來。就是在這一眨眼的工夫,我似乎想通了很多年也沒有想通的一些人生道理。生下來就心胸曠達的人,我想是沒有的,他必須經歷過幾次這樣的生死煎熬,才能真正地變得達觀和寬容,以平靜的心,去面對不平靜的生活。
這樣的經歷,還有很多。比如在無邊的大海上夜泳,突然就沒有了一絲的力氣,而海岸卻很遙遠,感覺自己再也回不到那片迷人的燈火之中了;還比如在仲夏的黑龍江裡,從船上一個猛子紮下去,我的頭卻觸到了水底的冰層,暈頭轉向地被江水衝到了俄羅斯;再比如在一片沒有人煙的荒野身陷沼澤,望著藍天白雲卻又無力自拔……
而最近的一次遇險,也是緣於旅行。那時我帶著幾位朋友去我的故鄉長白山,連日大雨,我們在一個停車場碰上了泥石流。泥石流來得十分迅猛,誰都沒有心理準備,因而在場的人全都手足無措狼狽不堪。大夥兒在野徑上狂奔,就如奧運會上的百米賽跑,人人都成了牙買加的那個博爾特。我並不是最後一個逃脫險境的人,但距離泥石流的峰頭也僅有十幾秒鐘的時間,亂石不斷地從我身邊飛過,用“抱頭鼠竄”來形容我此刻的形象,是一點兒也不為過的。這場災難的結果,是一人喪生,還有一些停在那裡的空車被埋在泥沙之下。
回安圖的路上,我的心情可以說是寧靜的。二道白河鎮的炊煙已經嫋嫋升起,斜陽照耀著暮色中的白樺林松樹林。路邊的池塘中,有一片連著一片的揚著頭的紅色蒲棒,在秋風中搖曳。我很奇怪自己在長白山林區居住了那麼多年,怎麼第一次注意到這些蒲棒呢?
我在心裡說:蒲棒真好!
當然,我在這一刻也琢磨過關於生與死的問題。說句心裡話,此前我就已經無數次地考慮過這個問題。我不否認我曾有過的消極,而且至今我也沒有活得更加積極。但我已經懂得了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哪些東西對我的生命有意義哪些東西毫無用處。我想我不會因為這些歷險就停下自己的腳步。
人生就是一種另外的旅行。
死裡逃生是一種幸運,需要你去面對死亡的時候,你不苟活,則是另外的一種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