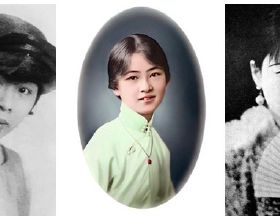作者:陳新泉
引子:故鄉已與我漸行漸遠了。我在故鄉的時間與我年齡相比只佔七分之一,除去有了記憶之前的矇昧期,也只是寥寥數年,但這並不影響我對她的感情,只因“釣於斯遊於斯”的關係,我們遂成相識,雖已離別多年,但總還是心心念念地想著她……
前幾年,我寫了一篇關於官塘堰村簡介,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整理、充實、完善,以事實說話,儘可能還原歷史真面貌,現饗廣大村民。(文中插圖:夏清龍 攝)
一
沿著巢湖北岸烔中路一直向西蜿蜒行駛,距黃麓鎮大約1.5公里處,有一口波光粼粼寬敞的水面便會映入你的眼簾,這就是當地人稱的“官塘”。官塘最早是靠北頭的那邊,只是一條小洩水溝,塘的中間青草萋萋,一條醒目的土路從塘中穿過,再往前回憶那都是一片沖田。臨近烔中路的那一頭和中間的水面,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突擊搶修烔中路,加之,歷經多年的拓寬與興修水利,才使塘的規模不斷擴大,成了現在的樣子。
在塘壩上住著一個古老且美麗的小村莊——官塘堰。
官“塘”與“村”有著密不可分的因緣,幾百年來風雨相伴,與村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
官塘堰村最早開始出現芻形的是在明代後期,幾戶劉姓人家居住在人稱“四鄰之瓴”的丘陵高坡上,四面丘壑起伏,人們形容天下起雨來,村莊流出的水,就像瓶子裡的水從頂端傾瀉而下流入鄰村的屋脊上。村裡老人還說,從烔煬下火車,向西一望就能看到村莊的大樹,可見村莊地勢之高。
因姻緣關係,陳氏從第五代移居加入,距今已有600餘年的歷史。陳氏入住官塘堰村後,主要集中居住在村北部的張家巷和大巷附近,土地分佈在西和北兩個方向。村莊西面的剪子山是陳氏最早祖墳之一,荇秧塘和方塘是陳氏的主要糧倉之地,為了提高官塘的行洪與蓄水能力對全村來說很重要,但對陳氏家族來說就更為迫切了。清代中期,陳氏第11代應和、運和倆兄弟同時為官,特別是運和身為五品銜,權顯位重,為官之時正是清朝的經濟復甦期,為了炫宗耀祖,造福鄉鄰,在家鄉積極疏浚塘壩,使原本的小水溝開始有了塘的基本形狀,塘也因此而得名,被稱為“官塘”,住在塘壩上的村莊也就順理成章被稱作官塘堰村了,現簡稱官塘村。
應和和運和兄弟倆,雖然離開我們有一個多世紀,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他們卒後仍葬在官塘堰村的大張墳。童年時期,我經常隨牧童去放牛,大張墳一個個墳頭就像一隻只蒙古包高高凸起,遍地綠草叢生,如同一個偌大的放牧場,牛往那一放隨意吃草,然後牧牛人分成幾幫,玩起躲迷藏。我清楚地記得在墳場中間有幾個特別大的墳包,面向朝南,紫氣東來,顯的十分特別,聽說是有錢人的大官人的墓,那時候年幼不懂得其深奧之意,只是聽聽而已沒有深究。後來離開村莊,聽說在開展平墳運動時,村裡實行大食堂,挖出來的棺木統統作為燒鍋料,說這幾座墳墓挖出來的棺木與眾不同,又寬又厚,還能辯出顏色。像這樣的棺木規模在舊社會沒有一定的身份等級是不可能的,足以說明,這些墳就是他們兄弟倆人的,是必定無疑的。
官塘,其實就是兩邊的崗丘突起在中間形成的一塊空曠之地,在它的上游是方塘,方塘是攔在兩丘源頭之間的一個水塘,它的下游依地勢又形成一塊塊沖田,到了汛期水沿著沖田直瀉巢湖。陳氏家族的田地分佈在兩邊丘崗上,完全靠一口方塘難以灌溉,只得在靠水井這頭再攔一壩,使上游的水在此儲蓄,形成一條深水溝,經過疏浚成了一口小水塘。
沿著古井那頭的塘埂,有一條彎曲的深水溝痕跡依然可循。夏天游泳厚厚的淤泥沒過你半個小腿,出了這條灣溝,到其它水面就沒有這種現象了,只是一層淺淺的表層泥,兩者區別明顯。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為了保護堤壩不受風浪衝擊,進一步提高官塘的蓄水能力,村裡的第四生產隊,在塘的北頭(古井這頭),對塘又作了加深、加固,還修了一條擋風堤,使官塘半個多世紀以來遇瀾不驚。
擋風堤修建後的第二年,楊崗村同時提出對官塘和旱塘的官轄權要求,後經公社調決官塘歸楊崗村,旱塘仍然歸官塘村,從此徹底改變了官塘的歷史權屬。
二
村子主要是由劉、陳兩姓組成,他們的祖輩都是從明代江西瓦屑壩遷徙而來,現在的村莊應該是移民後代的組合村莊。
不大的村莊由東向西依次漸高,從東南方向遠眺,似一把展開的精美摺扇,樹木遮映,青磚黛瓦,高低錯落,濃墨相宜。環繞村莊的有彎塘、大塘、奶奶塘和小方塘,四口塘像四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村邊,是活化村莊空氣的“肺”。
整個村貌可以用四句話概括:“ 東邊一口塘,南邊一片房,村中立有三根柱,頭上頂著一橫樑。”“一口塘”是指村前的大塘,是全村最大的一口煙火塘。水面開闊,水量充沛,承載著蓄水、灌溉、排澇、消防和日常浣洗等功能,還是天然的游泳場,無論是遇到乾旱還是洪澇都要在這裡匯合分流,保障著全村人的生計安全。“南邊一片房”是指在村最南方向至大塘沿一帶的明代建築風格的房屋。清一色黑灰小磚砌的牆,屋上蓋的是小灰瓦,屋內是敦實的七木落地的柱子,特別壯觀。有的人家在房屋橫樑與立柱的卯榫之間,還藏有一塊紅布,上面明確記載著在明代的上樑時間,一直儲存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三根柱”是指村中的三條主要巷子,即南邊巷、張家巷和北邊巷。三條巷子呈柱狀豎立在村中心,是“扇面”中的龍骨,頂天立地,穩如泰山。“一橫樑”是指大巷,一巷橫穿南北平行座落在“三根柱”子的頭上,連線、平行、固基,其責之重大不言而喻。這樣的地形在風水學中稱,利於藏風納氣,既利於排水又寓含步步高昇之意。
四條巷子,其中有三條巷子只要一聽就知道是以方位命名的,只有張家巷會引起人們的孤疑。究其原因,陳氏家族第5世先祖與劉姓姑娘喜結連理入住官塘堰村後,頂替了張姓舅舅的支,從此,陳姓被改成張姓,大家同住在一條巷子也就稱為張家巷了。到了民國後期陸續又被改回陳姓,但至今仍有少數在外地謀生落戶的,他們仍然還姓張。
張家巷是居三巷之中,立在村中的最高處,前臨波光粼粼的大塘,銀光四射,背靠橫樑大巷,穩如泰山。過去的張家巷兩頭門樓高聳,青石護階,門口還放有一石臼窩供村民享用,晚上為防不測還可以把兩頭大門栓上。與張家巷相鄰的一處房產,一個門朝南面巷,另一個門朝大巷,裡面有幾個庭院,院內植有天竹、桂花等名貴花木,堂廳裡牌匾高懸,十分氣派。當時,我與幾名同齡相仿的侄子經常在這裡玩耍,把高懸的匾放到地上玩,後來聽說被幾戶人家分掉打傢俱了,令人十分惋惜,現在想想牌匾上題寫的幾個字,極有可能就是陳氏家族的堂號。這些房屋也是陳氏家族在村子裡最早的明代建築,可惜的是在民國時期毀於大火,殘存的建築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繼拆除。張家巷至今還在,只不過巷道變窄,兩頭的巷口大門早已消失,兩邊的房屋已變成磚牆。
村莊呈“九龍攢珠”中的剪刀式排水格局。村中每條巷子房屋相互連在一起,每戶人家都有一條地下暗溝相通,透過暗溝把水流入大塘。
在村北邊有一處較大的竹園,園外都是小水溝,裡面長滿蝦草和藕,每到夏季,微風習習,荷花盛開,荷葉和蝦蟆輕輕搖曳,引來蜻蜒盤旋,恰似一幅靈動的水墨畫。在相隔幾十米的另一處,還有一處與稻田連著的小竹林,兩處竹林組成了村莊一道綠色的屏障,一年四季翠綠,是村莊的天然氧吧。一到晚上鳥兒棲息在竹枝上,嘰嘰喳喳,竹葉發出瑟瑟的響聲,在風的伴奏下,演繹成一場浩大的和聲音樂。在西北角還有一處桃園,四周被一層厚厚的荊棘和野藤圍的水洩不通,只有一條路通向主人家的門口,門前樹影婆娑,還有一口小水塘,塘邊就是桃林,三月一到,滿園桃花開的奼紫嫣紅,煞是好看。竹林曾留下我童年的足跡,桃園的藤條上有我們蕩千秋的身影。
村莊的竹林、桃園、小河溝,相映生輝,不是江南勝似江南。遺憾的是這幾處風景寶地,在歲月的流逝中也不知不覺地消失了。
三
環視村西北,與村遙遙相峙的另一處崗巒上,人稱“屋子框”,據說以前住的是趙氏人家,當時是觸犯了朝廷還是其它原因?不得而知,村莊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消失了,留下的是一片廢墟和靠近官塘上游的一口水井。在留存的土地上,起初殘存的房屋框架依稀可見,因此人們顧名思義把這個地方稱作“屋子框”。“屋子框”變良田後,有幾塊地的土壤與周圍地裡的土壤不同,它呈白色,在物資匱乏年代,許多人家買不起石灰粉牆,就到“屋子框”地裡挖白土回家粉飾房屋,粉出的牆壁既細膩,顏色還近似白石灰,非常奇妙與美觀。留下的一口水井也很神奇,井水甘甜,冬暖夏涼,是全村人的生命之泉,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家家戶戶用上了自家打的水壓井後,水井才隨之廢棄。原來一直傳說這口井,就是遇上乾旱也沒有乾涸過,還說這井水是來自西黃山的泉水,水勢洶湧井底是用一塊石磨壓著,水是從磨眼裡流出來的。1963年井體坍塌,才揭開了這個謎底。當時大隊基幹民兵們利用義務勞動重修了這口井。搶修時,我和一幫小朋友們就站在井邊圍觀,他們拉著三角架上吊環的繩,打幹了井水和淤泥,井底祼露出一塊凹形的鍋底,板結的黃泥粘土光滑結實,汩汩的清水就是從這地層中滲出來的,當時大家還做了一個試驗,就是站在旁邊幾分鐘就可以盛上一桶水,可見滲透量是非常之大,並非是來自西黃山的泉水。每逢夏季人們排著長長的隊伍來挑水,有時鄰村的井都幹了,這口井也沒有幹過,他們也來挑水。社員們在田間勞作,生產隊都會派人挑上一擔水放在田頭供人們飲用,清冽的井水甘甜可口,透徹心涼,是防暑降溫的天然飲料。那時,幾乎家家戶戶都不燒開水,口渴了拿起葫蘆瓢就到水缸裡舀水喝,也沒有聽講人生病。
據傳,村裡以前也有一口水井,是在村中心張家巷的東門口前,靠近德興老人西山牆的地方,相傳當年有一婦人尋了短見,從此,井填實廢棄。
村莊崗壑爭秀,阡陌縱橫,草木茂密,起伏的崗巒形成旗杆塘、夏家塘、方塘、荇秧塘、大塘五大塊沖田區。幾十口水塘星羅棋佈的散落在其間,構成了村莊詩意般的輪廓。
每個水塘的名字都有著它特有的個性。按形狀大小的:彎塘、大塘、小塘、方塘;按姓氏和性別的:夏家塘、奶奶塘;按塘深淺和生態原狀的,旗杆塘、黃泥塘、荇秧塘、旱塘,還有一個與村名直接相關聯的——官塘等。清澈的塘水如汩汩的乳汁呵護、滋潤著這方土地,養育和繁衍著村莊的祖祖輩輩。
五大沖田區是優質糧食和經濟作物的主要生產區。崗巒地主要種植一些耐旱農作物。幾百年間,村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過著清貧且隨意的生活。
四
解放前,村裡有三人在國民黨部隊服役,有二人到了臺灣,還有一人解放後被分到四川某縣水利部門工作,1964年夏季,實行責任田時返鄉務勞,直至後期落實政策又重返四川工作。到臺灣中的其中一人,改革開放後曾返鄉探親,之後與家人失去聯絡。
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期間,有識青年踴躍報名參軍,他們在戰場上留下了不凡的身影。參加新四軍的有劉德義、劉德金、劉德斌。劉德義從小瞞著家人趁在外放牛,跑到江南參加了新四軍,後來又參加了抗美援朝上甘嶺戰鬥。有次他回鄉探親到我家玩,給我說起他參加上甘嶺戰鬥的故事,他說:在上甘嶺戰鬥中,他在坑道里蹲了四十多天,條件異常艱苦,他們日夜堅守,坑道外面的山體被敵人炸成一堆灰土,都有好幾尺深,戰鬥打的異常慘烈,可我們志願軍將士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最終打敗了敵人。回國轉業到公安部門工作,後來又輾轉到淮南市工作。劉德金從三野回到村子裡,一直默默無聞,孤身一人,他從三野還帶回許多由陳毅和粟裕簽字的證書。劉德斌自從離開村莊後,一直杳無音訊,成了一位無名英雄。參加入朝作戰的還有劉錫祥,回國後被分配在合肥糧食系統工作,實行責任田時辭職回鄉務勞,直至終老;陳子祥(陳嘉珍繼子)參加抗美援朝回國後,成了一名團級幹部,轉業後回到自己的祖藉。
從村莊還走出了一批黨的優秀幹部。陳嘉定在解放前隨父做裁縫,在外面接觸的人比較多,他利用這一特殊身份,成了一名新四軍秘密地下交通員,負責為新四軍傳遞情報。有一次新四軍有個重要情報急需送出,各交通要道已被敵人把守,無法通行,他受領任務後,急中生智,把清涼油的小盒子掏空把信放在裡面,才順利透過檢查,使信及時送達指定地點。1949年新中國一成立,他就成了首任桐蔭鄉鄉長,後調入烔黃區工作。1956年在他擔任烔煬區委書記期間,在烔煬苗圃接待了回鄉探親的李克農將軍,幫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謝嫂子,圓了他多年的心願,臨別時李將軍送了他一張個人照留作紀念,1962年李將軍溘然去世,由於事急當時巢縣刊登訃告找不到他的照片,便派巢縣日報社攝影記者何競成(是陳的老部下)找到陳嘉定取走了這張照片。此照片後來經過複製,廣為流傳,現在許多場合用的仍然還是那張照片。陳嘉雲也是建國初期參加工作的,在1957年受到政治衝擊後,被分到兆湖農場,文革後期得到平反昭雪,重返公安戰線,後被調入法院系統退休。劉德清自從參加工作,一直在勞改系統工作,成了一名勞改系統的幹警。
解放初期,全村約有八十餘戶人家,人口近350人,主要是劉陳兩姓。後來,村裡陸續來了其它三個姓氏。一戶吳姓是從含山縣來村做理髮手藝,娶了劉姓姑娘在村落戶;另一戶李姓做皮匠手藝,是從烔烊前李村隨姐姐在村落戶;還有一戶查姓也是娶了劉姓的姑娘後在村落戶的。現在李姓和查姓已不在村裡居住,吳姓還有兩戶後代。
1951年8月,以本村名設立了官塘鄉(周邊村莊都在所轄範圍之中),鄉政府設在段曹村大祠堂。
當時,村裡成立了農民協會,會長是劉慶釗(劉德義父親),他高高瘦弱的個子,經常穿著一件長袍大袿,說起話來語句不太連貫,到了冷天習慣於兩手攏在一起走路,鼻尖上總是掛著一滴水,村民都喊他“老會長”。因為他屬於貧僱農,兒子又是新四軍,村裡就把去臺灣一戶人家的房子三間加二廂主屋分給了他,剩下前面的武架子分給了李皮匠。村裡還有三名共產黨員,我的母親張宗秀、劉慶球(劉德珍之父)和楊尊玉(陳嘉鎔之母)。那時候村子裡的事,主要是靠農會長、幾名黨員和一批積極分子維持。剛解放不久,面臨的事情又多又繁。開展互助組、動員群眾入社、訪貧問苦、社會聯防(包括打更)、舉辦掃盲班、調解群眾糾紛、配合政府抓中心工作、抓農業生產、開展社會救助、組織文藝宣傳開展群眾性的娛樂等項工作,千頭萬緒,沒有報酬,但大家心都非常齊,積極性非常高,全身心地為村民服務,各項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這股凝聚力主要是來自黨員和骨幹分子們以身作則和無私奉獻。我清楚地記得,母親和骨幹們,經常晚上到鄉政府開會,散會都是在深更半夜。白天大家還要忙著農業生產,晚上組織辦夜校開展掃盲,登門做工作,發動群眾,有的家庭發生矛盾母親和骨幹們還要去幫助處理,整天忙忙碌碌,毫無怨言。我家和骨幹們的家經常是出一屋進一屋,不少婦人流著淚到我家向母親傾訴,母親經常為她們出主意想辦法。
1957年全國基本完成高階合作社之後,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則改成生產大隊,我村獨立成立大隊,分設四個生產小隊,首任書記是劉慶球,楊尊玉是婦女主任。這中間還有幾年,我村和劉疃、楊崗同屬劉疃大隊,當時正值“一平二調”,我村與這兩個村子邊緣接壤的一部分田地,分別被劃入劉疃和楊崗村。文革期間的大隊書記是劉恆雲,據我瞭解,先後在大隊任過書記的還有,劉振華、劉德雨、劉錫松。改革開放之後,歸屬黃麓鎮建中行政村。
官塘堰村民風淳樸,善良厚道是村民之本。全村崇尚學習蔚然成風。解放前,在村大場和張家巷、南邊巷都有私塾,耕讀文化有一定的歷史基礎。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村一下子有四人考入黃麓師範附中,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因為劉疃是個大村子也就考了三名。他們四人不顧生活艱辛,忍飢挨餓,每天往返幾十裡地到黃麓師範附中學習,在寒冷的雨雪天氣裡穿著綁木屐完成了他們的學業。後來,劉德美成了省城的一名中學教師,直至學校負責人;陳嘉全畢業之後,進入煤炭行業工作,成為一名高階工程師。正是這種“綁木屐”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開創了全村人良好的學風,薪火相傳,使貧窮的鄉村從此有了大學生、中專生。
從解放到現在,全村湧現出三十餘名小學和中學教師。最早的教師應該是陳嘉珍夫婦。陳嘉珍最早在家教私塾後到東北,從東北迴來後和妻子成了桐蔭小學(現在的黃麓小學)最早的老師之一。全村有中、小學教師三十餘人,這在一個自然村是不可多見的,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教師之村”。
村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匠人多,有裁縫、木匠、理髮匠、機匠、皮匠,最多的還是蔑匠和瓦匠。有些匠人的家庭幾代人都幹著同一種手藝,是一代傳給一代的。舊社會流傳“江南好行錢,一去二三年”。江南竹木多,是這些匠人施展才能的好地方,那時交通不便,許多人到了江南後,時間長了也就在那裡定居了。
改革開放給全村人注入了新的活力,廣大青壯年積極走出去參與國家各項經濟建設,使村莊面貌有了“質”的提升。在村莊裡,人們雞犬相聞,和諧相處,就像一家人。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全村人攜手同心,與時俱過,奮發努力,捐資修路。2013年我和劉德美、劉衛兵、劉錫水、陳剛、陳金生、陳斌、劉二林、陳夢平、陳光再次捐款,從巢南購得一塊大石碑,我請書協主席胡克勤撰寫了村名,然後鐫刻在石碑上豎立在村口,讓村人永遠銘記自己的故鄉——我的村莊。
現在村莊每條巷道相通都與主路相連,一個清新、整潔、優雅的環境正在形成。為此賦詩一首:
四鄰之瓴甚為高,毗連藍天遨雲霄。
官塘拍岸驚濤起,瓜瓞連綿世代驕。
最憶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