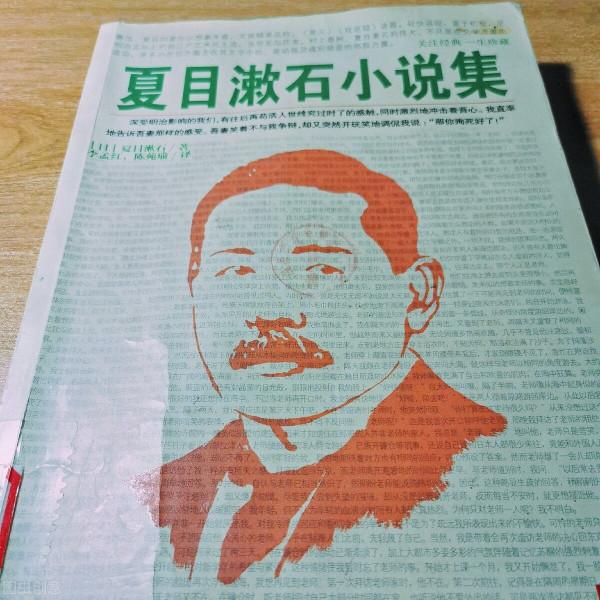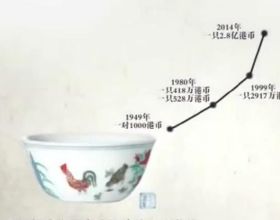《百年孤獨》作者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說:日本作家,全都是些瘋子
馬爾克斯《回到種子裡去》一書是這樣說的:
幾年前在巴黎,作家阿蘭·若弗魯瓦給我打來電話,說想介紹我認識幾位日本作家,他們現在正在他家中。那時候,我對日本文學的認識,除了上高中的時候知道的一些感傷的俳句之外,就是谷崎潤一郎幾篇翻譯成西班牙語的短篇小說。
實際上,我對日本作家能算得上深入的瞭解是,他們大家,或遲或早,總歸是要自殺的。
我第一次聽到川端康成這個名字,是在一九六八年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當時我試著讀一點兒他的東西,可很快就睡著了。過了沒多久他就剖腹自殺了,和另一位著名作家太宰治一樣——這位則是在幾次失敗的嘗試之後,於一九四八年自殺身亡。
比川端康成早兩年,也是幾次自殺未遂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也許算得上是在西方世界名氣最大的一位了——在對自衛隊士兵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之後切腹自盡。
所以,接到阿蘭·若弗魯瓦的電話,我腦海裡首先出現的就是日本作家這種對死亡的崇拜。“我非常樂意去,”我對阿蘭說,“只要他們別自殺。”
實際上,那天沒有人自殺,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那天我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全都是些瘋子。
難得的是他們也都同意我的觀點。“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想認識你。’他們對我這樣說道。
其實,別說那些自殺的日本作家了,就是夏目漱石,這個善終的作家也有點瘋。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是夏目漱石妻子夏目鏡子對夏目漱石的回憶錄。
讀完此書,會發現,夏目漱石是那樣的與眾不同,簡直就是一個奇怪的人。鏡子亦如此說。
他去與鏡子相親之後,他的哥哥們問:“那家小姐怎麼樣呀,中意嗎?”夏目答道:“牙齒很不整齊而且還髒兮兮的,但居然並不刻意隱藏,還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這一點特別讓人滿意。”哥哥們聽了便取笑道:居然看中這些莫名其妙的地方!鏡子總結,所以說他真是個怪人。
鏡子說,走在路上也好,進戲園子也好,夏目隨時隨地都能一眼發現漂亮女人。而且還不僅僅是女人,進舊貨店時也是這副腔調,不管看什麼眼光都很敏銳。在家附近的大路邊,有一家紙店。紙店的老闆娘在那一帶商家裡,少見的苗條白皙。夏目因此特別中意。當然,他並不會因此有什麼其他想法,但每次散步的時候,就要溜過去悄悄瞧上幾眼,回家後就說今天又看到了,如何如何。然後,也分不清他是開玩笑呢還是當真,跟孩子們說:那個老闆娘是你們的父親大人喜歡的女人,你們路過她店門口的時候,要記得恭恭敬敬鞠躬敬禮。他說這話時的口氣倒是全無卑賤感,但是這件事,還不僅僅是對孩子們,對門下弟子也大言不慚地吹噓過。即使我跟他說:吾輩之流雖說算不上美人,但你這樣說話,我豈不是跟個幽靈一樣,被你視若無物?可夏目照樣回答說:就是喜歡那種型別的嘛!
夏目心情好的時候,總是笑嘻嘻的,犯起毛病時——他有神經衰弱和胃病的老毛病,也是相當折磨人。鏡子說:我們如此提心吊膽,謹慎至極,絲毫不敢惹是生非;而夏目則拼命豎起耳朵疑神疑鬼,在腦子裡虛構種種妄想,刨根問底猜測著種種無稽之談。用他那對極為敏感的耳朵,蒐羅所有的聲音,然後再給它們新增上種種離奇的想象,無止境地在腦子裡描述各種異想天開的事。女傭咽喉痛,嗓子啞了。夏目說:“為什麼這副聲音?你給我說大點聲來聽聽。”不管嗓子多麼嘶啞,吊起嗓子大聲說一兩句話也不是什麼難事,因此女傭發出的聲音相當大。夏目一聽,頓時就怒了:“瞧!明明可以大聲為什麼要假裝不行?你這傢伙是在撒謊!居然搗鬼,豈有此理的傢伙!”他不管看什麼都覺得人家在搗鬼,只要神經衰弱,他就會出現這種怪癖,然後對那些“搗鬼”行為極度厭惡。
或許是因為作家本來就容易古怪。比如,博爾赫斯好不容易與相愛多年的女友結了婚,結果不到半年就離了,理由是因為他妻子睡覺時從來不做夢。博爾赫斯還解釋道:每天做噩夢是可怕的,但每天不做夢也是可怕的,兩者可怕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
麥家說:一個作家,他優秀的程度和他古怪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難怪有人說,作家是可憐的,與作家一起生活的人也是可憐的。
馬爾克斯還在書中舉了個例子——川端康成的《睡美人》。
它講的是京都郊區的一所怪異的宅子裡發生的故事,一群有錢的老頭付上一大筆錢,只為了以最精緻典雅的方式享受他們最後的愛:這個城市最美的女孩子,被麻醉後赤身裸體和他們躺在一張床上,任由他們徹夜觀賞。他們不能弄醒那些女孩,甚至不能觸碰她們,當然,他們也不會起這樣的念頭,因為這樣一種暮年消遣最純粹的滿足就在於能在她們身邊做上個好夢。
是夠變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