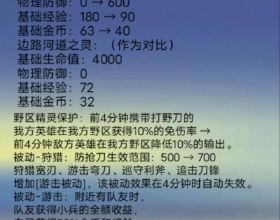於賡哲 著
中華書局
【讀書者說】
傳統中國醫學史幾乎都由醫學專業人士撰寫,以總結“歷史經驗”為現代臨床診療提供參考為主要目的,所以他們的成果往往只在醫學圈內流傳,不為主流的歷史學家重視,更不用說走進大眾視野了。
因為專業侷限,科學史的寫作確非“行外”人士所能輕易染指,缺少醫學訓練的學者很難準確把握疾病的預後轉歸,深切討論醫學思想的變化發展,判斷醫療方式在臨床表現上的優劣,於是留下一些不著邊際的隔靴之論;但另一方面,傳統的醫史家則抱守醫學的“一畝三分”,不善於把醫學事件還原到歷史場景中去體察,看不見醫學之外因素如何影響醫學,甚至弄不清決定醫學走勢的真正原因。就此意義而言,二者結合應該大有用武之地。於賡哲教授致力於此,《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從疾病到人心:中古醫療社會史再探》以及新著《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皆是中古醫學史研究的力作。
回溯真實的醫學、醫療面貌
於賡哲認為,分清文獻之“自我視角”與“他者視角”是解讀醫療文獻的關鍵之一。如果把“自我視角”理解成醫者對自身角色的塑造與建構的話,“他者視角”則指在其他角色眼中醫者與醫學的形象。研究者以此進行醫學文字分析,就不會侷限於文字的醫學內容本身,而能透視文字撰寫者的立場和動機,回溯接近真實的醫學、醫療面貌。
循此思路審視中古醫學生態,於賡哲的幾本著作新見迭出。他在書中提出,中古時期的官方、民間醫學的區分,本質上是人為製造的問題;文字話語權所代表的官方醫學不僅沒有成為“主流”,甚至未必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官方醫學”。據於賡哲觀察,民間醫學始終是主流,而官方居於被動從屬地位,這其實是對“官方醫學即意味著時代的主流,民間醫學僅僅是附庸”觀點的一次革命。在《從疾病到人心:中古醫療社會史再探》第二章“由天聖令復原醫疾令看唐代官民醫學分層”中,於賡哲明確提出,官方醫學體系之種種,主要是為了滿足醫療行政的需要,並未成為全社會醫學的代表。
按照傳統醫學史家的意見,醫學分科是醫學發展的必然,於賡哲打破了這一認知。他認為分科的出現不僅不能說明醫學進步的特徵,反而暴露出古代醫學發展中的弊端,即醫療技術保密。醫者之間不僅缺少學術交流,而且醫學本身也未按照普遍標準分科,教育方式侷限為極其單一的師徒、父子制。故於賡哲認為,分科並不是醫學發展的需求,僅僅是政府不能統合各種“異端”學說而已。透過對醫生地位的分析發現,限制唐代技術官的品秩,實質上是“不將醫者歸為士人”的歧視。
於賡哲對醫學融合的理解,用來解釋宋代醫學特徵非常有力。比如儒醫的出現其實是整個政治社會轉型的體現。因而我們能觀察到,宋代士大夫精英對醫學的熱愛遠遠超過以往的時代,在士大夫的唱和之間,醫學成為他們重要的交際紐帶。醫者好儒,儒者好醫並不鮮見。在社會階層發生巨大變動的轉型時期,醫學知識不再成為少數精英的專享,“儒醫”既可以是醫者的一種標榜,也可以是落魄文人為謀生計而預置的“人設”。
政府對醫學、醫政加大支援力度,醫藥學知識整理尤其突出,其中就包含對後世影響極為深刻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在於賡哲看來,儒醫與局方的出現可以理解為“士大夫醫學與平民醫學的合流,官方醫學與民間醫學的契合”。儒醫與儒學的全面介入,使中國階層發生巨大的變化,“局方透過行政力量和印刷技術等技術手段使得官與民,士與醫等各種分層得以糅合並且具備很強的操作性”。由此可以理解金元時期醫者在創立新觀點的同時,不得不面對局方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影響,在立說的標靶中,金元醫學家反對局方用藥是他們重要的基點。
傳統醫學史家通常按照斷代史的套路,從統治者如何加強統治的角度來解釋宋代的醫學發展與醫政措施,基本上沒有吸收中古歷史的研究成果。因此,討論宋代統治者加強醫政措施和支援醫學發展,多拘囿於強調統治者意志或儒家哲學的影響,這固然具有解釋力,但卻經不起追問,既然是加強統治的需要,可為什麼在宋之前又沒有表現出相同的醫學、醫政形態呢?很明顯的現象是,宋代的醫政措施幾乎覆蓋到縣,醫學文獻整理、醫學人才教育皆前所未有。通過於賡哲的啟發,很容易發現,加強醫政措施,僅僅是統治者為順應階層打破後的新格局,所做的統治技術性調整,換言之,即出於統治術的理由,將大量的散落民間,知醫懂醫的社會精英納入體制中來。
於賡哲在《從疾病到人心:中古醫療社會史再探》前三章中透過醫學、醫者分層考察,重新表述其對中古醫史的想法,後面數章中則體現專題研究的特色,即在熟悉的材料中,得出耳目一新的結論。他注意到,患者才是醫患關係的主導方面,因為古代醫生無法在經濟上獲得獨立,故高度依賴市場,富裕和權貴階層自然成為醫生的首選服務物件。於是醫生寧願放棄醫學原則,去迎合病人的要求;因為缺乏獨立性,醫學失去進步的動力。
從針灸流行的實際情況來看,北宋以前針法在民間的普及程度一直在灸法之下。於賡哲從技術角度分析認為,灸法簡單粗獷,易於操作,材料廉價易得,故在民間流行度高;針法操作複雜,學習的困難程度遠超灸法,實際使用並不廣泛。但從文獻獲得的資訊恰好相反,真實的原因是針法被官方醫學予以特別之注意,記錄者也樂於以誇張的筆墨,描述針法創造的種種“神蹟”,灸法則因為平淡無奇,遂被記錄者擱置一邊。此外,在韓城盤樂村宋墓壁畫的分析中,於賡哲討論了《太平聖惠方》與宋代社會思想中醫學文字化的傾向,回應了他之前對宋代醫學與階層糅合的假設。這些案例儘管不屬於傳統醫學史的分析,確為我們理解古代的疾病、治療方法開啟了一條可以操作的新路徑。
醫療史與大眾息息相關
於賡哲的新書《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其實是《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從疾病到人心:中古醫療社會史再探》兩書學術觀點的科普版。為了增強可讀性,拋開細密的論證,重新展現細節,歸納特徵,其中既包含了大眾關注的議題,比如傳染病與公共衛生,又討論了吸引大眾趣味的醫史問題,上至皇帝的疾病隱私,古代文化政治精英的死亡謎題,古代御醫的生存境遇,下至醫騙、醫托的陰謀手段。從毒藥到古代外科手術,兼顧學術性與趣味性,醫療史不光是學院學者關注的焦點,也可以與大眾息息相關。
《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全書十二章,如引言所說,“歷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思想的鉅變”,本書以“中國歷史上的大瘟疫”“中國古代應對瘟疫的辦法”作為開篇章節,既是題中之應有,也是對至今仍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陰影下的讀者閱讀心態的回應。
與疫情相關聯的還有第七章“現實或想象,蠱毒與瘴氣”。傳統文獻中經常提到的“瘴氣”,乃是晚近醫學社會學研究的熱門話題。在《從疾病到人心:中古醫療社會史再探》中,於賡哲以主流文化圈對非主流文化圈的認知分析為中心,分析主流文化圈擴大過程,以及南方知識分子階層的心理變化和話語轉移過程,並延伸到移民、交通、民眾心理、醫學觀念等問題,將“南方瘴氣”作為地域偏見對當時人疾病觀影響的例證。本書由此展開,結論更加鮮明:“瘴氣起自對多種南方地方病的恐懼,在口耳相傳中變得越發神秘恐怖,甚至成為南方不開化的象徵。但南北方的交融和南方最近一千年的長足開發,以及人們應對疾病能力的增強,使得恐懼感逐漸消退。而現代醫學概念對於瘴氣這個概念進行了最後的拆分,疾病終於迴歸疾病,再也不是神秘恐怖的符號了。”
於賡哲老師的研究更讓我們認識到,醫學知識的來源不只與醫學實踐相關,社會因素、時代的思想文化皆參與知識建構,因此知識社會學的理念對分析醫學知識成為可能。不過,如同科學內史的研究者所遇到的問題一樣,我們不能把所有的醫學知識完全還原成醫學之外的社會文化因素,畢竟醫學內部存在著不隨外在影響的“內在邏輯”,這種事實的存在,對醫史研究者提出兩點要求:第一,如何讓現代醫學的知識參與到歷史解釋中來,又要避免輝格史學預設的陷阱;第二,如何理解中醫疾病認知的侷限性,避免以中醫理論解釋中醫所導致的視野盲點,這對於醫史研究者來講,是對其知識結構、分析能力、理論總結能力的綜合考驗。
(作者:王家葵,系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鮮成,系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士)(本文圖片均選自《疾病如何改變我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