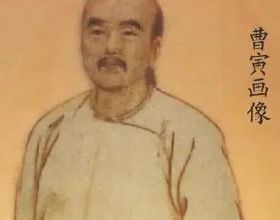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是嘉慶皇帝在位的最後一個年頭。這年春天,他準備動身前往清東陵祭祖,預計來回耗費一個月。
內閣上下為了這事很快忙了起來,在他們派筆帖式(官府中的低階文書)去六部領取行印,唯獨兵部遲遲拿不出來。
這行印平時不用,只在皇帝離京以後,才生效使用。雖只具備短暫調動全國兵馬的權力,這枚行印依舊是清廷重器。然而,已經動身一天的嘉慶皇帝,卻在路上得到快馬奏報:
皇上,大大大大大事不好了!兵部行印,它丟了!
庫丁發現兵部行印丟失,嘉慶急召鐵帽子王調查
兵部行印被發現丟失,是在這年的三月八日。那時候內閣來人,找兵部要行印,結果管理倉庫的官吏找來找去,愣是找不著。
兵部的其他印章都在,唯獨這枚皇上要用的行印不見了蹤影。這可是事關身家性命的大事,兵部上下頓時就慌了,發動人手把兵部上上下下翻了個底朝天。
結果發現行印蹤跡的是一個小小庫丁,名叫康泳寧。他在庫房角落一處落滿灰塵的舊桌椅堆裡,發現了行印——的盒子。
眾人又喜又驚,繼續翻找,卻只有這個空盒子,而不見兵部行印。最終確認:行印失竊了!
本來去祭祖,這嘉慶皇帝一路上高高興興,結果突然快馬來報告訴他兵部行印丟了,這事兒無異於後宮失火,叫嘉慶惱怒異常。
兵部行印是純銀製作,制式精良。盜竊行印融了當銀子花,這顯然是犯不著的事兒,犯罪成本也太大了。假如竊賊真是這個動機,真的只是把行印的價值當做等質量的銀子看待,那情況還不算太糟糕。
嘉慶腦中浮現出的是一個更加可怕事情:兵部行印在皇帝離京時具有調動兵馬的權力,莫非是有亂臣賊子,盜取行印企圖在他離開京城以後,舉兵作亂?
嘉慶得報之後餘怒未消,火速下旨,指派莊襄親王綿課、內閣大學士曹振鏞和吏部尚書英和帶著一眾刑部官員,偵破此案。
這莊襄親王綿課身份可不一般,他祖上是和碩莊親王,是清朝初年封的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之一,傳到他這裡已經是第五代了。
就在親王綿課率隊著手調查的同時,嘉慶皇帝的懲罰也降臨了:
負責督導兵部的內閣大學士明亮,被撤職五級,這還是嘉慶看在他年屆八旬的份兒上做出的決定;
兵部尚書戴聯奎、兵部左侍郎常福、右侍郎常英、曹師曾摘去頂戴調離,兵部尚書松筠留職以觀後效。(清朝六部尚書、左右侍郎各有滿、漢官員一位。)
嘉慶辦事這作風也夠雷厲風行的,案情還沒查清楚,處分決定就開始執行了。內閣大學士明亮,85歲還不退休,依舊在內閣掛名,結果丟印這事兒牽連上了,跟著一塊吃瓜落。
調查方向受誤導,嘉慶祭祖已回宮
兵部行印在庫房存放,丟了自然要找看管庫房的責任人。主事何炳彝和筆帖式慶祿這倆人,是去年秋天的時候,嘉慶皇帝結束圍獵,行印入庫歸還時候負責點驗的官員。
在威嚴的鐵帽子王綿課跟前,這兩個小官吏叩頭如搗蒜,堅稱自己當初點驗得明明白白,行印去年秋天入庫封存的時候,完好無缺。
既然如此,大學士曹振鏞等主審官便判斷,這行印是在封存之後在庫房中失竊的,與庫房有關的人員,都有盜竊嫌疑!
於是一眾兵丁、雜役都被捉來審問,兵部有個年紀頗大的老書吏名叫鮑幹,他經手兵部日常的事務,堅稱一切都經過程式,毫無疏漏之處。
盤問來盤問去,似乎這些小官吏都沒有盜竊的動機,最後倒黴的竟是率先找到行印空盒子的庫丁小康。
康泳寧被鐵帽子王力主大刑伺候,打得只剩下半條命。小康夠硬氣的啊,寧死不招供啊!然而,真是他偷得麼?
康泳寧知道,這行印根本不是自己偷得,自己不過是一個小小庫丁,掙得都是辛苦錢,吃十個豹子膽也不敢偷這玩意兒啊!實在挨不住打,康泳寧只好把別人牽扯進來,洗脫自己的嫌疑。
據他招供,同在兵部打雜的一對何氏父子,經常針對他,這事兒沒準是他們有意栽贓陷害的。何氏父子是兵部的雜役,不久前兵部庫丁補缺,小何競爭失敗輸給了小康,何氏父子就此和康泳寧結下仇怨,經常找茬擠兌康泳寧。
於是何氏父子也被抓來,嚴刑拷問。父子倆都快沒氣兒了,也沒招認自己盜走了官印。只是說了些兵部的瑣碎雜事,家長裡短的和案件毫無關係。
父子倆最後想來想去,提供了一個線索,把另外一個人牽進來了:任安泰是常常出入庫房的差役,他雖然是有婦之夫,但是卻和京城的一個女子有染。平日裡出手闊綽,和他的薪俸完全不匹配!
於是倒黴蛋任安泰也下獄拷打,連帶著他的情人一起挨板子。鐵帽子王綿課親自審問,據他觀察,這二人膽小如鼠,只有姦情而無涉案的罪行,最後只能停止用刑,暫且收監。
調查到這裡,似乎一切有價值的線索都斷了。兵部行印就這樣憑空消失,只剩下一個空盒子,盜賊難道就抓不住了嗎?
綿課、英和、曹振鏞三人一籌莫展的時候,前文提到的那個老書吏鮑幹,他主動站出來,揭發了一個嫌疑犯——兵部前任書辦周恩綬。
老鮑說,這個老周嫌疑很大,之前曾經多次請求自己替他加蓋官印,偽造一份公文件案。自己嚴詞拒絕,但這周恩綬還不死心,設計了一個賭局讓自己輸了50兩紋銀,許諾事成之後賭債一筆勾銷,但自己不為所動。很可能是周某人,盜走了官印辦事。
老鮑的檢舉讓三人組如獲至寶,很快周恩綬也被捉來提審。禁不住拷打,周恩綬很快就供述了這事兒的來龍去脈:
江西綠營將領郭定元,他年紀比身邊的將領都大一些,因此非常擔心年齡問題影響職務升遷。他買通了當地的文書,偷偷修改自己檔案上的年齡。結果這老郭長得實在顯老,而且周圍人記得他的年紀比他自己說得大得多。總督府的官員信不過老郭,揚言要去兵部調看他的原始檔案。這下郭定元慌了,遂上下打點,找關係到了周恩綬這裡,請他幫忙直接做一份新檔案替換掉舊檔案。
老郭被捉來一問,雖是牽涉犯罪,但是和兵部行印丟失一案也無關係。周恩綬雖然承蒙郭定元的請託,但是要用新檔案替換兵部老郭的原始檔案,需要加蓋的是兵部的堂印,並不需要使用兵部行印。所以行印的丟失,和周恩綬郭定元沒有關係。
日子一天天過去,以綿課為首的專案組,和行印丟失一案有關的東西愣是啥也沒查出來,一眨眼嘉慶祭祖完畢,已經起駕回宮了。他們三個人,該如何面對震怒的嘉慶皇帝呢?
嘉慶震怒,拔去鐵帽子王花翎
嘉慶回宮以後,專案組三人報告了查案的進展,其實就是根本沒有進展。嘉慶嚴令莊襄親王綿課必須每日到兵部督促查案進度,於是更多的人手被調派來參與偵破此案。
不但是兵部上上下下被掘地三尺,就連兵部方圓幾里的民房也被翻了個底朝天,但連行印的影子都見不著。
行印丟失一案沒有偵破,倒是順帶著查出了不少其他事情,這些事兒堆在一起,讓嘉慶更加震怒:
兵部下轄的許多部門,因為辦公經費不知去向,導致許多公務需要中下層官員自籌。衙門飯食寒酸,屋舍年久失修,多種因素疊加,極大滋長了兵部官員的貪腐慾望。
兵部的日常行政也完全視規章制度為無物,比如本該由官員專人管理的印璽信物,竟都交付給普通書吏貼身攜帶,隨意使用。這些人有沒有拿著官印幫人亂蓋章,誰也不知道。
兵部的官署,日常公務都是書吏們辦理,大小官員無論是否當值,都在官衙內聚眾賭博,一片烏煙瘴氣。
最刺激嘉慶神經的,是一個叫做黃勇興的兵部小差役,他結婚的時候為了闊氣,竟然擅自把兵部庫房院牆拆掉,生生打了一個小門,讓花轎和迎親隊伍穿越。
......
凡此種種,一樁樁一件件,全都彙報上來,嘉慶看完摺子都不知道摔了幾回,新一輪懲治風暴席捲兵部:
所有違法的官吏一併革職治罪,擅自把印璽信物交付書吏保管的官員,永不升遷。
兵部尚書松筠革職,調離京城任山海關副都統、上任半年的兵部尚書和世泰革職,調內務府任虛職,上任五天的兵部尚書普恭連降三級留用。
在第一波的懲治風暴中,兵部尚書戴聯奎、兵部左侍郎常福、右侍郎常英、曹師曾摘去頂戴調離,而今嘉慶追加懲罰,將這幾人全部革職。
嚴懲完這些人,嘉慶餘怒未消,繼續降旨:將負責牽頭偵辦此案的親王綿課、內閣大學士曹振鏞和吏部尚書英和拔去花翎,僅保留頂戴繼續審案。老曹是漢人,魏武帝曹操的直系後代子孫,他更慘一點,拔去花翎後官階還被降為二品。
老書吏鮑幹嫌疑極大,空印盒竟成突破口
專案組三位高官被嘉慶懲罰,這些知恥後勇,開始冷靜下來分析是不是案子查錯了方向。
先找的兵部老書吏鮑幹,他堅稱行印入庫時候完好無缺,導致大家只能從發現空印盒的庫丁康泳寧身上找突破口。結果被小康帶溝裡去了,先後審了何氏父子、差役任安泰,浪費了不少時間。
就在這個時候,老書吏鮑幹又出來主動揭發周恩綬,導致專案組又在周恩綬和郭定元偽造檔案的事情上浪費了精力。不但案子沒有查出頭緒,反而查出了不少其他瑣碎之事,牽連大批人等不說,三個主審都被拔去花翎。
所以,這個兩次誤導案件偵辦方向的老書吏鮑幹,實在是嫌疑很大!
綿課等人對鮑幹加強審問,結果鮑幹對去年秋狩歸來,行印入庫封存的場景描繪,出現了前後反覆、矛盾的情況。再單獨審問當時理應負責點驗入庫的主事何炳彝和筆帖式慶祿這倆人,發現他們描述的入庫時間、在場之人等等細節,都存在很大出入。
就一個兵部行印歸還入庫的事情,鮑幹、何炳彝和慶祿都是經手人,怎麼可能三個人有3個細節迥異的說法出現呢?很顯然,兵部的行印至少在秋狩以後歸還入庫之時,就已經出問題了!
內閣學士曹振鏞端詳著先前庫丁康泳寧找到的空印盒,這是行印失竊一案的唯一物證。他看來看去,覺得這個空印盒有些粗糙,懷疑並非行印所用的印盒。
綿課和英和當即召來負責統一制辦印盒的工匠,根據匠人的查驗,案發現場翻出來的這個空印盒,並非出自他手,可以確定不是行印所配的印盒。
曹振鏞比較嚴謹,問工匠有何實在的憑證。工匠也不多言語,只說:
“每一個印配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印盒,一個常用,一個備用。諸位大人若不相信我的判斷,可以去捷報處找來行印的備用印盒,對比一看便知!”
結果,綿課派去捷報處的人,遲遲找不到存放在那的備用印盒。捷報處的書吏餘輝庭支支吾吾,推說備用的印盒可能丟了。
如此,案件的突破口便出現了!這個空印盒並非兵部行印所用的原裝印盒,也不是備用的印盒。兩個印盒都不翼而飛,而鮑幹、何炳彝、慶祿以及這個餘輝庭,都是同行印歸還入庫密切相關的官吏,他們表現反常,前言不搭後語,且四人供詞疑點重重,必定和行印失竊案直接相關!
終於,在綿課、英和和曹振鏞的審問之下,四老書吏鮑幹交代了真相:兵部行印並非在去年秋狩入庫後失竊,而是早在秋狩之時就已經丟失。弄丟行印的人,是餘輝庭!
捷報處小吏餘輝庭,供述行印丟失經過
嘉慶二十四年秋天,皇帝例行秋狩,兵部官員帶著行印隨同出行。本應該負責隨身保管行印的官員,擅自將行印交給一個隨從書吏他爾圖揹負看管。
八月二十八日晚間,他爾圖不想悶坐在帳中,於是將裝著兵部行印的黃布包交給捷報處的餘輝庭,託他代為保管,自己溜出去玩了。
餘輝庭接過黃布包,就順手把包掛在了營帳的立柱上。夜深了,餘輝庭不知不覺伏在書案上睡著了。等到他醒來,已經是凌晨時分。
接著燭火的光亮,餘輝庭扭頭往身後立柱上一看,當即嚇得魂飛魄散——黃布包不翼而飛了!
驚懼不已的餘輝庭在所住的營帳內外仔細查詢,卻一無所獲。丟失兵部官印,這可是重罪!天亮了他爾圖可就要回來了,他一回來豈不是就要露餡!
思來想去,餘輝庭急中生智,找了個和兵部行印印盒差不多的空印盒,發現在裡面裝1000多枚銅錢,重量最為接近。於是餘輝庭把銅錢包好,裝入空印盒中鎖上,再把印盒用黃布包好。
天亮以後,耍了一夜的他爾圖盡興歸來,接過這假的兵部行印包,也不點驗,背上就走了。
他爾圖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可是餘輝庭卻膽戰心驚。他知道,一旦他爾圖還是其他人,開啟印盒就會東窗事發。哦,不,根本就不需要開啟印盒,因為印盒上的鎖,他爾圖手上的鑰匙根本就打不開!
所幸的是,秋狩結束,兵部行印也沒有派上用場。餘輝庭坐立不安,他找到了老書吏鮑幹,吐露了行印被他弄丟的事實,請他幫忙設法避禍。
老書吏鮑幹是何人?不過是兵部的一個小小書吏罷了,餘輝庭也是兵部書吏,他犯了事兒找這麼個芝麻綠豆的小官兒有什麼用呢?
別說,還真有用!清廷機構弊病叢生,兵部也不例外。許多官員調來此處,極少過問事務。業務能力堪憂,全靠中下層的小官吏遮醜。這些小官吏經辦了許多事,雖然官職卑微,但是卻能因此掌握很大的權力。
老書吏鮑幹就是如此,因為年紀大資歷老,不論是年輕的兵部書吏,還是兵部的一眾官員,具體辦事的時候都要仰仗鮑幹提點指教。餘輝庭眼下能夠指望得上的,就只有鮑幹這個人了。
鮑幹也不含糊,收了餘輝庭的50兩紋銀(你們看看,前面鮑幹這傢伙還揭發兵部周恩綬收人錢財偽造檔案呢,自己也逃不過真香定律)要為年輕後生餘輝庭,擋下此事。
於是當“兵部行印”回來的時候,鮑幹就主動帶著“行印”去入庫歸還。按理說,入庫之前要仔細點驗,可是面對在兵部“德高望重”的老書吏鮑幹,庫房負責人何炳彝和慶祿,根本沒有仔細點驗,開啟黃布包以後直接就把印盒交給庫丁入庫儲存了。
這樣的翫忽職守,是清朝兵部的常態,也是鮑幹敢於幫餘輝庭避罪的自信源泉——他在兵部多年,深諳官場規則,論圓滑世故,沒有人超得過他。
順利過了入庫這一關後,鮑乾和餘輝庭合計:
行印平時並不用,只有皇上出行才用得上,這一次封存之後,只有下次春祭,行印才會被取用。到了那個時候,便偽造一樁失竊案,這樣行印便不是在他餘輝庭手裡丟的,而是在兵部庫房失竊的。
嘉慶二十五年,臨近皇帝去春祭的時候了,鮑乾和餘輝庭便藉著職務身份的便利,順利進入庫房,將銅錢取出,把印盒丟在庫房舊桌椅堆的縫隙中。捷報處的備用印盒,也被鮑幹取走燒燬。
在嘉慶動身去春祭的時候,鮑乾和餘輝庭精心炮製的“兵部行印失竊案”就這樣發生了。
嘉慶尋印失敗,數月後駕崩
案件真相大白,最後一輪的懲辦結果新鮮出爐:
兵部書吏鮑幹,革職流放黑龍江為奴;
兵部書吏餘輝庭,革職流放黑龍江為奴;
兵部主事何炳彝,革職流放邊疆;
兵部筆帖式慶祿,革職流放邊疆;
原是從一品的兵部尚書松筠,從副都統的位子上再降為六品驍騎校尉;
......
其他一干負有責任的官員,依律治罪。
雖然餘輝庭供述了行印是他在去年秋天弄丟的,但是具體誰偷走了此印,嘉慶皇帝始終都查不出來。各省都在大力徹查此事,甚至清軍中懸賞與兵部行印有關的線索。朝廷行文遍及天下,嚴查加蓋行印的公文出現,以防有人密謀造反。
最終,嘉慶皇帝下令原印作廢,讓禮部重新熔鑄新的兵部行印。從此,各部行印必須由主官負責保管,歸還時必須親自在場驗看無誤,方可入庫。
數月之後,嘉慶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駕崩。
從這件小事便不難看出,所謂的康乾盛世早已離清朝越來越遠。晚清外強中乾的虛弱樣子,正在透過“丟印案”等事情展現在世人面前。如此百病叢生的清朝,又靠什麼抵禦西方的侵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