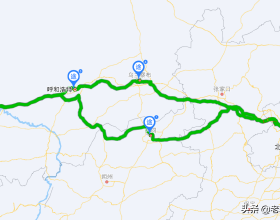有時候我在想,要是人死了以後,喪禮上放的是卡農該多好。兩天前,二爺爺去世了。我雖和他沒見過幾面,但二爺作為爺爺的親兄弟,我仍有義務帶上孝帶,前去他的喪禮,為他哭一哭,為他端坐在靈臺前,稍微盡些孫女該盡的職分。不過我們之間的爺孫情本身也很單薄,就沒花很多心思在二爺身上,全都是聽大人指揮。於是三天下來,在書叔叔家兒十平小院子內舉辦的喪禮上,我擁有一個與逝者很親近的身份,卻以一份極其陌生的感情參與了全程。
因為關係算的上親近,許多流程都必須參加,並且還要靠前、靠裡,不準缺席,也讓我增添了幾分不同的感受。說實話,這白事的氛圍真的很矛盾。陰森的喪曲,哭聲此起彼伏,地上鋪著跪著用的被子,屋裡屋外漫地是灑落的紙錢,來弔唁的人就快哭爛了門臺了,大門外卻搭起大群臺,他們要花大價錢僱演員敲鑼打鼓,"為的就是要讓一堆人國成堆看,要非常熱鬧才桁行。這種儀式其實不是很能讓人把感情投入其中,既便如此,不論前一秒在院子外笑的有多開心,初來弔唁的人,都要哭的夠傷心才行。
我一度懷疑,這種吭鬧的儀式難道不是為了告知逝者的靈魂他己經離去?以前看到新聞說,會有一些死去的人不知道自己己經離世,還做著生前做的事情,拿自己當話人一樣。要是這樣說來,也合適,反正我見那些人哭的時候,沒有一個是純粹的只張著嘴巴嘹啕大哭的。他們必須要哭著說話,必須要喊出來自己對逝者的稱呼,“我的二爺爺啊”,“我的二叔啊”……倘若人的靈魂真的在逗留,或者就算是逝者真的還沒意識到自己己經死亡,看到這陣仗,也要驚覺三分:原來我己經離世了,他們在哭的是我。
白事壓抑,又讓人有些通透。都說世事洞察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連喪事也不例外,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雙眼睛在看著你。姑姑哭的時候,我聽見兩個中年婦女小聲響咕,“怎麼這個閨女這麼會哭”,“人家會哭,你看她哭的一抖一抖的”,我無語,這都讓我聽見,還真把我當外人了。在這一人的眼中,其實大抵也就是如此,為了顯得孩子孝順,他們必須要哭的盡情、哭的悲傷,為了顯得人情溫暖,沾親帶故的,必須要來送一送,知了要三天,長了要七天,人的一生就在這樣的一場嘈雜喪禮當中結束了。
細細回想,人的一輩子,出生的時候雖是有人迎接,但當時自己終究是屬於別人的,可走的時候,來送的就有很多是自己的人了。所以今天那口棺材上印著的“百世流芳”有點意思,人生在世的時候,倒是也要花些時間,專心為自己打造“流芳”的條件才行。
人們把喪事做的悲傷,是因為逝者的離去多是象徵著可視生命的終點。人走,好比終點戛然而止的線段,不論是親人還是自己,逝者接下來的歸宿無人得知。但誰的心裡不深諳那將要去的是黑暗的地方?可不論是否清楚,之後都是入土為安、不復存在。因此,俗語講:人建茶涼,人們盡表哀傷之後,也就剁茶涼了。
可要是逝去不是這樣呢?要它是象徵著新的節點,是不是就可以把哀慟的喪曲換成卡農,為逝者歡樂的送行?倘若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天堂,我就不在乎這人世間最後一趟是怎樣走,不在乎是否有人為我哭,不要人米提醒我生命結束了,而要為我開心;生命要重新開始,倘若我要去的是天堂,誰人不為我開心,誰的心裡不清楚:那是個光明的地方。2021.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