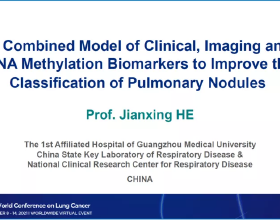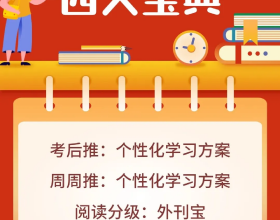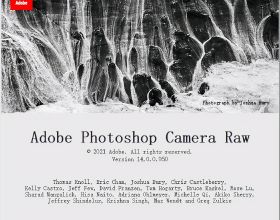05
如果僅僅是有感於梭梭的頑強,似乎還不能夠敘說再次路過沙井子,何來思緒萬千、何來百轉千回。其實我想的最多是,沙井子代表的文化從哪裡來?為什麼又消失了?回顧歷史,瞻望未來,我們是不是需要效法梭梭的“夏眠”“自我改造”和“自斷其臂”精神。
民勤境內的長城遺址
還是從柳湖墩遺址說起吧。沙井文化雖然是一個偏居西北一隅、分佈範圍較小、對中原文化影響力有限的小部族文化,卻代表了一個時期、一個階段、一個地域的歷史,必然是由幾代人經年累月、日積月累創造的。創造沙井文化的先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存在?依典籍記載:
史前,西戎人們過著逐水而居、隨畜移徙的生活。娥氏女簡狄浴於玄丘之水,後嫁帝嚳為次妃。漢鄭玄箋註時說:“禹敷土之時,有絨氏之國亦始大”。說得是居住在北方的西戎有絨族與中原華胥族首領有極為密切的婚姻關係,交往頻繁。因與西戎有血緣關係的大禹,治水成功,西戎有娥氏的國土也日漸擴大,並且逐漸東移。西戎東遷後,千里河西為氐羌所據。其後氐羌東移,千里河西又為月氏、烏孫共同居牧,並以黑河為界,月氏居東,烏孫居西。其後月氏逐漸強大,“有控弦之士十餘萬”,遂渡越黑河打敗烏孫,佔據整個河西,並在黑河西岸修築了昭武城。《括地誌》將關於月氏居處,置於“涼州姑臧縣”下,說明月氏先民活動的重心應該在“瀦野澤”邊緣地帶。後來隨著匈奴部族勢力向河西走廊擴張,月氏、烏孫部族相繼敗走,西遷新疆、中亞。這個時期與沙井文化存在的時期大體一致,就是中原的春秋戰國時期。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的重要目的,就是尋找西遷的月氏、烏孫,以合擊“縱馬揚鞭”“左衝右突”的匈奴部族勢力。
《括地誌輯校》
說這些的實質意義在於,能讓一個氏族長期居牧,且創造出以畜牧為特徵的“沙井文化”的地方應該是一個有水有草、可漁可牧的地方,最後落腳為瀦野澤。“澤”者,水聚集的地方。經過千年歷史變遷,作為不喜歡潮溼環境的梭梭樹來到這裡定居,而且讓它肩負了防風治沙的使命,重構起以保護為主旨的生態文明,肯定是這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無需考證期間的朝代更替、紛紜戰爭,在人們想到要在這裡栽梭梭樹治沙的時候,沙井文明已湮滅在一座座沙丘之下,就是安特生髮掘沙井文明的地方亦不復存在,有的只是光禿禿的沙丘,那些個代表一個時期的文化就散落在風沙之中。
夢想瀦野澤
水草豐美、可漁可牧早已成為人們口口相傳的美好回憶,策馬揚鞭、縱橫馳騁,輕舟短棹、漁歌晚唱早已隨風遁去,“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沙騎牆、驢上房”才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其時,代表美麗生活環境的水、澤、湖、田、草也蕩然無存,作為沙井子的先民、鎮番的先民、民勤的先民也早已從代表文明的古城堡、烽火臺以及長城外節節敗退,有的搬遷到了青土湖周邊、有的乾脆打起行囊遠走他鄉。就在不遠處的宋和村,人們也曾無法種植穀物開始外出逃荒。俗話說“好出門,不如待在家”,此等景象何其悲慘、何其悲傷。
06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人類的全部歷史就是組織起來,去改善限制自己的生存發展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其中有對自然的改造、有對社會的適應、也有對自我的革命和改造。
不遠處的縣城影影綽綽、跟前的莊稼已收割完畢,沒有了夏日的鬱鬱蔥蔥,先民們的無奈呼喚餘音繚繚、大風黃沙的陰陽怪氣陣陣低吼。這裡的沙漠是就地淤積、還是隨風而落,我無法考證。我知道的就是,曾在這裡生活的先民因這片沙漠而撤離苦海,因風沙肆虐而遠離故土。
民勤防沙治沙紀念館
宋和村還是在勤勞的汗水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保衛下,沒有繼續在風沙中“沉淪”,而是頑強地奮鬥在抗擊風沙的前沿。同樣奮鬥在風沙前沿的村莊、組織、人民何止千千萬,辛勤的民勤人民早已在抗擊風沙的路上,創造了不同於沙井文化——這一奠基於遊牧基礎上的,新的科學和文化,或者說是文明形態。
說起民勤繞不開的就兩個字,一個是沙,一個是水。翻開《鎮番縣誌》、《民勤縣縣誌》,可以說是: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半部分水案。
《鎮番縣誌》封面
1.成書於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的《鎮番縣誌·鎮番疆域圖說》載。“東邊外與寧夏口外沙河連界,六百餘里,平沙無垠,並無居民。”據此可想,在大清朝時期,由於沙患,民勤好多地方是無法居住的。
2.《鎮番縣誌·裡至》又載:“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總督佛題《籌邊第一疏》雲:鎮番沙磧鹵溼,沿邊牆垣,隨築隨傾,難以修茸。今西北邊牆,半屬沙淤,不能恃為險阻……”“紅崖堡一帶……至於東南邊牆,沙淤形跡,其舊址猶存者,止土脊耳。”不僅民勤境內的“堡”被沙埋了,而且民勤的縣城也是沙患無窮。
3.《鎮番縣誌·田畝》又載:學糧,各傾地通共一千二百四十傾二十七畝四分一釐七毫一絲八忽。今飛沙流走,沃壤忽成丘墟。蓋西北多流沙,東南多滷溼。
4.《鎮番縣誌·水利圖說》載:“緣紅沙堡一帶,居四壩之未,兼被沙患,舊壩水多淤遏,不能直達。”“惟頭壩以沙患,溝渠夏秋常行”“四壩下截,舊因大河沙淤,另開新河,以便澆灌”
5.《鎮番縣誌·建置志》載:明洪武時,因元季小河灘空城,修茸為鎮番衛。至成化元年,漸成規模。“後飛沙擁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參政張璽申呈都御史楊博,筑西關以堵飛沙。”清朝康熙元年,參將王三華重修西門樓。今池平,橋壞……西北則風擁黃沙,高於雉堞。康熙三十年以前,軍民負插搬沙,月無虛日,勞而無功。且沙以掀翻,易於漫溢,故罷其役。
描寫沙患、記述軍民治沙的記載,在民勤縣誌上可以說盈篇連牘。說明自大明朝洪武年間(1368-1398年)設衛,大規模農墾,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不到300年的時間,民勤的生態環境發生了無法逆轉的惡化。誠如《乾隆鎮番縣誌·風俗志》“舊志雲:‘鎮番土沃澤饒,可耕可漁。’按,土之肥瘠,水利能轉移之 。鎮邑名產,生被風沙。土沃澤饒成往事矣。”
有云:“民勤城,沒北門。”說的就是民勤城不是沒有北門,而是北門被埋在沙漠之中了。據說,民國十八年馬仲英屠民勤城時,就是從城北已經與城牆平齊的沙丘上進城的。
“別忘了/三千年前這裡還是一片古海/三百年前這裡還是波光粼粼/三十年前這裡仍有鴨塘柳林/而三十年後/三十年後的今天/你們卻只落得/一片荒漠/一道禿嶺/一雙呆痴的目光/兩片乾裂的嘴唇!”
注水後的民勤青土湖
這是詩人向人們發出的警告,時間可能不夠精準,但大體反映了民勤青土湖的演變歷程。據考證,新中國成立前近百年,民勤縣被流沙埋壓的村莊600多個,農田26萬多畝。明長城和沙井子、青松堡、連古城、三角城等都被淹沒在浩瀚大漠之中。
深受沙患侵擾的民勤人,篳路襤褸,艱苦奮鬥,深知植樹造林的重要性。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1950年民勤縣就舉行了第一次群眾性植樹造林誓師動員大會。1951年民勤縣建立了第一個以營造防風固沙林為目的的民勤防沙林場。從新中國成立伊始,民勤人就開始了一場堅持不懈、不屈不撓的防沙治沙的綠色接力……2008年,民勤縣召開了第二次生態治理誓師大會,拉開了新一輪防沙治沙保衛戰的大幕……
作為土生土長,又在這裡生活的民勤人,這段歷史是不能迴避的,站在沙漠一線的每棵梭梭也是不能忘記的。因為它記載了沙井先民曾經的繁華生活,因為它記載了鎮番古堡厚重的歷史文化,因為它記載了民勤人民的辛苦汗水,承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嚮往。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路過沙井子,我彷彿已幻化為一棵梭梭樹,既居其高、又處其遠,“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