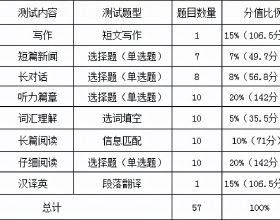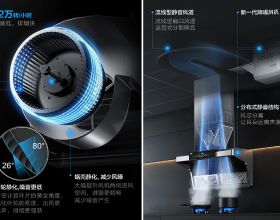我跟陸尋閃婚了,大學教授和女記者,看似天作之合,但實則我們井水不犯河水。
我對他沒什麼企圖,我希望他對我也不要有,我的心很冷很硬。
但婚後三個月,私生子、隱疾,我才知道,他跟我結婚的目的,讓我噁心。
1
我跟陸尋領結婚證,是在我們相親後的第二天。
結婚協議是我擬的,其中有一條:不接受婚內性行為。
陸尋一目十行,然後愉快地答應了。
當時我就提醒他,這一條,你看清楚了,是婚內,不是婚前。
「我知道,沒問題。」
陸尋微笑著扶了扶眼鏡,似乎在向我證明,四個眼睛看得很清楚。
從民政局出來以後,我整個人都還是恍恍惚惚的。
我任小琪,母胎單身的第三十個年頭裡,竟然真的就這麼草草率率地把自己嫁掉了?
誠然,陸尋的相貌和氣質已經算是所有男人裡讓我最不討厭的那種了。
高高大大,斯斯文文,乾乾淨淨,穿衣服挺有品的,脫衣服禽不禽獸那就說不準了。不過我並不關心這個,我們是無性婚姻,他在外面勾男惹女還是招貓逗狗,都跟我無關。
「明天收拾一下,後天陪我回趟老家吧。」
坐在副駕駛上,我臉朝窗外,對正在開車的陸尋漫不經心地說。
沒等他答覆,我又加了一句:「你先陪我回家,然後我再陪你去見你父母。」
我結婚,實在是因為被我媽催得精神衰弱了。
我不知道她以前接受的到底是什麼教育,好像女人不結婚就觸犯了天條,十惡不赦。
說起來,她自己的婚姻明明也是一塌糊塗的。我生父家暴,離婚後嫁了繼父,我媽帶著我這個拖油瓶去給人家兒子當後媽,她忍氣吞聲熬了這麼些年,前兩年我繼父終於掛了,她終於解脫了。
我說她一個人跳跳舞,看看劇,做做飯,養養花,享受一下晚年生活不好麼?怎麼就一根筋地非要逼著我往婚姻這個火坑裡跳?
我是真搞不明白,結婚到底有什麼好?自己進了火坑不算,還非催著逼著我也趕緊跳進去。
可我媽振振有詞:「結婚當然有好處啦。要是不好,我還能結兩次?」
我以為,陸尋家裡也是這樣的。
沒想到,聽了我的話後,陸尋搖了搖頭:「你要回家我陪你,我父母那邊不用。」
嗯?
我很是驚奇。
「我爸媽都是很敏銳的人。他們一生相愛,幸福和諧,一眼就看得出你的眼裡對我沒有愛,我帶你回家,他們反而會擔心。」
陸尋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老凡爾賽了。
我更奇怪了,如果陸尋說的都是真的,他沒有被逼婚,那他為什麼跟我結婚?只見過一次面就跟我領證,甚至連基本的夫妻生活都願意放棄。
除了陸尋是 gay,或者他不行,我想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釋。
但我什麼都沒說,只是結結實實地嘆了口氣。
陸尋看了我一眼:「不是你想的那樣。」
哈?這麼敏銳嗎?連我想什麼都能猜到?
哦,也對,陸尋是個大學教授,教心理學的。
我索性直接問了:「那你為什麼會願意跟我結婚?」
「你有錢啊,我想吃軟飯。」
我用手指抹去額頭上的三滴汗,然後彈了彈身下這輛小汽車 polo 的窗玻璃。
車是陸巡的,十多萬的代步車,沒我的車好開。
不過陸尋一個大學教授,除了那點死工資,基本上也沒什麼油水,收入估計真的沒有我高。
我是個記者,目前在市電臺一檔民生欄目任職。月薪兩萬一,單位管三餐,在市中心租著一室一廳的單身公寓,過得還是挺瀟灑。
等紅燈的時候,陸尋眯著眼看著我。他的五官很別緻,一說話就好像在眯著眼笑一樣。
我想了想,說,陸尋,雖然我們現在結婚了,但請你牢牢遵守我們的婚前協定,不要試圖破壞我們原本的生活節奏,否則,我可能真的會對你不客氣的。
你知道一個連性生活都不需要的女人,她做起事來能有多極端多恐怖?
陸尋笑了笑,舉單手投降狀。
說實話,他用另一隻手打方向盤的樣子實在是有點帥。
吃軟飯,他確實有這個資格。
我是記者,他是大學教授,我們的職業都算體面,也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共識。
那麼,不管是形婚也好,無性婚姻也罷,我們應該能處得和諧順利。
只是我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切,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2
陸尋把車開到江景花園的時候,我開始不淡定了。
這地方寸土寸金,是宣城最高階的社群之一,這裡的房子,我幾輩子都買不起。
陸尋住這裡?不會吧?這小區的業主,怎麼可能會為了仨瓜倆棗的租金,把房子對外出租呢?
我疑惑地看著陸尋。
不愧是心理學教授,陸尋把車停穩,指著前面那棟樓的最頂層對我說:
「上面那個,頂層複式,我買的時候挺划算的,閣樓是贈送的,五萬三一平,貸款的。」
我瞪了他一眼:「三年前這房子開盤的時候,我是現場記者。你有五萬三千一平的?有多少給我來多少!」
五萬三?做夢吧!十五萬三千萬還差不多!
陸尋有點尷尬地抓了下頭髮:「主要是離學校近。不過,還貸壓力確實很大。」
「所以只能開十萬的車?」
我回頭看了一眼這個金黃色的小 polo,突然有點懷疑剛才陸尋是怎麼把自己的大長腿給塞進去的。
然而就在這時候,一輛銀灰色的保時捷停了過來。
車上下來了一個四十來歲,圓潤溫和的大姐。
「陸教授您回來了啊!」
我狠狠地震驚了!果然是有錢人住的小區,隨便一個穿得像家政阿姨的人,出行都開著兩百萬的車子!
「嗯,回來了。」陸尋點點頭。
大姐下了車,拎了包,笑眯眯地看著我:「這位是……」
「王姨,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太太,剛結婚。」
陸尋大大方方地介紹我,我只能壓住驚訝,硬著頭皮,微笑著叫了聲王姨。
「呦!恭喜陸教授,看來今晚我得多做點好吃的了!那什麼,這個鑰匙給你,車我漆好了。polo 你還是給我吧,我正好去超市買點菜哈!」
說著,王姨用自己手裡的保時捷的鑰匙換走了陸尋的 polo 鑰匙。獨留我在風中凌亂著。
「陸遜……」
我愣了半晌,轉頭看向陸尋。
「王姨是我家阿姨,我的車颳了,她幫我去 4S 店取回來。」陸尋輕描淡寫地解釋道。
原來他今天開去跟我結婚的車,是他家阿姨的買菜車?
電梯停在頂層,門開了,我站在門口怔怔不敢進。
陸尋問我:「怎麼了?」
「陸尋,你說實話,你是不是很有錢?」
我看著陸尋,眼中充滿了糾結和警惕。
陸尋皺皺眉:「你所謂的很有錢,多少才算很有錢?」
「就是跟我的經濟條件差距特別大,天壤之別那種!」
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看現在才兩點半,民政局四點才下班,如果咱倆差距太大,現在去離了也行。
「任小琪,你是不是有病。」
陸尋扶了扶眼鏡,看似有些不悅,但他的嘴角是往上揚的。
我搖頭,我說不是這樣的。
「我們結婚了,就是合法夫妻。但門當戶對這種事,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如果你擁有超乎我認知的財富和社會地位,那麼在日後的相處中——」
「你別跟我說,這也是你媽教你的?」
陸尋打斷我的話。
我點點頭。
的確是,我媽兩段婚姻都很不幸,歸根到底,不就是差在門不當戶不對上麼?
第一段婚姻,我媽低嫁了。我生父是個沒念過書的小混混,好賭酗酒,喝醉了就打她、打我。為了離婚,我媽幾乎掉了半條命。
第二段婚姻,我媽高攀了。我繼父是個高階知識分子,他打心底裡瞧不起我媽,娶她回來,不過是看在她賢惠能幹,做得一手好菜,能幫他照顧前妻留下的兒子而已。
「你繼父是幹什麼的?」陸尋問。
「是我最討厭的一個職業。」我低頭,盯著自己的皮鞋尖,我說:「大學教授。」
陸尋長出一口氣,趁我不備將我拉進玄關。
「結婚第一天就離婚,你不要面子我還要。另外,我沒你想得那麼有錢,家裡的錢是父母的,和我沒關係。你嫁給我,做好吃糠咽菜過苦日子的準備就行了。」
3
第二天,我帶陸尋回老家。如我所料,我媽對他簡直是一百二十分滿意。
出身知識分子家庭,體面的工作,人長得又周正,簡直是我媽心中完美的女婿人選。
臨走前,她還專門把我拉到一邊,悄聲問我,小琪,你倆打算什麼時候要孩子?
我不耐煩擺擺手:「再說吧,我倆都忙。」
「忙什麼忙啊,都多大年紀了?」
我媽臉一沉,急了,「我告訴你任小琪,孩子一天不生,你拿什麼綁住男人啊?像陸尋這樣的家庭,能看上咱們就不錯了。你還不趕緊把他牢牢攥住了——」
「你倒是生得出孩子,是我親爹能綁住,還是我後爹拿你當盤菜了?」
我火了,說話很毒。
「你!要不是我在你繼父面前忍氣吞聲,你能有機會去重點高中唸書,能有機會上大學?!」
「所以我不想將來也像你一樣忍氣吞聲啊!乾脆不要生不要養!」
這番爭執的結果,以我媽被氣哭告終。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了老家。
後來我才知道陸尋給我媽留了一個大紅包,裡面放了八萬塊。
我們那邊有給彩禮的習俗,我沒提過,估計陸尋是自己打聽的。
回宣城以後,我和陸尋相安無事相處了一個來月。
每天早上,我們各自去上班,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王姨每週一三五上門,打掃洗衣買菜做飯。平時我們都在單位食堂解決三餐,週末的時候,陸尋偶爾也會心血來潮下個廚。
他的廚藝特別好,所以我忍不住調侃他:「你不是一位脫離了低階生理需求的人類高質量男性麼?怎麼還整天琢磨著怎麼做飯好吃?」
陸尋臭不要臉地看著我:「那還不是因為還有你這張世俗的嘴巴需要餵飽麼?不塞你點好東西進去,你能乖乖聽話?」
我也不知道為啥,這話怎麼聽著這麼五顏六色,怪里怪氣的呢?
那天,是我結婚以來第一次在他面前紅了臉。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陸尋剛洗了澡下來,身上還沒有完全擦乾的水漬透出了他結實緊緻的腹肌。
他有健身習慣,體型保持得很好。
這麼來看,他或許真的是個 gay。
打臉來得太快,兩天後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找上門來,徹底顛覆了我對陸尋的認知。
那天我外出跑新聞,忙完都快三點鐘了,我也就沒回臺裡,直接回了家。
剛到小區門口,就被一個女人攔了車。
這車是陸尋的,就那輛銀灰色的保時捷。他借給我開的,答應我不用我付油錢。
攔車的女人大約二十五六歲,面板很白,長得很漂亮,眼神卻有點恍惚,精神狀態不怎麼好。
我奇怪地問她,你找我?
「你是陸尋的妻子吧?」
女人意味深長的樣子,讓我心生不妙。
我應了一聲:「你是……」
女人得意地看了我一眼,還沒等我反應過來,她甩手又是一記重磅大炸彈丟過來。
「我是陸尋他兒子的媽。」
看著女人劃開手機螢幕,展現在我面前的一張照片,我的腦子「嗡」的一下就炸了。
陸尋在左,女人在右,當中的小男孩五六歲的樣子。
背景是迪士尼小鎮,一家三口出行,浪漫又溫馨。
我定了定神,臉上擠出一個挺尷尬的笑容:「所以您,是他前妻?」
除了這個可能,我一時也想不到別的。
然而女人直接就給我跪下了!
是真的跪下了,當街跪那種,一把抓著我的衣服,怎麼都不肯松!
「我求求你,你離開陸尋好不好!我真的不能沒有他,孩子也不能沒有爸爸啊!」
我直接傻眼了,資深記者當了這麼多年,我什麼樣的大風大浪沒見過?
可我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陷入這麼尷尬難堪的境地。
「你先起來!起來再說!」
我拼命拉她。
「我不起來!你不答應我我就不起來!你帶我去見陸尋好不好?我保證以後再也不任性,我真的不能沒有他!」
「你起來好好說啊!」
眼看周圍的人越聚越多,我的臉都沒地方擱了。
就在這時候,那女人突然仰面一倒,整個人開始抽抽起來。
不多時,她眼睛翻了,口中一個勁兒冒白沫。
「這是羊癲瘋啊!快打 120 啊!」
我在病房外面坐著,半小時後,陸尋才趕過來。
「喬禾怎麼樣了?」他問我。
我說,打鎮定劑了,人還睡著。
「她怎麼會突然過來找你的呢?」陸尋問我。
陸尋抓了下頭髮,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這麼侷促緊張。
我冷笑一聲:「你問我啊?」
這時候,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拖著一個小男孩來了。
那是喬禾的媽媽和她的兒子小蛋。
我瞅瞅陸尋,說:「你看,你兒子長得多像你。」
陸尋皺眉:「小琪,你胡說什麼呢?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想哪樣了啊?」
我簡直哭笑不得,我說陸教授,咱倆為什麼結的婚我心裡沒數麼?
那你明明都有老婆孩子,你幹嘛拋妻棄子地隨便找個女人又閃婚?
而且不圖我錢不圖我色的,你該不會就為了故意氣喬禾的吧?
我敏銳的記者思維一下子燃了起來——
捂著嘴,我大驚失色:「我的天!陸尋,那女的是不是把你給綠了?所以你才不原諒她?」
陸尋兇著一張臉:「任小琪你有病是不是?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樣,你聽我說——」
「打住!」
手機響了,我看了一眼單位的來電:「我沒興趣知道你倆以前的事,我找你結婚就是圖個乾淨省心。那既然現在不乾淨不省心了,我給你幾分鐘時間想個像樣的說辭,然後咱倆趁著沒到四點半,趕緊體體面面去把婚離了。我先接個電話哈!」
電話是我同事打過來的,一接聽,那邊就傳來震耳欲聾的叫喊聲。
「你別砸了!喂,我警告你!報警了啊!」
「住手!你到底想怎麼樣!」
「喂喂,小琪我跟你說,不好了!有個男的自稱是你哥,紮在你工位上不走,說今天一定要見到你!」
4
我心裡罵了句操他大爺的任高飛,掛了電話就衝了出去。
任高飛是我哥,沒血緣關係的。
我媽帶我嫁給任志光的時候,我才八歲,任高飛十二歲,是我繼父和他亡妻的兒子。
估計是怕他受後媽的氣,所以他大多時候都是在奶奶家。
他的奶奶和姑姑、叔叔沒少嚼舌頭,以致於他對我和我媽懷有天生的敵意,即便我媽任勞任怨當牛做馬的,到最後也撈不著一句好話。
他爸是體體面面的大學教授,可惜這小子不學無術,三十幾歲連個正經營生都沒有,這次跑來我單位鬧,用屁股想想也知道原因——
為了爭我繼父生前留下的那套房!
我繼父原來有套小房子,是任高飛爺爺留下的,才六十幾平,我和我媽嫁進去以後,一家四口人非常擁擠。
後來學校給分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的福利房,五年期的共同產權。五年以後,就算是商品房了。於是繼父就把這小房子給了他妹妹——也就是任高飛的親姑姑——結婚用了。我們一家四口搬進了大房子。
這套大房子雖然是學校分給我繼父的,但那會兒他和我媽已經結婚了,而且前期個人要出資六十萬,我媽賣了我外公外婆留下的房子,跟我繼父一起出的這筆錢,所以這房子本來就是夫妻兩人共有的。
我繼父死了,這房子若要分,那得是分我繼父的那部分,再一分為二,按市值最多也只能給任高飛四分之一,也就是八十多萬。
可是他不滿意,說什麼那房子是他爸爸的,自己至少要一半。
就這樣,前兩年為這房子的事,我們兩家也沒少扯皮。
後來我和我媽不堪其擾,乾脆把房子給賣了。
錢多錢少讓法院去判,最後的結果當然沒什麼懸念,年初那會兒就判下來了,錢也跟他家結算清楚了。
我就是怕他總來騷擾我媽,才讓我媽回老家的。可是這人要是不講道理,那可比癩皮狗還要賴皮。
我回到單位,看到任高飛坐在我的椅子上,雙腿翹得高高的。
已經臨近下班,辦公室裡外都圍了不少人。
我上去一把就把任高飛的煙給扇飛了,我說你想幹嘛?
「我想幹嘛?任小琪,你不把我該得的那份吐出來,今天你就別想囫圇離開這兒了!」
我說行啊任高飛,幾天不見,能耐見長啊?
你跟我要多少,我就給多少,那法院是幼兒園啊?
「你有種在這兒立霸,你有種繼續砸啊!我們有保安,有警察,我還怕你鬧不大呢!有種你往我這兒招呼——」
我指著自己的腦殼,笑他是個孬種:「今天你要是能把我放躺下了,回頭坐個十年八年的牢,我反倒清淨。」
見我壓根不吃硬的,任高飛又軟了。
「小琪,咱們怎麼說也是兄妹一場嘛,你也不能眼看著你哥走投無路是不是?我最近做生意虧了點,你說你和姨兩個人手裡握著好幾百萬呢,也沒啥急用場是不是?先借我點唄,回頭我賺了,我給你們分紅——」
「滾。」
我輕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個字都不想多說。
我的態度激怒了任高飛,他一蹦三尺高,指著我的鼻子辱罵我:「任小琪你以為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你跟你媽兩個嫁進來,不就是賣*的爛貨麼?我爸*完你媽再*你,你當我不知道是吧?」
「咣噹」一聲,我操起手邊一個訂書器,直接砸在了任高飛的腦殼子上!
我在拘留所裡待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陸尋帶著律師進來,把我保了出去。
後來我才知道,他跟任高飛私了的,賠了他五萬達成了和解。
我連一句感謝都不想說,我一路跟在他身後,像他提在手裡的行李箱。
快到家的時候,我說:「我上去收拾東西,明天咱倆去離婚。你把喬禾和小蛋接回來吧。」
陸尋哭笑不得:「小琪,你怎麼就一根筋呢?我和那孩子哪裡長得像了?」
陸尋說,喬禾可不是他前妻,甚至一點關係都沒有。
她只是他的病人,一個有著嚴重心理障礙合併妄想抑鬱症的女病人。
單身未婚,卻帶著一個兒子。
陸尋說,自己只是看她太可憐了,偶爾多關照了一些。
結果,這姑娘妄想症犯了,非要說他是她的男人。
聽完這些,我不厚道地笑了:「話說,女病人愛上自己的心理醫生本來就是很常見的事,否則怎麼叫病人呢!但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你怎麼能允許這樣的事發生呢?還帶著人家母子兩個去迪士尼,你可真敬業啊!」
我犀利地提出了質疑,甚至已經做好了抨擊的大綱。
誰叫我是個以筆代槍的有良知的新聞人呢?
「瞅你這幸災樂禍的混賬樣!」陸尋瞪我。
我說,那可不,我是記者,致力於挖掘事實真相。
「行,你要想寫喬禾的事,以後我保證你有機會。」
陸尋這個烏鴉嘴,竟一語成讖。
臨近五點半的時候,喬禾的母親打了電話過來。
我和陸尋飯都沒吃,急忙出門。
喬禾站在醫院的天台上,穿著一件素白色的長裙,隨風起舞。
「喬禾!」
我和陸尋跟著保安爬上樓頂,此時警察還沒到位。
「小禾,小禾!小禾你快下來啊!」
喬禾媽媽坐在一旁的水泥地上,哭得力竭聲嘶。
「喬禾!」陸尋大聲呼喊著:「你冷靜一點,想想小蛋,想想你媽媽!快回來,不要做傻事!」
喬禾回過頭,長髮被風吹散,笑得甜美又悽絕。
「陸醫生,謝謝你。我已經想起來了很多事……給你添麻煩了,真抱歉……」
陸尋白著臉色,一邊大喊她的名字,一邊試著往前靠近。
「你別過來!」喬禾激動大叫。
陸尋不敢再動,「喬禾,聽話。既然你什麼都想起來了,你就應該明白,那些噩夢已經過去了。你聽話,下來。」
「不會過去的。」喬禾搖頭,「永遠不會過去的,我已經毀了,我的一輩子都毀了,還有我可憐的小蛋,只要我活著,他就永遠會被別人指指點點。除了死,我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不!這不是你的錯!喬禾,你是個好姑娘,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應該為此付出代價。但這個人,絕對絕對不應該是你和小蛋!」
喬禾的淚水隨著風飄過來,落在我的臉頰上,燙出我心口上的共情。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喬禾身上發生過什麼事,只是一低頭,我看得到我手腕上陳年的割腕傷——
我想,那種共情,大概來源於這個世界對女孩子們的敵意。
「陸醫生,謝謝你。可是我不死,那個人渣又怎麼能得到報應?」
喬禾說完,縱身一躍。
「砰」的一聲!
樓下是高八度的尖叫聲,人們在驚呼,在圍觀。
他們像我一樣,只嗅到這場意外裡獵奇的味道。
5
回家後,陸尋一頭扎進了洗手間。
一個小時後,陸尋出來了,眼睛很紅。
他沒理我,直接上了樓。
我跟進去,看到他坐在陽臺的地上抽著煙。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抽菸。
我靠著他坐下,從他手裡接過煙,就了一口。
很嗆,嗆得我眼睛也跟著疼。
然後,陸尋給我講了喬禾的故事。
喬禾上大學的時候,還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姑娘,愛說愛笑,人人都喜歡她。
人人都喜歡她,禽獸也喜歡她。
那個禽獸叫金鼎元,是喬禾的專業課教授。
他總是以指導課業等名義有意無意接近喬禾,最後終於有一天,在一次學院活動之後,他將喬禾灌醉,侵犯了她。
為了安撫喬禾的情緒,他謊稱自己是真心喜歡喬禾,並哄騙喬禾,說自己已經跟妻子離婚了,等她畢業後就跟她結婚。
就這樣,可憐的女孩陷入了禽獸的 PUA,三年為他流了四個孩子,最終萬劫不復。
東窗事發,禽獸的老婆打上門來,所有的髒水都潑在喬禾的身上。
她從學校退了學,才發現自己又懷孕了。
醫生說,再流產的話,她很可能這輩子都不能做母親了。
生下小蛋,喬禾得了很嚴重的抑鬱症。她和她的家人不是沒想過去找金鼎元討公道,可是金鼎元的背景通天,喬禾這樣的女孩,不會是第一個受害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幾年狀告無門,喬禾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去年初,喬媽媽帶她來找陸尋做心理諮詢。
溫柔體貼的心理醫生,讓這個可憐女孩產生了病態的依戀。
她的精神時好時壞,這也就是她一開始突然來找我時,瘋瘋癲癲的緣故。
最後,陸尋對我說:「小琪,有關喬禾的事,我那裡有一份完整的口述資料。你,能寫個報道文案麼?你是記者,說話有分量,你爆出去的料,會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
我怔了一下,盯著陸尋。
我說:「你什麼意思?」
「金鼎元那樣的畜生,不該逍遙法外。」陸尋低著頭說。
我笑了:「陸尋,全世界就我一個記者麼?」
「金鼎元背景很深,我找過其他媒體,要麼沒有人敢報,要麼就是隻想享受流量的紅利,都不是真心想幫助她。」
「我不接,我怕有危險。」我毫不猶豫地拒絕。
陸尋說:「小琪,我以為,就算全世界都不幫喬禾,你也會去幫她。」
我笑:「為什麼啊?」
陸尋的眼睛依然明亮:「小琪,我知道你的事。」
我腦袋一炸,心臟劇烈地跳動起來。他說他知道!他知道什麼?他到底知道什麼?
「你……知道什麼?」
「我什麼都知道。」陸琪直視著我的眼睛。
原來如此。我什麼都明白了。
我的聲音冷冷的:「你知道什麼?就因為我也遇到過同樣的事,所以我義不容辭,所以我不能拒絕,是不是?」
「小琪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不是個狗屁!」
我呼地一聲站起身,淚水一下子湧出眼眶。
這是我第一次在陸尋面前流淚。
「我告訴你陸尋,我跟喬禾不一樣!她腦子蠢!她自甘墮落!她自作自受!我呢?我他媽的,我被我繼父強姦的時候,我叫救命了!」
我真的喊了,求了,我掙扎了,我也絕望了……
可我能怎麼辦?我媽以死相逼,讓我不要報警,讓我忍!她說她丟不起這個臉。
是啊,離開了繼父,我媽怎麼生活?我還在上大學,而她,連一份像樣的工作都沒有!
我抑鬱,我脫髮,我自殘,我以為我的人生徹底完了!
我熬啊熬,終於熬到那個禽獸死了!
為什麼,為什麼陸尋還要來揭穿我的傷疤!
「小琪!」
陸尋將我緊緊摟在懷裡,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胸腔裡的心臟如此鮮活有力。
我歇斯底里地大哭,但我不想在他面前哭出聲。我張口咬住他的肩膀,狠狠地咬。
他一聲不吭,只是把我抱得更緊了。
他說,小琪,你一定會願意幫助喬禾的,對麼?
只有為喬禾討回一個公道,你才能真正救出你自己。
「小琪,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我恨恨地說,陸尋你少給我放屁,你不是心理醫生麼?你就是想治好我的心結,治好我的性冷淡,然後好睡我是不是!
「你來啊!老孃有什麼心結?老孃是受害者,老孃又沒錯!我憑什麼因為那個禽獸把自己一輩子的幸福都毀了?」
我一撲身就把陸尋壓在了身下,直接騎上他的腰。
我撕扯他的衣服,像一隻中了邪的豹子。
我說,我用不著你治癒,你想睡就睡啊,今天你要是不做點什麼,你丫就是孫子。
然後,陸尋就真的當了一回孫子。
他不行,是真的不行。
我分明能感覺得到,他對我是有感覺的。
可是在最關鍵的時候,他沒能成功。
我鬱悶地爬起身,在後半夜的濛濛細雨中,走出了家門。
我坐在馬路邊,手邊放了好幾罐啤酒。
都是剛才在便利店買的。
我很努力地喝,卻怎麼也喝不醉。
大概是因為,那酒喝進去立馬就出來了,全變成了眼淚。
6
我糾結了整整一週,終於做出了決定。
沒錯,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記者,我沒有必要冒著風險去為別人抗爭。
可是,如果當年有人為我抗爭了,如果當年,有人能站在我身邊、握著我的手一起面對邪惡,我的人生,會不會不一樣?
我選擇當記者,不正因為我曾孤單站在雨裡,所以才想為別人撐一把傘嗎?尋求真相,聲張正義,我忘記自己的誓言了嗎?
girls help girls,喬木的痛,沒有人比我更懂。
我聯絡喬木媽媽,拿到了很多一手材料。回到單位後,我跟我的上級領導說,我有個稿子要發。
不出所料的,提交複審的時候,稿子被攔下來了。
說我沒有證據,不符合一個媒體人的職業道德。
我笑說:「要什麼證據?小蛋不就是證據麼?是不是那畜生的,親子鑑定還不夠?另外喬禾自殺的時候二十四歲零六個月,不如咱們推算一下她生小蛋的時候,多大年紀?」
「任小琪!你簡直胡鬧!你知不知道金鼎元什麼背景啊?」
我仰起頭,笑著說:「我管他什麼背景?我只知道他是個人渣。」
我說,你們不發,我就到別的媒體去發。我不相信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就找不到一個敢說真話的人!
幾經波折,新聞稿終於發出來了。雖然沒有直接用當事人的姓名,但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按照慣例,這樣的新聞一定會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和徹查,我知道,金鼎元一定會有所動作,但我一點也不怕。
就在第二天一早,我和陸尋被一陣敲門聲驚醒。
開門卻發現外面沒人,只有一個帆布包。
開啟來,裡面是五十萬的現金。
我們對視了一下,報了警。
接下來一週,陸尋都來單位接我。我知道,他怕我出事。
於是我笑他,你擔心什麼啊,當初不是你把我拉下水的麼?我死了,你當英雄,正好以丈夫的身份繼承我的花唄。
陸尋沉著臉說:「小琪,我是擔心你。」
我眯眼一笑:「陸尋,你愛上我了啊?」
「琪姐!」
真掃興,有個同事突然從後面追上來,叫我。
我趕緊跟陸尋分開,回頭應聲:「什麼事?」
「差點忘了,你有個包裹在前臺呢。」
我和陸尋面面相覷。
我說,我最近沒買東西啊?
包裹沉甸甸的,開啟來,是一隻血肉模糊的黑貓。
我尖叫一聲,嚇白了臉。
我和陸尋衝回家,看到大門被人撬開了,到處被人潑了紅油漆。
接下來,依然是報警,調查,取證。動靜越來越大,除了我的一封新聞稿外,漸漸地,其他受害人也開始在各大平臺揭發金鼎元。
終於,我們微不足道的發聲,引起了司法部門的重視。
為了保證這場官司能夠獲勝,除了寄希望於陸尋的律師團隊之外,最重要的是保護好活生生的證據。
我問陸尋,要不,先把喬媽媽和小蛋接到我老家怎麼樣?等開庭的時候再回來?
「你媽媽同意麼?」陸尋問。
我不太確定,只能說,試試吧。
其實我心裡也沒底,於是打了電話回家。
果不其然,我媽把我一頓臭罵,說我多管閒事吃飽了撐的,跟人家無親無故的,以為自己是救世主麼?
我被罵到懷疑人生的時候,反駁了一句讓我媽也懷疑人生的話——
我說媽,我被任志光強姦的時候,哪怕有一個陌生人能站出來見義勇為保護我,我也不至於自殺那麼多次!
結束通話的電話那邊,我媽是什麼反應,我已經不知道了。
我愣愣地看著陸尋轉身衝進了洗手間,半晌沒出來。
我敲敲門:「陸尋你沒事吧!」
他突然推門出來,像炸彈一樣撲到我身上。
他把臉埋在我肩膀,手臂的力度幾乎要把我揉斷。
他的聲音嘶啞而顫抖,他說:「小琪,對不起。」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以為他是因為擔心我,壓力太大了。
我笑著說你放心吧,現在這件事已經發酵成這樣了,我倒不信金鼎元還敢動我。
可他卻把我抱得更緊了。
我說,我快透不過氣了,陸尋……你,你讓開一點,別拿東西頂我啊。
話一出口,我自己反而愣了一下。
陸尋低頭,用悲傷的眼神看著我,然後,吻了我。
我低聲問他,要不要再試一試?
他將我直接推到在沙發上,可是當我們正式開始的時候,他又不行了。
「對不起,小琪。」
他抱著我,這道歉聲真的讓我太心疼了。
我不知道陸尋到底是怎麼回事。
上天為什麼這麼殘忍,讓一個這麼優秀這麼完美的男人有這樣難以啟齒的缺陷?
那我,有沒有可能讓他恢復正常呢?
可是,上天沒有給我們這個機會。
開庭的前三天,我和陸尋從律師那裡回來,經過地下停車場時,遭到了襲擊。
我一眼看到三五個身形晃動著,投影在停車場的牆壁上。
他們的腳步越來越快,來者不善。
「陸尋。」
我拉著陸尋的手,另一隻手摸索著電話準備報警。
然而陸尋單手護住我,衝我使眼色。
「報警來不及,你先跑!」
那些人的動作快如閃電,還沒等我反應過來,陸尋的身體已經擋在了那把尖銳的匕首之前。
我從來不知道,男人的身體,原來也是可以那樣偉岸,那樣讓人充滿安全感。
「陸尋!」
「救命!救命啊!來人啊!」
我抱著陸尋,雙手按住他腹部汩汩流血的傷口。
那種恐懼,瞬間沖淡了我十多年來的噩夢。
「陸尋!陸尋你堅持一下!陸尋!」
「小琪……」
他吃力地弓著上半身,嘴角微微一動,鮮血就止不住地溢位。
「對不起……如果當年,我可以再勇敢一點。」
7
金鼎元的案子宣判下來的那天,我同時接到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醫院打來的,告訴我說陸尋的父母從國外過來,把他帶走了。
也是,我是他的妻子,卻不是他真正的妻子。
陸尋受傷失血嚴重,腦部缺氧導致昏迷,能不能醒來,還是個未知數。
他的父母都是通情達理的人,說是要把他帶回國外去,他們問我,還有什麼要求,會盡量滿足。
我只在電話裡說,我想知道,陸尋有沒有什麼東西留給我。
他媽媽想了想說,陸尋有封信,夾在他的結婚證裡。
上面寫著:小琪親啟。
十六歲那年的暑假,我捉了一隻蟬,於是以為自己捉住了整個夏天。
那天,我媽做了一碗涼粉,讓我送到繼父任志光的辦公室,他在值班寫論
文。
蟬鳴陣陣,整個辦公室,乃至整個走廊都空無一人。
空調壞了,他看著我進來,滿頭大汗。
我以為任志光會舀起涼粉,可他卻掀起了我的百褶裙。
他強迫我的時候,世界全都黑暗了。
我只記得,在門玻璃後,有一個穿著白襯衫的清瘦身影一晃而過——那個男孩子,他看到了。
陸尋在信裡說,他是過去提交保研材料的,最後一道流程,就是身為系主任任志光的簽名推薦表格。
所以他害怕了,猶豫了,然後選擇了離開……
陸尋說,就是從那天開始,他發現自己不行了。
他交往過各種女朋友,環肥燕瘦風情萬種,他去看那種片,去刺激自己,可無論如何,都不行。
他病了。只要一閉上眼,滿腦子想的都是那天下午,我被任志光壓在桌子上哭喊懇求的樣子——
最後,他放棄了保研,考了心理學專業。
他想救自己,也想救千千萬萬個像喬禾一樣的女孩子。但他最想救的,是我。
8
又一年秋天,我仍然單身。
年前申請領養小蛋的資格終於下來了。今天,是開學日。
我送他到校門口,看到他主動給女同學開門時紳士有禮的樣子,我很欣慰。
陰霾終究都會過去,日子一點一滴,溫馨且平靜。
放學時我牽著小蛋的手回家,走到街角時,我看到了一個身影。
夕陽給他的身影鍍上了一層金光,他身材高大,五官溫潤,即便不笑,嘴角也總是翹起來的。
我的淚水模糊了眼睛。他身上的光,我真的很想牢牢抓住。
時間是最好的良藥,讓所有的罪惡曝光,讓所有的正義雖遲但到。
兩年後,我和陸尋迎來了我們的第一個女兒。
加上小蛋,我們兒女雙全了。
教女兒,保護好自己;教兒子,嚴於律己。
願天下所有的父母,不再心碎。
關注我 “超短小小說”,每天更新有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