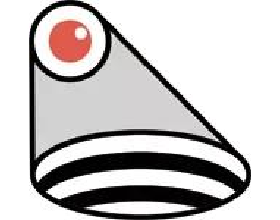1856年,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帝面對外來侵略,時而主戰,時而主和,進退失據,狼狽不堪。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況下,僧格林沁一度力主反對外來侵略,是從清王朝內部分化出來的抵抗派。
1858年5月,英法聯軍攻佔大沽,進逼天津,清廷命大學士桂良、史部尚書花沙納赴津查辦,這時清政府中不少達官顯貴均主張“安內而後攘外”,在一片議撫聲中,僧格林沁於6月毅然寫了一篇主戰奏疏《奏為華夷通好敗害無窮事》。
在奏疏中,他慷慨陳詞,指出逆夷之所以能“長驅直入”、“勢如破竹”是因中國武事失修,再加近幾年來的封疆大吏等大多庸懦之輩,“一聞賊至,則觳觫恐懼,抱本妄奏,求請和議,無非欲全身家,保妻子,誰復以社稷為重,生靈為重”,因此逆夷“敢任意驕橫,肆行無忌”。他力陳和議條款之危害,並請兵出戰,乘其(侵略者)驕而擊之”,“至於勝敗,兵家常事,勝不足以喜,敗不足以懼,人心非不可奮興,天命非不可挽回也,何至以堂堂上國,俯首乞和於外夷哉?”主戰立場,十分明確。
由於僧格林沁是親王且堅決主戰,便成了“主戰派的一個領袖”,引起了外國公使的注意,英國公使普魯士就聲稱“僧格林沁是和平的障礙,非到他被趕出舞臺,滿意的解決是不可能的”,“在這位蒙古親王的主持下,主戰派的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可見,以僧格林沁為代表,在當時清政府內部形成了一股主戰勢力,他力排清廷對外一味求和的做法,從清廷那裡爭得了整頓海防,保衛大沽的權力。據記載,他自1858年“奉旨辦理海防以來,晝夜辛勤,殫誠竭慮”。1859年初,又“親至海口駐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無間”,為大沽海防建設作出了貢獻。
他對大沽口的防務進行了周密佈置:在大沽除重建了四個炮臺外,又增設二個炮臺,六臺都安設各種火炮;恢復了直隸海口水師,增兵防守大沽海口;嚴格挑選士兵,親自督率訓練,提高畫質軍戰鬥力;在海岸築壘、挖壕,在海口設定三道攔河欄障;做好防務保密工作,以便出其不意地消滅來犯的敵艦。
1859年6月25日,在英法兵艦“皆豎紅旗,立意啟釁用武”之時,僧格林沁仍復“隱忍靜伺,以恣該夷之驕,而蓄我軍之怒”,命令炮兵不要先行開炮,待敵艦先行向炮臺轟擊後,他“揮鞭上馬,督軍鏖戰,戒炮臺同時開炮”,“以冀上申國威,下抒民望”。在僧格沁的指揮下,廣大官兵奮勇戰鬥,各營大小炮位環轟疊擊”,集中炮擊英國艦隊司令部及最鄰近的船隻,僅幾分鐘,帶路的“負鼠”號被擊中,死傷多人,緊跟其後的“鴇鳥”號也被命中,艦長拉桑上尉和第一兵團的凱南上尉等多人被打死,英國艦隊司令賀布也受重傷,迫使他只好改乘一艘運輸汽艇“鸕鷀”號指揮戰鬥,清軍炮火馬上又集中在這艘有旗艦標幟的汽艇上。
由於剛交鋒,清軍炮火就命中敵艦的指揮中心,打亂了敵人的陣腳,在清軍炮火的猛烈轟擊下,打得敵艦“有直沉水底者,有桅杆傾側,不能移動者,僅有火輪船一隻駛出攔江沙外,餘皆受傷不能撐駕”。
狡猾的敵人並不甘心自已的失敗,他們企圖哄騙岸上炮臺停止炮擊,而命陸戰隊千餘人分乘小舢船二十餘隻在南炮臺河岸強行登陸。僧格林沁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即調集火器營等的抬槍和鳥槍隊前往攻擊,北岸炮臺也發炮支援,聯軍登陸部隊死傷枕藉,只好退藏蘆葦地內,又乘夜“伏地搶進”,清軍施放火彈,殺傷聯軍。聯軍“術窮力盡,不敢戀戰,向船逃竄”。經過一晝夜的激戰,共擊斃、擊傷英兵四百六十四人,法兵十四人,英國軍官死五人,傷二十三人,活捉英、法兵各一人,繳獲舢板船三隻、洋槍四十一枝以及其他許多軍用物資。清軍在這次作戰中僅陣亡三十二人,大沽炮臺只遭到輕度破壞,海口一切防禦沒有損失。連侵略分子也不得不承認,“這確是一次可怕的慘敗”,“這是英國人自撤出喀布林後在亞洲所遭到的最嚴重的失敗”。
1859年6月大沽保衛戰的勝利,固然主要歸功於廣大中國官兵的英勇奮戰,但與主帥僧格林沁戰前積極備戰,戰鬥中親臨督陣,指揮有方分不開的。他直接指揮了這一戰役,鼓舞了士氣,起到了一個稱職主帥的作用,是一個有功之臣,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