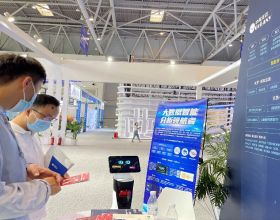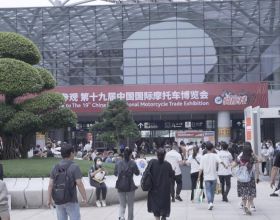老男人的友情,沉默而平淡,須細心體悟,哪怕不叨擾,也要讓對方知道,心裡有他。
在《隨園詩話》讀到一則:“乙未冬,餘在蘇州太守孔南溪同年席上,談久夜深,餘屢欲起,而孔苦留不已,曰:‘小坐強於去後書’。予為黯然,問是何人所作。曰:‘任進士大椿《別友》詩也。首句雲:‘無言便是別時淚’。”
這兩句平易的詩,一下叩中心裡某一根弦,教眼睛一熱。老男人對所擁有的人、物與自身情感,一路做減法,所餘無多。以朋友論,就那麼幾個,少下去是絕對的。本來,可另行物色,補充新血,然而,何其艱難!關於朋友這人生最後可供自由選擇的物種,我的至交有名言:“越老越交不起。”不是經濟問題,並非怕對方請吃了私房菜無法回請;也不是感情問題,彼此沒有斷袖癖,而是擔當,是道義上的義務。除非維持在“泛泛”的水平,一旦深交,同氣相應下去,難免接近生死與共。而老年多事,要牽掛,思慮,支援,安慰,拔起蘿蔔帶起泥,顧及對方的配偶和後代。你有個三長兩短,人家也這般。平添多少糾葛?精神、體力和錢包(對不起,還是不能免俗)對付得了嗎?
老男人的友情,以平淡為基調。男人表達感情,遠較女性含蓄,兩個白頭人更不會一見面就摟在一起說“好想你”。“相見亦無事,不來常思君”,恰切地表現了這種狀態。說“無事”嫌籠統,“事”是有的,從國家興亡到私密情事。但“無話”,不說也心照。相見絕對必要,不然心裡不踏實。
交情動輒以半個世紀算的男人,晚年的默契得自歲月的“厚積”。從青春到中年,交流的頻密和坦率,老來憶起,直呼“不可想象”!我家鄉三個男子,二十郎當歲結交,發誓當詩人。晚上在一起不知抓脫多少黑髮,要拼出一首朗誦詩《大瀑布之歌》。雞已叫頭遍,靈感耗盡,廉價菸絲抽完,連菸蒂也拆開來再卷一次,燒了。詩還是難產,繞室彷徨,接受蟋蟀的譏笑。“煙沒得抽,所以思路斷了!”有人發現了癥結,於是出門,熹微的星光下,拔了幾棵貌似可啟發詩思的枯狼尾巴草,回去碾碎,用煙紙捲起來。抽一口,一起嗆出驚天動地的咳嗽。
老男人心裡最在乎的,是相知。“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徹底地懂得,無保留地欣賞對方,這樣的高階友情,不是普通人都有幸獲致。次一等的,觀點一致,意氣相投,喝咖啡時默默對坐兩個小時。
上文所引的“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好就好在精準地反映了男人的友誼。聊興正濃,不讓你走,再坐一會兒,不比回去以後寫微信便當嗎?話說完,沉默就是別淚。記起知青年代一位朋友,他常常踱進我家,不必打招呼,我坐在藤椅上看書,至多眉毛挑一下,意思是:“來了?”他從書架抽出一本書,坐在板凳上讀,互不干涉,直到時間到了,他說,走了!五十年後,一次,我回國長住結束,明天返美。他非要給我餞行。席間他才透露,近幾天尿血以公升計,本來今天去檢查,但改為明天。臨別,我緊緊擁抱他,此生第一次對同性如此親密,嶙峋瘦骨刺痛了我,我的心發抖。無言,只有無窮盡的牽掛。
寫到這裡,愧疚湧上心頭。不多的老友,疫情中閒居,卻也疏於問候,十分不該。老男人的友情是植物,它的需求不會直接道出,須細心體悟,哪怕不叨擾,也要讓對方知道,心裡有他。(劉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