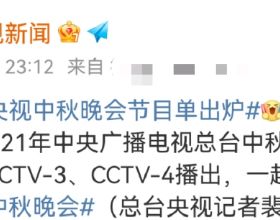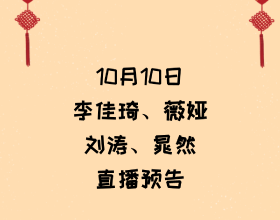自古以來,男婚女嫁,都由媒人撮合,俗話說,天上無雲難下雨,地上無人事不成。
媒人失業,是農村分地以後的事兒。
土地分到了戶,種田人真正自由了。
隨著種地“三機”的實現——機器耕,機器種,機器收——農民越來越輕鬆。
他們說,一年三百六十天,農閒至少在三百天以上。留家的老弱病殘,有的就近打打短工,力所能及地掙些零花錢;有的飯後不約而同地聚到一起,壘起了城牆,打起了牌。年輕人,已婚的未婚的,一窩一夥地外出打工掙大錢。
農民,大大減輕了對土地的依賴,土地也大大減輕了對農民的束縛。
這是古老的國土上,開天闢地以來,面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莊稼人,從來沒有過的自由而又幸福的日子。
媒人,尤其是職業媒人,也在這日新月異的新時代丟了飯碗、失了業,在令人失落的同時,也讓人感到社會的進步。
你看,越來越多的青年男女離開家鄉,離開黃土地,遠走他鄉,打工謀生。
在打工的地方,來自四面八方的年輕人聚到了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由陌生而熟悉,日久生情,自由談情說愛,最後攜手並肩,返回故鄉。尤其男方,實在是省卻了父母的勞神操心,了卻了一樁大大的心事。這一來,倒把一些又吃又拿的媒人給晾在了河灘上!
不過這種現象也有他的不盡如人意的另一面:
其一,什麼第三者插足,三角戀愛,什麼喜新厭舊,見異思遷,鬧離婚的多起來;其二就是,有著老榆木疙瘩腦袋的父母,見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閨女,不管不顧地跟男人跑了,落個人財兩空,心中自然氣惱。
村裡六十多歲的憨大就是這樣的人,他四十五歲上才得了個女兒。老伴死得早,是憨大把獨生女兒紅蓮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實在費了不少心血。
閨女紅蓮高中畢業後,出落得亭亭玉立,模樣出眾,跟村裡一幫子年輕人外出打工,進了“藝達家紡”——一家大型企業——與廠裡的一位小夥子談起了戀愛。
挺帥氣的小夥子是大城市來的人,端的是鐵飯碗。家裡沒有兄弟姐妹,大學畢業,比漂亮的紅蓮早來到這“藝達家紡”兩年,父母都是上班族。
兩人一見鍾情,月明之夜,節假日裡,兩人出雙入對,卿卿我我,同事們都認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到了年底,紅蓮跟男朋友先是去了婆家。
然後又結伴來走孃家,打算在孃家過春節,然後再一起去單位上班。
當然小夥子按照爸媽的安排,沒忘了帶上豐厚的禮品。
二人開著轎車,來到鄉下,進了小村。紅蓮爹——憨大——見閨女和物件上門兒來了,氣不打一處來。
他早就聽說閨女瞞著自己找了男的。心裡冒火,卻毫無辦法。因為女兒遠在天邊,鞭長莫及。只能在家裡生悶氣。
黃毛丫頭,總有回家來的時候!
這陣子,憨大憋了好久的一肚子火“騰”地一下子爆發出來,二話不說,抄起門後頭的一根頂門棍動起手來。
閨女在院子裡轉著圈兒躲閃。憨大一邊追一邊叫喚:“混賬東西,你給我滾出去!”那場面,令好多人想起《朝陽溝》裡銀環媽哪幾句話:“黃毛丫頭你氣死我,你不顧羞恥找公婆,任憑你丫頭跑天外,我也要把你往回拖”。
看憨大那架勢,這最後一句該改成“我也要讓你不能活”。還有,戲裡是老媽對閨女,這會兒是老爸對女兒,可氣又可笑。
這紅蓮,一邊躲閃,一邊說:“爹,你別生氣,聽我把話說完。”
這憨大,哪容閨女講話,依舊不依不饒,罵罵咧咧地追打,從院子裡追出家門,追到大街上。
憨大在後邊追,閨女在前面跑,爺倆圍著小村跑起了馬拉松。
弄的街坊鄰居都出來看風景。
有人勸憨大:算了吧,生米做成了熟飯,只要他們在一起能過日子,你何必狗咬耗子,多管閒事。
憨大不理不睬,一味逞強充能,炫耀家規,邊追邊罵:“傷風敗俗的東西,我沒你這個爛貨。從今以後別進這個家!”
女婿見狀,一口一個“大叔”地哀求。
這憨大還算聰明,沒有對這位既成事實的女婿下手,只是兩眼瞪得驢屎蛋子一般,吼了一句:“滾遠點兒!”憨大氣喘如牛,汗如雨下。
他不再追打閨女(可能是累了),回到家裡扔了木棍。然後把小兩口卸下的禮品,一件一件地扔到大門外,最後“咣噹”一聲,關門閉戶,任憑女婿女兒拍爛大門,憨大既不應聲,也不開門。
無奈之下,小夥子摸出手機,在大街上撥通了千里之外老媽的電話,把遭遇訴說了一遍。
站在小夥子身旁的鄰居們,很清楚地聽到手機裡有個女人在說話:“兒子,你倆不要在那裡再待啦!一分鐘也不要待!回來,馬上回來!這個老東西不讓進門兒,咱不進。你對紅蓮說,這裡才是她真正的家,一輩子的家!我不是她婆婆,是她親媽;公公也不是她公公,是她的親爹。從今往後,再不回那個家!”
小夥子掛上電話,把滿地的禮品撿起來,什麼王光燒牛肉,北京烤鴨,還有茅臺、五糧液······,統統裝入轎車的後備箱裡,懷揣著還沒來得及掏出的幾萬塊百元大鈔,然後拉著姑娘紅蓮的手,上了轎車,“嗚”地一聲,絕塵而去。
圍觀的鄰居們,好多人都說憨大榆木疙瘩腦袋,棒打鴛鴦沒拆散,落了個人財兩空。
憨大是傻、是笨、是半熟?還是二百五、半吊子?是腦子進水了,還是讓驢踢了?
這事一時間在鄉間傳得沸沸揚揚,當然也傳到了老支書張萬山的耳朵裡。
晚上,他和幾位鄰居來到了憨大家裡,對他好一頓叮噹,直截了當說他違法亂紀。
開頭憨大還嘴硬,說自個生的閨女自己管教,犯了哪門子法了?張萬山說,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你憑什麼棒打鴛鴦?
張萬山又是批評,又是勸說,把上下左右,前前後後,遠遠近近的利害關係擺了大半天,這憨大那不服氣的聲調才由高到低,由大到小,最後不吱聲了,那顆腦袋恨不能耷拉到褲襠裡去。
無論是憨大,還是紅蓮小兩口,這場風波都是在氣頭上,一個六親不認,一個揚長而去。
俗話說,打斷了骨頭連著筋,父女之間畢竟血濃於水,尤其紅蓮,從她記事起,老爸白天當爹,夜裡當娘,識文斷字的紅蓮難以割捨這父女情。
下一年的春節,紅蓮把心思先說給了物件,物件又說給了老媽,不等兒子說玩,老媽說:“我也正想找你們商量,別讓紅蓮他爹一個人在鄉下待著了,把他接回來,跟咱們住一起,年紀大了,有個頭疼腦熱的也好照顧。”
誰知,憨大破家難捨,尤其捨不得那二畝八分土坷垃,說是有活幹著,身上舒坦,一閒起來,他孃的,啥毛病都冒出來了。我還是在家待著吧。
閨女和女婿沒答應他,後來把他帶到了“藝達家紡”廠子裡,讓他幹起了清潔工,活兒也不累,不就是掃掃落葉,撿撿廢紙什麼的,既活動了筋骨,又不至於寂寞,閒時候跑到門衛處,跟幾個保安天南海北地扯閒篇。
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