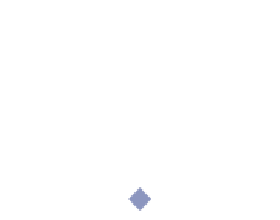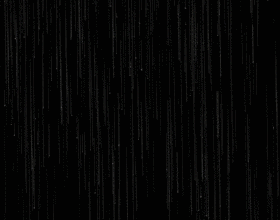晴朗的冬日,父親在陽臺上獨坐,他長時間地望著我養的那些花草,一會兒有一句沒一句的跟我聊著哪盆好看,一會兒又想起什麼似的沉默下來,淡淡的日光,落在他的眉毛和皺紋上,把老去的孤寂無限放大。
我曾經禪意的認為,老去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想象著,一對白髮蒼蒼的老人,在夕陽下牽著手散步,他們走過了歲月的風塵,經歷了人生的悲歡,進入風平浪靜的晚年,百念俱消,像是一棵樹,一株草,帶著回憶,沉默于山林。
這個畫面在我腦海裡,詩意般縈繞了很多年,直到母親去世。六年前,母親突發心臟病,在醫院搶救了9天,終是迴天無力,撒手人寰。我握著母親尚有餘溫的手,看到站在病床對面的父親,他眼裡和我一樣同樣寫滿了悽惶和痛楚。彷彿霎那間,腦海中的那個溫馨的畫面就被擊碎了。
母親去世那年75歲。如今,父親82歲了,他一個人獨住,他很少到我家和漢口的小弟家去。他說,那是你們的家。
我住的這個單元,7樓上住著一對老夫妻,70多歲了。十幾年前,他們的兒子意外去世,兒媳婦改嫁,他們就養著幼小的孫女。爺爺當保安,奶奶做保潔,捎帶撿廢品。經常,我把拆完的快遞包裝有意放在門口,不多會他們就撿去了。有時我沒來得及帶下樓的垃圾,他們也會悄悄地帶下樓扔了。他們說,天天上頂樓,已經走不動了,等明年孫女上大學去了,他們就搬回鄉下去住。
曾經腦海裡,那個在夕陽下牽手散步的浪漫場景,在這對老夫妻的身上,大機率是不會發生了。明年孫女上大學去了,他們還要愁孫女的學費。
老了,大概無奈和傷心的事就很多吧。年輕時,孩子們都是天真爛漫的樣子,怎麼看都可愛得充滿希望,忙著竭盡全力地做家庭的保護傘。當孩子們長大了,去社會接受錘鍊和洗禮,在婚姻和事業裡尋找平衡和穩固,如果遇到變故和難關,老人們除了傷心,大多是無能為力的。
父親老了,親朋好友們都說,活到這份上,耳朵不聾,眼睛不花,真是好福氣。他每天早上自己下樓去過早,去買菜,自己做飯,他說,只要自己能動就不麻煩我們。下午,他看電視,偶爾還玩玩二胡電子琴,還讓我教他玩iPad,他說,鼓搗這些東西是怕老年痴呆。
前段時間,舅舅老年痴呆了,舅舅不到80歲。折騰著在醫院住了兩回,回家,在家裡也弄了個像醫院那樣的病床,阿爾茨海默病的症狀最主要就是失憶。去看舅舅,他偶爾能認出我來,嘴裡不住地嘟囔著過去幾十年前的事情,聽不清,聽清了就啼笑皆非。和父親說記舅舅的老年痴呆,父親滿臉落寞,說舅舅多年不出門,自我封閉太久了,誰又願意這樣呢?還是年輕好啊,年輕腿腳好,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年輕的時候,我們哪裡懂得這些。老去,意味著與社會的脫離、身體機能的消退、疾病的折磨,更甚的是失去另一半後內心巨大的孤寂。
即便是父親的身體還算健康,我還是不能想象,退休前還是單位的主要領導,琴棋書畫被譽為才子的父親,竟然連智慧手機也不會操作,我和小弟都手把手地教過他多回,當時貌似學會了,轉頭不是忘記了密碼就是開不了機,鼓搗到最後一概鎖定,只好放在一邊,還是用他的老人機,最後也只能無奈地由他。我隔三差五地回家,有意不去張望牆上他和母親70歲時在天安門前的的合影,我不敢想,除了看電視就是枯坐,憑著回憶和孤獨消磨這一日日不急不慢的時光,父親該是怎樣的落寞。
曾經在新聞裡,看到在馬路上獨行的老人,被壞人謾罵或者欺負後,靜止地站在身邊川流不息的人群哭泣的場景。如此淒涼,哪裡來的夕陽浪漫可言?
隔壁文運苑3號樓1樓的桂醫生,前年老伴得病去世了,在北京社科院工作的女兒把她接到北京去住,她說不習慣,不多久就回來了,一個人獨住。鄰居們慢慢發現她有了輕微的失憶症,告訴了她女兒,女兒把她哄去了養老院,打那至今就沒有再見到過她。
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芸芸眾生,從出生的那一刻起,買的都是往生命終點的單程票。許多記憶裡熟悉的人,待某個時候和熟人談起,說已作古時,總是不勝唏噓。
其實,我也60歲了,我們都在義無反顧地老去,我們被生命的手牽著,每走一步都有一步的收穫和失落,好的,壞的,都要自己親自擔著。
父親又去睡了,發出輕微的鼾聲,陽臺上溫暖的陽光也留不住他太久。我下意識地給他掖了掖被子,在想,自己老去會是什麼樣子,是不是也和父親一樣?可我相信父親的一句話是對的,還是年輕好。
是啊,還是年輕好。儘管我已不再年輕,但我身體還好,腿腳也利索,腦子還夠用,趁著還沒有和社會脫節,多參加各種群裡的活動,多和妻自駕出門,走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完成年輕時想做而沒有時間做的事,能吃就吃,能玩就玩,把所見所聞所想都寫成文字發上平臺......到了父親如今的這般年紀,老得不能出門了,就把過去的記錄翻出來看看,這樣,應該算得上是浪漫的老去吧。
很喜歡聽趙詠華那首《最浪漫的事》,我真希望自己活得像歌裡唱的那樣,我知道那是浪漫,“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一路上收藏點點滴滴的歡笑,留到以後坐著搖椅慢慢聊......
我知道,歌裡唱的和現實是有差距的,但有一點,明明知道有差距,但不妨礙我有浪漫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