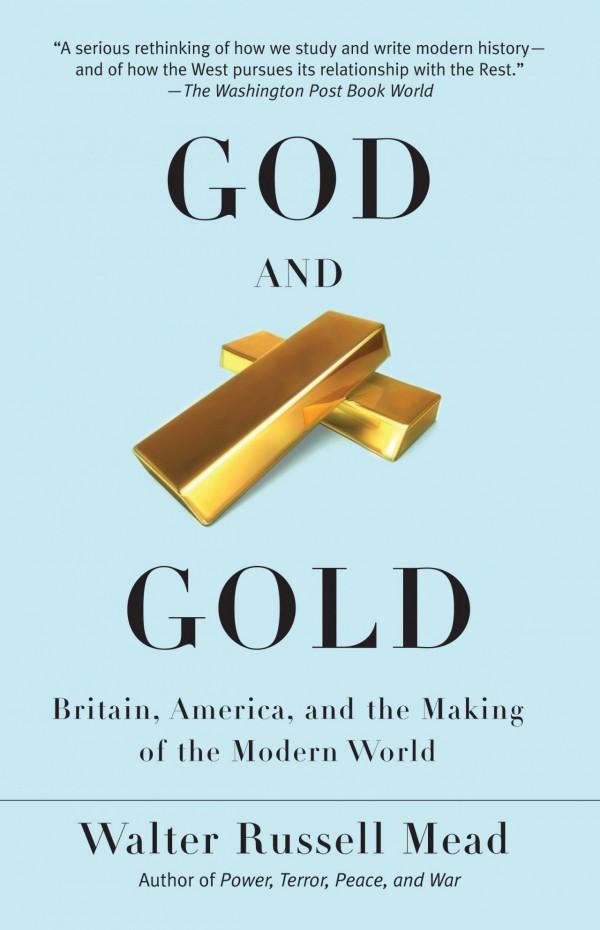【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30年前的今天,蘇聯解體。
1991年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投票決定解散蘇聯。12月31日克里姆林宮的蘇聯國旗被俄羅斯三色旗取代。
蘇聯的解體,意味著美蘇冷戰的結束,兩者往往被視為同一個歷史性事件。在此後的30年裡,學者們一直在努力弄清楚這一巨大事件的真正含義。
首先,人們普遍確信一些非常深刻的事情發生了,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都極為重大。但事後看來,真正的反思並未進行下去,這大體上是兩方面情況造成的:一是對於西方來說,這是一次突然來臨的勝利,而且是歷史上的再一次勝利,西方在相當長時間裡沉浸在驚喜和自滿當中,沒有足夠的動力進行深刻反思;二是由於美國開始面對一個單極霸權時代,對於美國在即將來臨的新世紀裡的角色產生了樂觀且天真的期望,從而產生了急於在現實世界中實現“天命”的衝動。
喬治·凱南是當年美國對蘇遏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1995年他91歲時,關於這一事件說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話:“在對現代國際關係史的回顧中,從十七世紀中葉到現在,我發現很難想到有什麼事件比先後被稱為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的大國突然完全解體並從國際舞臺上消失這件事更奇怪、更令人吃驚、乍一看更難以解釋的了。”
此話在以下幾點上是正確的:1)此事件的歷史意義屬於“從十七世紀中葉到現在”的整個世界歷史,應在其中進行闡釋;2)在這段長達三百多年的國際關係史中,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和其後的蘇聯Soviet Union應被視為同一個國際關係主體;3)人們對這一行為主體在國際舞臺上的突然消失感到奇怪、令人吃驚、乍一看難以解釋,反映出人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解釋理論,應繼續尋求。
30年後的今天再看,情況大體依然如此,被勝利的幻覺所左右的西方仍然沒有完全明白事件的真實含義。但時代的前進卻不會停下來等待遲鈍的領悟,隨著中國在極短的時間裡重新回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世界轉眼之間又迎來了一個新的巨大事件,而且更加奇怪、更加令人吃驚、乍一看更加難以解釋。
1.理論與現實的顛倒
近30年裡人們關於蘇聯解體事件的意義認知,自始至終受到中國迅速崛起這一事件的影響。
在最初的階段,焦點主要圍繞在“實行社會主義的蘇聯-東歐集團崩潰了,同樣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何時崩潰?”這樣一個假設性問題上。當時的中國,剛剛經歷了1989年政治風波,正在受到西方國家的集體制裁,一個直白邏輯應時而生:作為20世紀世界共產主義浪潮最後的餘波,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最後的陣地,在蘇聯失敗、西方勝利這一疊加事件的強烈衝擊和西方的高壓制裁之下,中國發生崩潰的問題將從“是否”轉變為“何時”。
假設一下,如果中國在不晚於“1999不戰而勝”的預言時間之前,發生了類似於前蘇聯的那種解體和崩潰,那麼,從蘇聯解體到中國崩潰這整個事件,也就有了一個非常簡明的理論解釋,可以滿足當時的世界從西方到東方、從精英到大眾各方面的認知需要:在意識形態上,資本主義勝利了,社會主義失敗了;在地緣政治上,西方集團勝利了,東方集團失敗了。

第一代開爾文男爵威廉·湯姆森 (William Thomson, 1st Baron Kelvin)。來源:維基百科
回顧歷史,整整100年前有過一件類似的事情。在經過了19世紀的全面發展之後,經典物理學作為一種科學理論,幾乎成功解釋了所有可見的運動現象,滿足了當時絕大多數人的認知需要。著名物理學家開爾文勳爵在1900年的辭舊迎新講演中宣佈:“19世紀已將物理學大廈全部建成,今後物理學家的任務就是修飾、完美這座大廈了。”但是很遺憾,由於“以太”學說和“紫外災難”等難題無法透過經典物理學解決,成為了當時看起來一片晴朗的物理學天空中的“兩朵烏雲”。結果,新的一場物理學革命如期而至,在人類科學精神的推動下,現代物理學大廈拔地而起。
但是,歷史見證,與具有科學精神的物理學家們大不一樣,西方的政治學家在20世紀末面對中國崛起這一無法在其自由主義經典理論中得到解釋的重大現實時,卻採取了一種完全相反的態度——不是尊重基本事實、修改錯誤理論,而是堅持錯誤理論、歪曲基本事實。
於是,可笑的一幕出現了:當“歷史終結”論和“中國崩潰”論作為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邏輯推論,在中國崛起的現實衝擊之下面臨土崩瓦解的前景時,原本應該發生的一場理論革命卻並未如期發生。恰恰相反,一種絕不針對理論、偏偏針對現實的奇怪論調出現了,這就是近幾十年裡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
隨手開啟一本關於“中國威脅”論的專著,類似論述撲面而來:“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辯論之一就是: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大國的崛起,將成為國際體系和東亞地區的穩定力量還是不穩定力量?辯論雙方目前都提出了有力的論據。”[1]
事到如今人們終於發現,這場辯論毫無意義,中國到底是“穩定力量”還是“不穩定力量”?“中國威脅”到底存在不存在?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今天的人們早已明白,在物理學中,牛頓力學體系中所假定的“絕對運動”和“絕對空間”事實上並不存在,只是為了讓經典理論能夠成立才假定其存在。所以,當現實世界實際發生的現象與經典理論不相符合時,需要修正的當然是理論本身,而不是去論證那些否定了“絕對運動”和“絕對空間”存在的現實物理現象是否是一種“威脅”或一種“不穩定力量”!
在物理學世界,現代物理學中的相對論和量子論,正是從那“兩朵烏雲”中降生的,自從量子論建立之後,人類對物質的認識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天地。但在政治學世界,這一類似的思想革命卻從未發生。

2015 年6月22日,美國自由主義者在街上游行。來源:洛杉磯時報
由西方自由主義理論所定義的“自由”“民主”“人權”,就像牛頓物理學中的“絕對運動”和“絕對空間”一樣,被西方政界和學界死死地抱住不放,儘管自由主義理論的“美麗宮殿”早已搖搖欲墜,現實世界中新的巍峨大廈就在人們眼前拔地而起,但人們卻沒有見到“西方現代政治學”理論的誕生,只見到西方針對中國的無端攻擊和謾罵日甚一日。
2.迴歸真實的歷史
就像今天的物理學家不會再應用牛頓力學的公式處理量子世界的問題一樣,對於當下世界的理解,人們也無法繼續照搬已經嚴重過時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了。這個轉變不僅適用於解釋中國崛起的問題,同樣也適用於反思蘇聯解體的問題。
蘇聯解體並不代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失敗,這一點,隨著中國這個堅持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並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不斷取得成功,已經越來越確定無疑了。
那麼,一旦走出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幻象,來到真正的歷史和現實中,又將如何把握諸如蘇聯解體和中國崛起這些極為重大的問題呢?如何給出最基本的解釋並做出最起碼的預測呢?
面對這個難題,不妨再借助一下喬治·凱南的那個指引。如果將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這個事件,放在自17世紀中葉直到現在的長達三百多年的近現代歷史中來理解,將之前的俄羅斯帝國和後來的蘇聯作為一個連續的主體來理解,那麼,是否存在一條貫穿始終的歷史主線呢?如果撇掉那些關於各種主義的理論泡沫,最後浮現出來的赤裸裸的岩石是否構成某種歷史邏輯關係呢?
無論是否願意正視,答案卻是肯定的。

1991年7月,美國總統布什和前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進行會晤。來源:路透社
美國前總統里根和老布什是蘇聯解體事件的親歷者,前者將美蘇競爭置於上帝與“邪惡軸心”對抗的歷史敘事中並將美國推向了最終勝利,後者則在蘇聯解體後立即著手推動建立“世界新秩序”,宣揚“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自由社會的福音”。其實這是一個很熟悉的場景,甚至也是很熟悉的話語,學者們毫不費力地從歷史資料中發現了這兩位當代美國總統在過去幾個世紀英國曆史中的前世先驅們。
17世紀50年代,英國護國公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當政,他向議會發表演講時說,世界上存在邪惡軸心,英國人的敵人“全是世界上邪惡的人,他們或在海外,或在英國國內”,他們“反對能夠服事上帝的榮耀和祂子民的利益的一切”。對當時的英國來說,這個“邪惡軸心”指的是當時的西班牙帝國,克倫威爾說,“因為它從始至終對我們這些上帝的子民充滿了敵意。”

英國護國公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來源:維基百科
沿著這個線索一路看過來,人們會發現這樣一個更真實的歷史圖景:以英國或美國或英國和美國這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為一方,以歷史上它的主要敵人為另一方,雙方之間的戰爭從未間斷,持續三百多年直到今天。
按時間順序,“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主要敵人這一方,先後有:17世紀中後期的西班牙帝國、同時期的荷蘭殖民帝國、從17世紀晚期路易十四時代直到18世紀初期拿破崙時代的法蘭西帝國、希特勒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從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帝國直到蘇聯。
在這個真實歷史圖景中,分不出什麼主義、原則和理想,不過就是有你無我的爭霸戰爭,而且戰爭雙方不僅暴力手段類似,所使用的謾罵語言也都大同小異。沃爾特·米德這位美國曆史學家在他2008年出版的《上帝與黃金》(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歸納了歷史上這些“反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Waspophobe)勢力在妖魔化對手時先後使用過的話語方式和手段。
例如,在法國人眼中,長期的法英對抗,是虔敬的、文明的、以土地和農業為基礎的羅馬與殘酷的、貪財的、以海洋和商業為基礎的迦太基之間古老戰鬥的重演,在這個歷史敘事中,英國一再被冠以“野心勃勃的迦太基”之名。拿破崙執政時期,報紙的文章宣稱:“法國在武裝。歷史在記錄。羅馬摧毀了迦太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維希政府的廣播每天都重複“英國就像迦太基,必被毀滅”的口號。
而在德國人眼中,德國之所以被困在了狹小的地域裡,就是因為邪惡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構建的世界體系對德國的束縛,於是從德皇威廉二世到希特勒,都為德國擴充套件其“生存空間”而奮鬥。在這個歷史敘事中,“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既是可憎的對手,又是可敬的先生。
第三帝國期間被任命為德國勞工陣線領袖的納粹官員羅伯特·萊伊,看到了從克倫威爾直到丘吉爾和羅斯福的一脈相承,他在1942年寫道,(英美)“把他邪惡計程車兵看作上帝的選民。丘吉爾和羅斯福學到並牢記殘忍偽善的克倫威爾的辦法,證明了在過去三百年內英美世界沒有變化,完全沒有變化。”
從大英帝國時代進入到美國時代之後,仇美、反美和恐美成了一種更為廣泛的情緒。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的觀察廣為人知:“美國是歷史上唯一一個神奇地直接由野蠻走向墮落、沒有慣常的文明間隔的國家。”蘇聯作家根裡赫·沃爾科夫寫道:(美國)“總體上它對人類、對個人和精神文化有敵意,對獲取收益有著夏洛克般的激情,不僅存在於血液中,也存在於活生生的靈魂和跳動的心臟中。”
伊斯蘭世界的新聞記者指出,“謀殺在美國文化的基因中根深蒂固”。伊朗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在回應小布什總統時所說的:“這些人的胳膊肘浸在其他國家的鮮血中。世界上哪裡有戰爭和壓迫,他們都參與其間。這些人用他們的工廠製造武器。這些人在亞洲和非洲發動戰爭,殺害千百萬人民以促進他們自己的生產、就業和經濟。這些人的生物實驗室製造細菌並輸出到別的國家,從而征服其他國家的人民。”
如果說,在“自17世紀中葉直到現在”這個歷史時段中,有什麼超出了各種主義和理論解釋框架之外更為真實的歷史本來面目,那麼就是這個傳統了。沃爾特·米德寫道:“對世界上很多地方來說,憎恨盎格魯-撒克遜的一切已成為一項古老而光榮的傳統。19世紀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擁有世界上動力最強勁、最先進的經濟,仇英心理是當時最普遍的狀態;反美主義則是當今的首選形式。
但不討論直接目標的話,從極左到極右,從共產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納粹分子、天主教神父和神學家、世俗的傳統主義者、激進的雅各賓派和瘋狂的保王黨,自克倫威爾時代到現在,謾罵的狂流一直傾瀉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盎格魯-撒克遜領袖們在幾個世紀以來用高度一致的元素展開修辭時,敵人們對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攻擊也一直綿延不斷。”[2]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同樣真實而且更加驚人的歷史本來面目,那就是:每一次“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與他們主要對手們的“大博弈”,總是前者勝利、後者失敗。沃爾特·米德寫道:“在三百年的戰爭中,英語國家確實常勝不敗。換一種說法,自17世紀末以來,英國或美國,或是兩國聯盟在它們參加的每次主要戰爭中均處於勝者陣營。這類勝利的歷史塑造了我們生活的世界......”[3]
30年前的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無法被解釋為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勝利,或自由民主對獨裁專制的勝利,或西方集團對東方集團的勝利,但是很難不被解釋為:在三百年來追求世界霸權的爭霸戰中“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對於早期的俄羅斯帝國和後來的蘇聯這個挑戰者主體的最後勝利,作為先後戰勝了西班牙帝國、荷蘭帝國、法蘭西帝國、德意志帝國各個主要挑戰者之後的最近的一次決定性勝利。
這就是撇去了各種關於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泡沫之後,人們看到的那個由一個個爭霸戰爭構成的真實歷史圖景。
3.以中國的成功重讀蘇聯解體
如果沒有中國的強勢崛起,如果今天的中國仍然只是一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角色,那麼,近三百年來上述幾個強權國家圍繞世界霸權的爭霸戰,幾乎就是近現代國際關係史本身了。而爭霸戰的勝利者,也幾乎就是世界霸權的實際掌握者了。
在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有過與此非常類似的時代,每個有意稱王稱霸的諸侯國,都是一隻眼盯著與競爭對手的實力對比,另一隻眼盯著整個天下的霸主地位,於是就出現了天下無一日無霸、霸主相更迭的歷史圖景,被稱之為“霸政”時代。從中國歷史上看,“霸政”時代是介於“分裂割據”和“大一統”之間的一個特殊時代,只在一些特殊歷史條件下才可能出現。
在“分裂割據”時代,自立為王的地方政權群雄並立,每一個都無力一統天下,因此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爭權奪利、擴大實力,雖然也是混戰,但並無稱霸天下的總目標。一旦出現了少數幾個地方政權每一個都強大到有實力完成統一時,就會進入“霸政”時代,霸主輪番稱霸,天下無一日無霸。而一旦其中某一個爭霸者最終滅掉了其他強國,一統了天下,也就進入了“大一統”時代。
以此做參照,近三百多年來“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與其他主要挑戰者之間的爭霸戰,很類似於兩千多年前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霸政”時代。唯一的不同,就是看起來很像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列強爭霸,其實並不是關於整個世界的,歸根結底是一個“小天下”範圍內的“霸政”。即使在蘇聯與美國的東西方“兩極”對峙時期,其時的中國也仍然構成單獨的一極,不在列強爭霸的“霸政”天下之內。曾記否,在20世紀60-70年代,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立場就是團結整個第三世界反對美蘇“兩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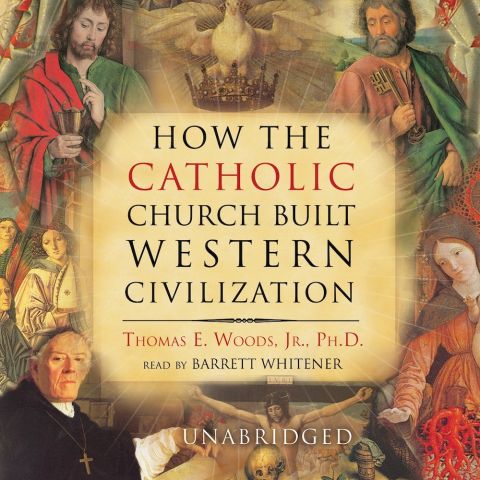
天主教是如何建立西方文明的。來源:Christian Audio
而這個“小天下”的範圍,更準確地說,其實不過就是西方文明和東正教文明這兩個基督教文明的範圍。近三百多年來的列強爭霸戰,無論多麼像是“現代國際關係史”的全部,其實並不是;在按照幾大主要文明劃分的世界範圍內,這些歷史只是其中兩個主要文明甚至是泛稱的“基督教文明”一個文明內部的事。
在同時存在著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等“非基督教文明”的當今世界裡,“基督教文明”不過是存世的諸文明之一,不能代表整個人類社會。而在中華文明重新復興的新時代裡,“基督教文明”也已經越來越暴露出其“小天下”的侷限性。
如前所述,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虛假和過時已經顯而易見,即使現代國際關係歷史上顯著標示著“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常勝不敗的記錄,其真實原因卻也不是自由主義理論中自吹自擂的自由民主必勝、自由市場必勝,而俄羅斯-蘇聯帝國的失敗,其真實原因當然也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更應該被視為是追逐霸權這個錯誤目標所必然導致的失敗。
之所以長期以來世人被大量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理論所迷惑,不過就是因為近幾百年里人類社會整體上被“基督教文明”所主導、所改造,而近幾百年裡也只有“基督教文明”生產出了諸多普世性的現代主義理論,其他幾大文明中都沒有與之相比的建樹,於是“小天下”內赤裸裸的爭霸戰與同樣出於“小天下”內的意識形態“諸子百家”混合在了一起,令人難辨泡沫與岩石。
但是,這個時代畢竟是要結束了。中國以世界大國的政治身份首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中的文明論含義就是:人類社會存世的幾大主要文明沒有高低之分,應該和平共處、交流互鑑、共同發展。正如習近平2019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指出的:“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鑑,因互鑑而發展。”這才是面向全天下的、真正意義上的普世主義,而不是“小天下”內作為爭霸戰裝飾物的普世主義。
這也就意味著,在“基督教文明”內部發生的世界霸權爭霸戰是不能被接受的,無論是哪個帝國,無論是什麼主義,都不可以是世界霸權的掌握者。以自由主義之名行使的世界霸權必遭世界人民反對,以共產主義之名行使的世界霸權同樣也必遭世界人民反對。
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針對蘇聯的大批判中,曾反覆出現過這樣一些說法:“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臺的實質,就是把列寧和斯大林締造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霸國。”“他們同美帝國主義一樣,充當世界憲兵。”“蘇修叛徒集團和美帝都是妄圖稱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國主義。”等等。雖然語言方式明顯帶有那個年代的特色,但還是觸及到了問題的本質。
這就是蘇聯解體這個事件從中國和中華文明的立場上得出的結論。雖然蘇聯的誕生可以視為共產主義理論的勝利,在誕生後的一定時間內也有過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但是一旦轉入世界霸權爭霸戰,就變成了霸權國家,就喪失了文明意義上的普世性和先進性,也就必然會失敗。回顧歷史,從針對中國的戰爭威脅,到針對捷克等“衛星國”的武力鎮壓,再到出兵佔領阿富汗,其霸權國家的本質已暴露無遺,即使沒有與美國的全面對抗,其必然失敗的命運也早已註定。
如此來看,蘇聯解體之謎並不難解。隨著中國重新回到世界歷史的中心,中華文明重新恢復其在世界諸文明中的原有地位,真正的世界歷史和真正的人類文明也恢復了其本來應有的面貌。“基督教文明”主導整個人類社會的時代終將一去不復返,“基督教文明”內部列強之間的爭霸戰也終將一去不復返。蘇聯解體不過就是作為爭霸者之一的又一次失敗,既然昔日的西班牙帝國、荷蘭殖民帝國、法蘭西帝國、德意志帝國都經歷過作為爭霸者之一的失敗並也都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帝國解體,蘇聯的解體也並非偶然。
2021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進一步指出:“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文明的魅力所在……要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鑑,促進人類文明發展” 。在這個願景中,沒有給世界霸權留下位置,也沒有給任何一個“小天下”內部的爭霸戰留下位置。
不僅如此,數字時代的來臨和全人類“數字文明”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全天下”的形成,也壓縮了 “小天下”的空間。雖然霸權主義還存在,對世界霸權的爭奪也還在繼續,但畢竟今非昔比了。
那個成就了“基督教文明”強勢地位的“自十七世紀中葉以來”的地緣政治格局在數字革命的衝擊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不僅主權國家的形態已不同以往,權力本身的形態也已面目全非了。這也就意味著,當今世界再次出現傳統形式的爭霸戰,出現一個繼蘇聯之後的新興爭霸者並再次開啟與“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之間圍繞世界霸權的爭奪,已經不大可能了。
所以說,那些繼續鼓吹“中國威脅”論的人,那些執意將中國比作前蘇聯、將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比作當年的美蘇冷戰、並將未來的希望寄託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再一次依靠“自由民主”、依靠“上帝在我們一邊”取得對於“邪惡核心”的勝利的論調,可以說是既誤讀了中國,也誤讀了時代。他們沒有看到或者說不能理解的是,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真實歷史實際上恰恰就是這兩個誤讀的反面——中華文明的根本精神正在透過數字文明的發展而得到充分的弘揚,並開始顯示出其真正的普世主義意義。
歷史見證,與“自十七世紀中葉以來”三百多年的“基督教文明”世界爭霸歷史恰成對照的,是一條兩千多年來貫穿始終、綿延不絕的光明主線——從中國歷史傳統中的“公天下”理想直到今日中國首倡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而光明所向,蘇聯解體之謎隨之而解開,霸權主義的歷史也將隨之而終結。
註釋:
[1]Edited by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First published 2002 by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2] [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塗怡超,羅怡清譯:《上帝與黃金:英國、美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02
[3]同上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