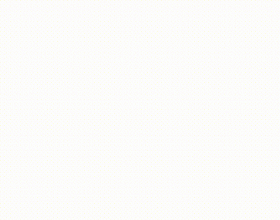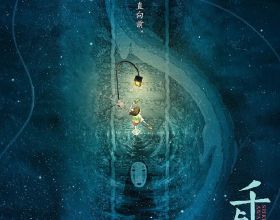敦煌明月
傳說梧為雄,桐為雌。梧桐同長同老,同生同死。
村中老宅旁有一棵挺大的梧桐樹,很老的樣子。舊村改造後村民都搬入了二層小樓,只剩下老宅孤零零的佇立在這兒,與旁邊二層小別墅似乎有點格格不入。
墨羽上下班途中都會從樹下走過,每次都會放緩腳步,禁不住看幾眼。四月一天傍晚梧桐花開了,微風拂過,空氣裡瀰漫著淡淡的梧桐花的甜味,直撲入墨羽的鼻孔,他貪婪吸了幾口,仰頭凝望著搖曳的梧桐花,有種說不出的久違而熟悉的感覺……
飯後,墨羽走到客廳,不知為何心神不寧,一個人端坐在沙發上,也許最近的事情挺多,太累,一會兒竟靠抱枕半睡半醒。
今夜的月亮彷彿特別清冷靜謐, 皎潔的月光透過窗戶灑下來,周圍安靜極了。看到墨羽睡著了,妻子怕他著涼,披了一床薄毯在身上。
忽然一道白光閃過,不知為何,墨羽已身在老宅梧桐樹下。正當他詫異之時,老宅的門徐徐而開,從裡面緩緩的飄出一女子,但見她神情憂鬱,長髮披肩,一襲古衣裝扮。
墨羽驚呼,臉色微變,退後幾步,故作鎮定道:“是人是鬼,我堂堂一七尺男兒,斷然不怕。”白衣女子不語,過了一會兒,緩步輕移上前。月光照著他,墨羽清清楚楚地看見她面容姣好,一雙如水的眸子定定地望向墨羽,眼神似喜似悲,頗為複雜,只是臉色有些蒼白。 “你一直住這兒?老宅好像好幾年沒人住了?”墨羽忍不住問。
“是,已是很多年了。”女子落寞地答。
“怎麼平日從沒見你?”
“見我?”她抬起頭帶著奇異的神色微笑著:“哦,我總在夜裡出來隨便走走。”他看看四周:“什麼都在漸漸變化,許多東西都已不存,唯獨這棵梧桐樹。”
墨羽不覺看看那棵極古極大的樹。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只是實言,緩和一下尷尬的氣氛,“其實我不是這個村的,只是在這裡買了房子居住。”
“我知道,我天天見你,比起剛來的時候,你變了很多”。
“是麼?”墨羽詫異地說:,“可直到今天,我才看見你。”
女子輕嘆了一聲,說了一句:“時間太久了,你忘記了。”模糊間又彷彿什麼也沒說,只是風吹過樹葉。
過了一會,女子勉強一笑說:“明嘉靖年間,這裡發生過一場戰爭。”
“是嗎?”墨羽頗為好奇,也很想知道這座小鎮的歷史。
女子像是在自言自語,“其實這裡原本叫增城,是大明的一個邊陲重鎮。當年嘉靖帝欽定的一甲一名頭等侍衛張殿揚就此戍守邊疆。”
“不會吧,皇帝的御林侍衛會鎮守在這個小鎮?豈不是大材小用?”墨羽大為不解。
“張將軍剛正不阿,潔身自好,任中軍,清正廉潔勤政為民,深得將士擁戴。只因不堪與朝中宦官同流合汙,故遭奸人所陷害。帝也是日漸腐朽,不理朝政,聽信讒言。後幸得東閣大學士毛大人所保護,才得活命,貶黜至此。”白衣女子見墨羽聽得認真,繼續娓娓道來。
“我本是增城一煮鹽女子,名阿朱。年二八,父母雙亡,無親投靠,只得在海邊煮鹽為生。張將軍巡查海防,見憐之,收我為婢女,服侍將軍。這才結束居無定所,奔波勞累之苦。將軍對城中的百姓體恤有加,輕賦稅,重民生,百姓們很是愛戴將軍。我每日除去在府中打理家務後,最期待的是去城外校場遠遠的偷看將軍與眾將士操練,日久生情,慢慢喜歡上了將軍。”
“那你沒和將軍表白過?”墨羽為阿朱著急
“尊卑有別,何況將軍事務繁多,不敢擾。這樣遠遠的看著,就感覺很幸福。”阿朱幽幽的說:“我總是擔心,擔心這歡樂不會長久,人總是會認為自己已牢牢地握住幸福,千百次地祈求這歡樂永存,可是天意難測,命運太難以捉摸,明日之事誰人能知?”。
“也許我錯了,也許命運已是待我太厚,也許我該靜心地領悟這所存的一切。我猝不及防,可是那時的我怎會知,這世界上什麼是永恆,什麼不變,什麼是真,什麼是所能真正把握的。”
墨羽沉默了一會,靜靜地道:“你好像哭了。”
“你不會懂”。阿朱輕嘆了一聲:“嘉靖六年,東南沿海倭寇成患,燒殺搶掠,民不聊生。朝中奸相怕與倭寇正面交戰,責令沿海防線,後撤百里,百姓內遷,禁海了之。只可惜我大明江山,被外邦所佔,百姓之苦難以名狀。”
“增城為產鹽重鎮,大明官鹽十之七八產於此地,倭寇早已是覬覦。四月初一,突然沿海順勢北上,幾萬大軍已是兵臨城下。增城府尹於百姓於不顧,率一干貪生怕死之輩棄城而逃。只留下幾千將士和幾萬老弱病殘百姓。”
墨羽頗為不解:“我拜讀過《光州府志》,當時卻有此記載,後幸得朝廷援手,百姓們才得以活命。”
“朝廷?若不是朝廷貪生怕死,見死不救,張將軍也不會血灑沙場。”阿朱憤憤道來:“豎日凌晨,城中百姓突聞鼓聲大作,知是校場點兵,紛紛湧上街頭,朝城東校場奔去。我也是幾日未見張將軍,甚是擔憂,也是和府中下人一同奔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