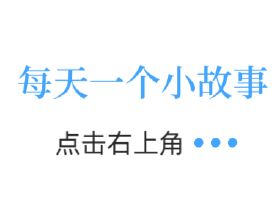李寶才迎娶薛明珠那天,黃蜂四起,像一團烏雲般籠罩在村子的上空。
在李家熱鬧的人群中,村西的趙神算隨口一句,“此乃異象。”
薛明珠頂著紅色的三角巾,歪著身子坐在腳踏車後座。
李寶才故意騎得顛簸,她一摟他的後背,他就渾身觸電似的,他李寶才從此也是有媳婦的人了。
薛明珠讓他騎得穩當點。
李寶才再次耍壞,嘴裡還唱起來,“顛它個一顛,晚上才有勁嘞。”
薛明珠摟緊,掐了他一下,“沒個正經。”
紅旗牌腳踏車歪歪扭扭,張張揚揚的行進著,車頭的紅綢帶隨意飄揚著。
東頭大樹下的一圈娘們趕著去李家吃喜酒,一路不忘調侃說劉蛾子的風騷勁頭從此該盡了吧。
對薛明珠來說,那天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親朋好友頻頻的祝福,酒席間朋友的玩鬧之語,還有李寶才的繾綣溫存。
唯一不得勁的是婆婆劉蛾子在整場婚禮中始終沉默著一張臉,不冷也不熱。
半夜的時候,
婆婆劉蛾子拿著李寶才老爹的牌位敲門說他們今天拜完了她,寶才他爹也該拜,這步不能省。
劉娥子的行徑著實耽誤了兩人的洞房花燭夜,春宵一刻值千金的道理難道老婆子不懂?
話說回來,雖然劉娥子早年喪夫,並且孜然一身守著兒子,出格之事也並未做,但並沒有獲得村裡碎嘴女人們的一致稱許。
早有傳言,劉娥子的兒子李寶才來路不明,至於那個猜測中的男人是誰,碎嘴婆子們始終不得知。
劉娥子不是農村一般的鄉下婆子,她半老徐娘的風姿,至今還喜歡在嘴唇上摸上一唇紅。
她內心似乎燃燒著某種火焰,而這種火焰的助燃劑似乎與薛明珠有關。
李寶才結婚那天,劉蛾子硬是用脂粉填滿了臉上的溝壑,連壓箱底的衣服也穿上了。
李寶才和薛明珠都在鎮上的磚廠上班。
薛明珠在食堂,李寶才在窯子場。
當所有人以薛明珠為夢中情人時,李寶才可謂暗度陳倉了。
他們結婚,任誰也沒想到,像一場意外。
大家都說李寶才這個癩蛤蟆吃上了天鵝肉,說薛明珠明珠暗投了。
薛明珠剛到廠裡上班的時候就被工友們暗地裡稱為薛寶釵。
無他原因,工友的文化程度裡薛寶釵是極溫柔又漂亮的,男人都好這口。
中午打飯,排在薛明珠視窗的人最多。
一次,薛明珠請假,工友們照常去哪個視窗,一見食堂哪個胖的流油的阿姨,都問,“薛明珠人呢!”
胖阿姨一聲怒吼,“咋,我打飯掉價了,不吃拉倒。”
其實,他倆人的感情,借用毛主席的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李寶才不像工友瘦小三,會耍腔調,逗女孩子開心,身邊三天兩頭換面孔。
他除了幹活就是吃飯,吃完飯再幹活,呆木頭,傻大個是工友給他起的綽號。
中秋的時候,廠裡分發福利,一廠的男女老少堵在食堂門口,排著隊伍為領一塊五仁月餅。
李寶才是全廠最後一個領月餅的。
等到了視窗,薛珍珠說,“發完了,沒了。”
薛明珠的語氣裡有些嬉鬧的味道,李寶才沒咂摸出來。
他二話沒說,轉身走了。
“喂,你站住。”薛明珠覺得好沒意思的人,有些惱。
待李寶才轉身的時候,薛明珠又笑了,“真是呆子,你看這是什麼?”
李寶才的眼裡倒映著兩塊月餅,包著月餅的油紙已經被油浸透,發著亮光。
李寶才怔住了,一秒兩秒過去了。
薛明珠再罵,“拿著呀!”
李寶才是跟著這霸道的命令走的,她叫拿就拿。
直到薛明珠離開才有所反應,大喊,“我多領了一塊。”
薛明珠走一步,他就跟一步,薛明珠煩了,說“下班了,你還跟著我,想耍流氓咋的。”
當時,天色向晚,倦鳥歸巢,靜聽還能 聽見它們即將睡覺時發出的微弱啁啾聲。
這樣的環境的確適合耍流氓,但李寶才沒那個心思,捧著一塊月餅跟著薛明珠。
李寶才說,“你多發我一塊月餅。”
“我說你是真傻還是假傻,要是其他人巴不得呢!”
要不說傻人有傻福呢,從此,李寶才的飯和菜像是會生長似的,每天長高一點。
工友眼饞,嘴臭,“這幫老孃們被男人用的沒勁了咋的,就這點飯菜塞牙不夠,李寶才你的吃不完吧,這樣,我心好,幫你分擔點。”說話間把李寶才碗裡的紅燒肉蹭去。
李寶才的腦海裡顯現出那晚薛明珠吃的滿嘴月餅屑衝他笑的表情,不惱,卻笑。
工友一看真是傻子。
2
磚廠的二把手,其實就是老總的兒子,要來視察廠區生產狀況。
二把手叫胡賢勇,名字挺褒義的,只是不知道賢不賢,勇不勇了,其實他一早在工友的心中就有了定論。
這個掛名老總,聽說生活不檢點,抽菸喝酒,樣樣在行,搞了幾任女朋友,進過幾次監獄,和監獄的長官混的很熟。
在磚廠工人那裡,輕易地被規劃到了社會敗類範疇。
工友們私下裡還預言過,磚廠遲早毀在他手裡。
對於他的下廠視察,大家一臉隨便,量他那身嬌肉貴也到不了這熱礦裡。
可是傳聞畢竟是傳聞,工友們帶著有色眼鏡看人了。
胡賢勇不僅到了礦裡,還大張旗鼓地懲罰了幾個隨地抽菸的男人。
胡賢勇來的那天算是喬裝過的,大家以為新來的,瘦小三吆五喝六的指使他,新來的,新來的叫著。
胡賢勇很快接手廠子,以前鬆鬆垮垮的政策也緊了起來。
這個時候,李寶才專注幹活的傻勁被抖摟出來,很受他的賞識。
但不久後,胡賢勇對他說飯堂的薛明珠機靈,說正好給自己配個秘書。
李寶才當場一個哆嗦,險些把手中的檔案灑落,胡賢勇眉頭突然擰了起來說,“也不知她願意不。”
李寶才迅速抽出幾個字,把自己都嚇壞了,“她肯定不願意。”
聲音鏗鏘,胡賢勇奇怪地望他一眼,“你這麼確定?”
李寶才也覺得話說的過滿,遂又補充,“我的意思是她在飯堂乾的時間長,工友都喜歡她做的大白饃,這一下子抽調,怕是工人間有怨言。”
胡賢勇因李寶才這一番話,目光亮了亮,“我果然沒有看錯你,廠子裡就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李寶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人才”兩個字可以用在他身上,這個殊榮是薛明珠冥冥之中助她的。
但李寶才莫名的恐慌,“莫非”兩個字成天在李寶才腦袋轉悠。
老總麵皮雖不佳,臉上還有坑,這點不如他,這也是李寶才感到欣慰的地方,但老總有錢有能力,足以撐起他那樣不佳的麵皮。
李寶才無論走到哪裡,薛明珠那張沾滿月餅屑的笑臉就崩出來。
他想過主動出擊,像瘦小三那樣,但薛明珠和那些女人不一樣,萬一遭拒,豈不尷尬。
就在這猶豫像絲線一般纏繞著李寶才時,薛明珠在他回家的路上攔住了他。
李寶才被薛明珠那雙大眼瞪的心臟險些從嘴裡跳出來。
薛明珠是質問的,“你,李寶才斷了我的人生。”
此話一出。李寶才當場呆立住,啞了半天,不是被嚇的,是薛明珠在他煩亂之際主動找他,他激動了。
見李寶才半天不講話,薛明珠愣了一下,旋即怒火再次捲上面部“你啞巴啦。”
“你怎麼生氣了。”
“我來問你,老總讓我做秘書,你為什麼阻止,我的升遷之路被你斷了,我的後半身也被你斷了。”
“後半生?我........”
“少來,等我嫁給老總,我吃香喝辣,不用伺候你們這些渾身酸臭的磚廠工人了。”
天空掉下了雷,瞬間劈中李寶才,他眼中美麗溫柔善解人意,是薛寶釵,是仙女,是他的夢中情人,竟然是個攀.......不,不是,不可能。
薛明珠再次發話,“你得賠。”
李寶才矇住了,這還能咋賠,再和胡賢勇說,那他的“人才”豈不捲鋪蓋了。
薛明珠不依不饒,仰頭大喊,堅硬的喊聲裡帶著某種柔然的力量“你賠,你毀了我的一生,你得用你的一生來賠。”
李寶才失望的幾盡絕望,呆呆的點了點頭,超前走,嘴裡喃喃自語,“什麼都沒了。”
薛明珠大罵,“李寶才,你個呆子。”扔出石子砸了他的背,李寶才頓了一下,繼續走,背部也漸漸映紅起來。
薛明珠火似的竄過去,摟住李寶才,“你個傻呆子用你的一生來賠我的一聲,你要......”
李寶才突然轉身抱住她,緊緊的,再不願意撒手。
3
過門後的薛明珠在來年產下一名女娃。
李寶才在廠子中的地位初見光明,胡賢勇並沒有因為薛明珠的事冷落他,反而越發器重他。
李寶才明白,這裡面有薛明珠的一份功勞。
一家人的生活雖然蒸蒸日上,但李寶才心中始終揣著警惕,三番兩次的勸薛明珠重新尋找一份工作。
薛明珠人是清白的,怎麼看不出李寶才心中的小九九,他讓她離開磚廠,那是不信任她,是對她的侮辱,如果她離開了,那豈不是顯得咱們肚量小,再說了這年月找一份像食堂這般輕鬆,包吃的工作,有嗎?
她的女娃,可就是她一次次從食堂的飯食里扣吧出來的。
為這事夫妻雙方還吵了一架,薛明珠堅決冷戰到底。
晚上將自己裹的緊緊的,她接連幾日聽見李寶才煩躁的嘆氣聲,她知道自己離勝利不久了。
果然,那一夜,李寶才忍不住了,想把薛明珠的身體扳過來,可薛明珠像是鑽進了蚌殼,怎麼也搬不動。
李寶才也不能霸王硬上弓,“不就是工作的事嗎?我以後不逼你了,成吧。”
“早說不就不用受罪了嘛。”
李寶才如一隻猛虎張揚著爪子撲了過去,薛明珠躲閃不及,落入,“虎口”。嬌嗔道,“你個呆子,輕點。”
暗夜一點點消逝,趴在窗戶根聽牆角的劉蛾子嚥了口唾沫,輕手輕腳回到了屋裡。
拿著一片窗戶紙,抿了抿。
昏黃的鏡子裡,劉娥子悽苦的笑著,笑著,眼睛陡然貼近鏡子。
一隻手細細的擦著嘴唇上哪越界的一抹紅,卻越擦越遭,用袖子一抹。
顫悠悠的手又拿著紅紙抿了一下,二下.......不滿意......又擦。
如此反覆,直至嘴唇紅腫出血,她竟然滿意的笑了,嘴裡輕輕哼唱著格調昂揚的調,一點點的蔓延在房間,自由,純淨,似乎有水流潺潺,鳥鳴幽幽。
薛明珠似乎看透了婆婆劉娥子的漠然。
自從嫁到李家,她無論怎樣趕早做事,餵雞餵鴨,即使做月子,也是不肯隨意將息,勤快的連自己都都想誇自己——真是好兒媳。
可婆婆那張無波無瀾的臉始終找不出一點微波。
其實哪怕不鼓勵,彎個嘴巴,讓她知道一下婆婆的態度也好。
可是婆婆的臉像是塑膠熔融而成的。
直到那天,薛明珠經過村頭大樹,聽見嬸子的抱怨,說自家的兒媳婦的肚子實在不爭氣,連生了三個女娃,你說這可咋辦吧。
薛明珠想天下的婆婆都一個樣,自己得為李家填一個帶把兒小子,興許婆婆會放開她的冷漠。
薛明珠努力和李寶才造娃。
可是家中的氛圍卻越發怪起來,婆婆劉娥子澆院子時,總會忘記關水閘,結果下班回來的院子裡像經歷了一場暴風雨。
娃子拉屎用完的尿布說扔就扔,好幾次,薛明珠以為屋子裡老鼠的屍體味,結果大掃除時,在桌子下看見了已經發褐色的一坨屎。
薛明珠問李寶才,李寶才說,“媽老了,這都很正常。”
薛明珠的心越發地焦急起來,她的肚子還沒動靜。
懷女娃的時候只一次,這次怎麼不太順利?
隨著日子的流逝,薛明珠和李寶才漸漸沒了當初那般的激情與留戀,像是例行公事般,每次都草草了事。
有幾次,李寶才突然停了下來,薛明珠推了推他,竟然睡著了。
夫妻二人去醫院檢查,醫生只送了一句話:這事著急不來。
薛明珠終於懷孕了,只是她想先保密,等一個合適的時機,只是什麼才是合適的時機。
薛明珠等待的合適的時機是什麼?
發工資?
女兒生日?
婆婆的笑臉?
這些她生命中位列前三的喜慶日子?還是什麼?不過她似乎享受這個等待的過程,每天工作家裡兩頭跑,即使累了,也會摸一下肚子,笑容旋即驅散所有的疲憊。
幾日後,磚廠裡有一個跑差對的活,需要在外地待上一個月,李寶才猶豫著要不要去,誰知劉娥子當下做了決斷,“你是男人,賺點錢還猶豫什麼,怎麼捨不得媳婦。”
薛明珠張張嘴,最終沒有說什麼。
上車餃子下車麵條,薛明珠一大早煮了一鍋餃子,趴在李寶才耳朵邊說,“我等你回來吃麵條,到時候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那年的冷空氣來的特別早,一場秋雨後溫度就直線地落了下來。
薛明珠每天計算著日子,還有十天,還有五天,快要三天的時候,李寶才打來電話,說,“可能晚些才出發,天氣不好,大雨綿綿,路不好走。”
薛明珠心裡不知為何,總是發慌。
一天打了好幾通電話過去。
那一次電話那頭沒了人接,只剩下那句你撥打的電話暫時無法接通,薛明珠狠狠的,“這傢伙,看回來不收拾你。”
然而,黑暗的一天來了,迎接薛明珠的是醫院的一張李寶才的死亡通知:患者李寶才,頭部重創,失血過多,不治而亡。
薛明珠掀開雪白的蓋布,看著面部安詳的李寶才,她始終不夠冷靜,捂嘴嗚咽起來,拉著李寶才僵硬的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腹部,“寶才,咱們有孩子了。”
“寶才,你聽見沒。”
一顆豆大的淚珠啪的落下洇進被單,又一滴.......
“咱們......有孩子了。”
“聽說一車子的人全部喪命了。”村頭大樹下那群娘們依舊飢渴地議論著。
劉娥子跳躍過來,大笑,“一車子人全喪命了,嘻嘻。”
最後揪起額頭前的一縷碎髮,吹了一下,“全喪命了耶!”
那眼神深邃的可怕,一樹下的人都在嘆息,“沒了兒子的可憐女人啊!”
“是啊!你看以前的劉娥子多麼風騷。”
“如今倒成了這樣。”
幾個娘們依舊議論著,只當是劉娥子接受不了兒子的死,而只有劉蛾子自己知道。
當初兒子說晚些回來時,她是如何打電話告訴他,他不是他兒子,是她的丈夫和別的女人生的野種。
劉娥子能想象齣兒子冒著大雨回來的著急蠻荒的模樣,還有耳邊車子落入懸崖的彭東聲以及薛明珠的停不下來的哭聲。
她興奮又激動。
可是薛明珠在兒子死後為什麼還那麼堅強,能做的,該乾的一樣不落下,她不應該和自己一樣墮落下去嘛,為什麼她還活的那麼充實,那麼幸福。
劉娥子不懂。
直到薛明珠給她擦身子時,劉蛾子明白了。
那是她花了一輩子也不能領會的道理:貪嗔痴愛惡欲,可以輕於鴻毛,可以重用泰山。
而薛明珠年紀輕輕的就做到了,也活該她幸福。
劉娥子笑了,那是薛明珠一直在等待的態度,卻在這樣的時機。
-喵姐的第590個故事-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