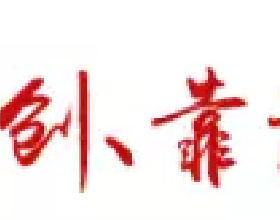惠師記憶
原創 李玉德
“泱泱大學止至善,巍巍黌宮立東南。”在一個深冬霧霾的天氣裡,偶有機會,我又回到了闊別三十餘年的母校---山東省立惠民師範學校,簡稱惠師。惠師位於惠民老城東南方巍巍峨峨的老城牆下,建校幾十年來,為惠民地區(包括現在的濱州市、東營市和淄博市的桓臺縣、高青縣)培養和造就了無數人才,她在山東教育戰線佔有一席之地,也是人們敬仰的育人黌門,用“泱泱大學止至善”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霧霾下的惠城如同我的記憶,時而朦朧,時而分明。當走到通往母校的必經之途——大寺牌樓時,母校的過往一下子湧上了心頭。駐足審視,只見牌樓孑然挺立於陰晦的街頭,兩邊硃紅色的明柱也已油漆斑駁,高大雄偉的牌樓已失去了往日的風采,給人一種蒼涼的感覺。穿過牌樓,當終於走過零落不堪、坑坑窪窪的街道、向右向左一拐時,曾經魂牽夢縈的校門就到了眼前。抬眼望去,校門映入眼簾,看上去猶如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可憐兮兮地矗立在冷風裡,完全沒有了心中常常憶起的風采和雄偉,曾耀眼醒目的立額長扁也早已沒有了蹤影。待轉身欲進母校時,一道鏽跡斑駁的鐵門阻斷了進校的甬道,順鐵門空隙向裡望去,目光所及是一派沉寂。曾經朝氣勃勃的校園看上去卻是滿眼的蕭索。面對此景,心中不免疑惑起來,這就是我曾經的母校嗎?我所記得母校全不如此,但細想起來,也說不出有什麼不一樣來,心中不免自我安慰起來,也許母校原本就是如此吧!只是,校門已換成“惠民縣第一中學東校區”的牌子顯得格外扎眼,似乎它原本就不應該懸掛在這裡,一種鳩佔鵲巢的感覺在心底升騰。母校易主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由她更換的校牌足以證明。校址雖在,卻已物是人非,留下的只是一具軀殼罷了……此時此刻,一種難抑的情緒湧上心頭,“試從絕頂高呼:問!問!問!這半江月,誰家之物?且向危樓附首:看!看!看!哪一塊雲,是我的天?”佇立校門,入學的情景彷彿又到了眼前,校門口歡迎新生入學的橫幅和兩側的五彩旗迎風招展。同學們懷著激動的心情,洋溢著青春的笑臉,肩負著希望的行囊,邁著自信而又憧憬的腳步,從四面八方湧進了學校。開學典禮上,教務主任張雲亭老師那抑揚頓挫的聲音又似乎在耳邊響起:我們學校有著光榮的歷史,始建於1948年10月,起初在渤海行署,惠民城東北,馬畫匠村借用破廟和民房建“渤海後期師範”,1949年春,遷至惠民城內西門街,6月又遷至城內文化街至今。1950年5月,惠民專區建後,“渤海後期師範學校”改為“山東省立惠民師範學校”。1952年春改為“山東省惠民師範學校”。惠師的首任校長是關鋒。提起關鋒,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記得,他曾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駐足校門,一下子打開了記憶的閘門。彷彿,校園黎明前薄霧濛濛中,起床號聲又驟然響起,同學們在匆忙中奔向操場,深冬的寒風吹進了脖領,吹紅了鼻尖和臉孔。哨聲、口號聲、跑步聲連成莊嚴的軍陣聲,寒冷中嘴巴吼出去的熱氣和頭頂的熱氣在薄霧中升騰……早操在食堂飯香的誘惑下終於停下了腳步,下操的同學們一下湧滿了餐廳,去享受那一粥一菜兩饅頭的國家待遇了。那時候大中專生上學,包括生活,都是免費的。日復一日的飽餐終日在有所用心中度過。當時同學們巳經習慣了這一切,一切覺得都是正常,一切都是應該享受,不需要感恩,也沒人要求感恩。然而,今天的學生想求得這種賜予已經是一種妄想。
入學伊始,讓我記憶最深的是學校甬道旁黑板報的報頭了,“讀書苦,苦讀書,苦盡甜來人。”報頭讓人震撼和新奇,但道理淺顯而準確。莘莘學子競走高考路,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十年寒窗,含辛茹苦,書山題海,艱難跋涉,一朝成功,農業戶口就會轉為非農業戶口,立馬就有了糧油指標,立馬就有了生活補貼,在那個生活困難的年月裡,最直接的兌現就是立馬由糠餑餑換上了大白饅頭。苦盡甜來是最恰當,也是最通俗的高考真理。和古人說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異工同曲。柳青的《創業史》上也有一句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要緊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所以從某個角度上講,苦盡甜來也是一種對機遇的把握。這報頭也讓我從志得意滿中重新審視這條從校門口到教學樓用青磚立起的凹凸不平的甬道,這條路既是同學們的上學路,也是同學們的求知路。這條路,也應該是直接通往同學們邁出校園後的人生之路。入學起初,我是恵師82級四班的學生,班主任是李風坤老師,李老師既飽經學問,又是一位穿著樸素、為人樸實、待人和善、令人敬重的長者。李老師的數學課淺顯易懂,有條不紊,娓娓道來,在不知不覺中就印入了腦海。對待學生更是和藹可親,有一次,有位同學請假超假了,李老師故作嚴厲地說,“再不到校,同學們就把他的饅頭吃了!”結果引得全班同學轟堂大笑。到了83年,我無緣再聆聽李風坤老師的教誨。經過考試,我又進入了生物專業班學習。生物專業班是一個八十個學生的大班,班主任是做事幹練,工作能力強,教學優秀的李洪傑老師。記憶從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一首《楓葉飄》的歌曲又在教學樓的臺階上響起,歌手是八一級的一個男生。利用晚點的時間,他已經不是第一次唱這首歌了,“楓葉飄,楓葉飄,楓枝搖,楓枝搖。楓葉不知飄何處,楓枝搖過……”原唱好像是李雙江吧!這男同學在沒有伴奏的情況下也唱得悲悲切切…… 記憶深處的還有八二級四班一個女同學的演唱,元旦晚會上,她的一首《知音》曾轟動全校,“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韻依依。一聲聲,如泣如訴如悲啼,嘆的是將軍拔劍南天起,我願做長鳳繞戰旗……”真個是餘音繞樑,三日不絕。為此同學們送她一綽號叫“山青青”,讓這綽號鬧的,卻把她的真實姓名給忘卻了。“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惠師的讀書聲,惠師的書香,惠師的快樂,在悠揚的歌聲裡飛揚。那時候,課休時間教學樓上的廣播都在不停地播放歌曲,而且是反覆地播放一首《達坂城的姑娘》,記得歌詞挺有意思的:“大阪城的石頭硬又平呀西瓜是大又甜大阪城的姑娘辮子長呀兩個眼睛真漂亮……”後來好像換了一首《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當然,大喇叭也不單單播放歌曲,有一段時間的確還播放過小說,小說的名字忘了,錄音的是蔡曉光老師,蔡老師那帶有磁性的朗讀聲至今還記憶猶新。惠師的歌聲不但留在了記憶裡,同時也標註上了環境、天氣、人物、情感的色彩,甚至連聽歌時的感觸,都烙印在了記憶的深處。後來,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再聽到惠師期間那熟悉的歌聲,心中不免會激起層層漣漪。如果說人生是一本書,那麼惠師生活便是書中最美麗的一頁;如果說人生是一臺戲,那麼惠師生活便是戲中最精彩的一幕;如果說人生是一次從降生到死亡的長途旅行,那麼擁有惠師生活的我們,看到的就是一道最靚麗的風景。回憶母校和過往,人們往往用美好的記憶來表達。其實,真實的記憶卻不一定全是美好,所謂的美好,不過是過來人表達的一種追思而已。或許當時的經歷本來十分平淡,後來拿出來一曬也就感覺美好了。比如漢代的一塊極普通的瓦片,如果儲存到現在拿出來,那不管它形象的美醜,人們必定會認為它珍貴和美好一樣,沒有人忍心去挑剔它的不足或醜陋。而我的記憶裡卻也有這麼一片瓦,什麼時候拿出來都應該不算美好。也是在冬季,也是在惠師,我的髕骨脫臼了。脫臼,這是可以肯定的,由本人腿部的劇痛和不能站立可以證明。這是一個無意的傷害,是因為我和同學開玩笑造成的,本人可以確認,同學絕對是無意的,或者說是絕無惡意。雖然一時不清楚傷勢如何,但清楚的是,自己已經不能下床行走了,不能去出早操了,不能去上課了,不能去食堂打飯了……這年的冬天感覺特別得寒冷,當同學們都走出宿舍走向教室的時候,能容納二十幾人居住的空曠大房子裡就孤零零地丟下了我一個人。讓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宿舍之大,世界之靜。宿舍裡沒有一絲熱氣,有的只是從窗戶上吹進的嗚嗚作響的冷風。特別是到了日落黃昏的時候,讓我第一次領略到了什麼是孤獨,而且不清楚這樣的孤獨何時是一個盡頭。甚至,我感覺到了宛如一種死亡,不管我怎麼努力,都無法加入活著的世界。對我的缺課,是沒有人責怪的,也沒有人過問。此間,我感覺到了自己的“無”,或許自己真得不存在了,人真可憐,那時候,最期盼的就是一聲責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我找到一種存在感。但我的存在又很快就被證明了,因為有一個同學在課堂上大聲公開宣佈了我某種生活上的不便,此訊息讓我的確感覺到了自己的存在,有我屈辱的淚水可以證明。我似乎一下子被人扒光了衣服,而且是在課堂上,教室裡,裸奔!讓我第一次有了並且不得不接受的人生屈辱。“看破紅塵嚇破膽,識盡人情傷盡心”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大都是在人失意的時候才能夠體會得到吧。然而,人間自有真情在,期間那些給我打飯、送飯,扶我行走,照料我日常生活的同學們,尤其是我回家養傷期間多次探望關心我的同學們,都時時刻刻記在了心裡,以至終身難忘。這樣的情誼在我落難的時候,顯得尤為珍貴。謝謝了!同學們,請收下我相隔三十餘年真誠的謝意!畢業的時候,腿還是瘸的,和我開玩笑的同學雖從未主動和我聯絡,我想他一定會默默地關心著我。我可以告訴那些關心我的,那些很難再見到的同學們,我腿已經不瘸了,只是到了陰天下雨有點痛,特別是到了寒冷的冬季。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往事如同莊周夢蝶一樣,都成為了幻影。自己感傷的情懷,只能像託身杜鵑的望帝那樣,化為無窮無盡的哀鳴。人生,都會有夢。然而,夢和夢想是有極大區別的,一般的祝福語都是“夢想成真”,由此可見夢想之美好便非同一般。而夢則不會有褒貶之分,它應該是中性的,但真實的夢境卻有好壞之分。畢業幾十年來,我經常重複一個夢。夢裡,我分明還在惠師上學,但忽然找不到學校了,甚至連去學校的路都找不到了,千找萬找終於找到學校了,卻又找不到教學樓了,找到教學樓了又找不到教室了,找到教室了又找不到課桌了,找到課桌了又找不到課本了……往往驟然間,在對母校、教室、課程的陌生和茫然中驚醒。母校呀,不知您為何要送我這麼一個不了夢。“同學們,不該發生的事情在我們學校發生了!”這是張校長蒼涼而又無可奈何的聲音,從神態和表情上足以體現出他的痛心。張校長身穿寬大的中山裝,單薄的身體似乎有些不勝其重,瘦弱的身軀無力地站立在教學樓正門的臺階上,嘶啞的嗓音響徹了學校每一個角落。張校長的左邊是省教育廳的領導,右邊是惠民地區教育局的領導,臺階下是全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會場一派肅然。也就是幾天前,學生和學校食堂人員因伙食發生衝突。因事件沒有得到及時處理,事態不斷蔓延擴大,後來演化成學生靜坐和絕食,最終引起省教育廳的高度重視,並對事件當事人做出嚴肅處理,儒雅而和藹的張校長也被迫離職。這是張校長的最後一次主持惠師師生大會和講話,隨著這次講話的結束,張校長便黯然離去了。當張校長和學校老師們揮手握別時,才見他慮及學校前途,慘然至於泣下。有道是, 天下事了猶未了不了了之。事態的平復讓校園又恢復了原來的平靜,時光一如往常的在指縫間流失。同學當初的衝動換來的不過是日後的談資。同學們仍在早操、早飯、早讀、上課、下課、晚自習、讀書、歌唱的充實而歡娛的氣氛中一天天地度過。這重複中,同學們多了一條經常光顧閱覽室的路。我在閱覽室第一次讀到了斯諾的《西行漫記》,閱覽室也給我們認知的世界又打開了另一扇窗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很快,我們惠民師範八二級的同學到了畢業實習季。我實習的學校是陽信一中,實習的科目是植物課,三個月的實習緊張而短暫,待我上完最後一節課後,我們的實習就圓滿結束了。可誰知,在我臨上課時,備受師生尊重的純學者型的李光尙老師趕到了。因為是實習中最後一節課了,抱有僥倖心理的我,沒有做充分準備。但老師卻是一定要聽課,而且還邀請了陽信一中的校領導和任課老師一同聽課。事到臨頭,我只好硬著頭皮上架了。這節課講的是光合作用,誰知忙中出錯,課程即將結束,竟把光合作用的意義忘講了。前排一女生小聲地對同位講:“老師沒講光合作用的意義!”聲音雖小,被我聽到了耳朵裡。此刻,我也見到了李老師那期待和關切的目光。於是我即興發揮,“同學們,講到這裡,我們不難總結出光合作用的意義……”僥倖過關,心裡不免有些緊張,卻贏得了李老師的鼓勵。老師還一再說,“順序顛倒得好!”老師的表揚讓我實在是慚愧至極。老師,事隔三十年後,學生再一次說:謝謝您!然而,這件事卻對應了一句“種豆得瓜”的人生真諦。畢業的步伐如田徑運動會上的跑表,在急!急!急!地奔跑著。我和我的同學們終於在跑表地催促中到達了終點,迎來了畢業的這一天。當我離校時,也是佇立在這校門口,恭恭敬敬地對著校門鞠了一躬,謝謝您!我的母校,我的老師。在茫然和失落中我和同學們離開了母校。“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可我不是飛鴻,沒有超然物外的境界,也很在意雪泥中的爪痕。然而,找遍記憶的每一個角落,竟然無復指爪的痕跡。有的,只是膚淺的記憶。也許這些記憶在流失的歲月裡也會越來越蒼白吧。天漸漸的黑了下來,霧霾也顯得更加嚴重,惠師的輪廓也更加模糊起來。也許回首和不堪回首都是同樣的感知,那些當年的同學,那些不能再重踏母校,不能重溫舊跡的同學,或許很難擁有我當下的這份情感,從這個角度上講,我擁有這份情感實屬相當的幸運。就讓我把這份情感在這裡分享給我的同學,我的母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