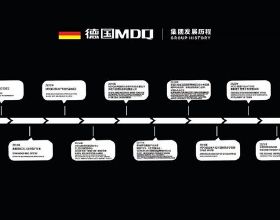“我從小不愛學習,十八歲跟著我父親出來打工,天南海北的跑過不少地方,最開始的時候在建築工地上幹,從小沒吃過那麼大苦,受不了,就跑到南方那些工廠裡幹,沒文化,兜兜轉轉,幹幾年還是個工人,技術沒有,錢也沒掙到。”
說這話的人我叫他老陳,看著五十歲左右,頭髮花白且稀疏,滿面都是歲月。其實老陳是八一年生人,正經的八零後。
見到老陳是在他上班的宿舍。
一個普通房間裡有四個架子床,不過只住了老陳一個人,滿屋蕭索,一種塵土的氣息。架子床上層隨意擺著破舊的被褥和日用品,其中兩個下鋪鋪有被褥,兩個下鋪還有做飯的簡單廚具。
一張桌子,桌子上有茶杯,水壺,菸灰缸,空煙盒,煙,打火機。
“隨便坐,別嫌棄。”
“前幾年廠子活多,人也多,這兩年,沒活了,人也快跑完了。”他見我打量那些空床。
兩根菸,煙是黃金葉,兩杯茶,茶是普通花茶。
煙霧繚繞,窗戶透進來一縷陽光,老陳就坐在陽光中,看不真切。
“眼看著到了娶媳婦的年紀,人介紹的,隔壁村姑娘,見了幾次面,就過了門,是個過日子的,跟著我,吃了不少苦啊。25歲那年,有了我兒子,日子過的惜惶啊,就跟著人來了這裡,下煤窯,這回沒挑了,啥掙錢幹啥。”
“媳婦一直在老家嗎?”我問他。
“剛結婚的時候,跟著我跑了一年多,有了大娃就沒再出來了。”
“幾個孩子?”
“倆,老二是個女娃,上幼兒園。”老陳又拿了支菸給我,我推開了,我沒煙癮,更多是為了交際。他沒再抽,拿在手裡把玩著。
“六年前,老家那道從小就鑽進鑽出的爛山溝,說是啥大峽谷,開發成了旅遊區,我就從煤礦回了村,買了個二手車,跑了出租。”老陳點上了那支菸,狠狠的吸了一口,菸頭在陰影裡都紅了一下,然後慢慢的吐出兩個菸圈,晃晃悠悠的擴散開來。菸圈散開的盡頭,老陳看向我的的眼神裡有一種先前沒有的光。
“那是我這輩子過的最有勁的兩年。”對,他說的是有勁。終於可以不用一家人分隔兩地,可以照顧老人,可以和日益長大的兒子舒緩隔閡,還有了一個女兒,日子一天天好起來,渾身感覺都是使不完的勁。
他先是低下了頭,抽了最後一口快要燃盡的煙,沒見他吐出來,就那麼突然的沉默了。陽光離開了他,就像是他躲在陰影裡,低著頭,我看不見他的臉。
感覺過了很久,也可能只是一瞬,他抬起頭,那最後吸入肺裡的煙吐了出來,像是一聲嘆息,又像是沒有。
老陳身體前傾,他的頭恰好伸進了陽光裡,朦朧中我看見他的眼,那道光沒有了。他就那麼盯著我,帶著問詢又或不是,他說“你信命嗎?”
“旅遊區搞了沒兩年,遊客慢慢的少了,跑出租的人卻越來越多了,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他的身體收了回去,躲在陰影裡。
那是一個陰雨天,老陳在長途車站附近等了兩個多小時,沒有拉到一個人。他決定回家,父親的胃疼了很久了,一直沒去看過,就是疼了吃點胃藥。“農村人命硬,有點不舒服都是硬抗。”父親已經扛了很久,老陳準備趁著今天沒生意,帶父親去看看。
命運真的和老陳在開玩笑,老陳的父親被診斷為胃癌。“醫生說來的還不算晚,有的治。”
“現在你父親身體還行吧?”我帶著一絲希翼。
“沒了。”
看到老陳帶他出了縣醫院直奔市裡。老父親明白了,站在市醫院的門口,怎麼說都要回家,硬說他感覺好了不疼了。沒辦法,老陳只好說了實話,告訴父親還有的治,治好了還能活好多年。
“我給我父親說,你看我這日子,你要是治好了,還能幫我幾年,就這麼走了,誰來幫我!我知道他怕花錢,我知道他捨不得走,他的兒子過得不好,孫子還小。我只能這樣勸他。”他用狠吸一口煙,掩飾自己哽咽的語氣,但他的手分明在抖。
但他還是沒有留住父親,手術後三個月多月的一天,正在跑車的他接到了妻子的電話,父親昏倒了。二十多天後,父親走了。
父親的走,花光了他的積蓄,也好似抽走了他的脊樑。
“你們家就你一個?”
“還有兩個姐姐,她們過的還不如我,再說在我們農村,嫁出去的女兒,我不能花他們的錢。”
父親走後半年,安頓好妻兒,老陳又來到了這裡,雖然離家遠,但賺得多。
“也虧的我來的早點,這兩年疫情,老家的旅遊區徹底涼了。這裡都是煤,幾乎沒有影響。”
“有什麼打算嗎?過幾年你還乾的動煤礦嗎?”
“我這樣的人能有什麼打算,幹不動再說吧。”
“有打算就是看能不能熬成正式工吧,這裡好壞算是國企的下屬單位,每年都有幾個指標。不過大概輪不到我吧。”
“人這一輩子,有多少錢都是一定的,賺了不屬於自己的錢,都得吐出去。”
“我這輩子命裡沒錢。”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