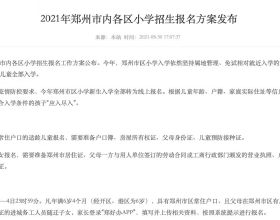唐婉與陸游的緣分,不過是五代那首《擷芳詞》:都如夢,何曾共,可憐孤似釵頭鳳。其間多少求不得,愛別離。
她頗負才名,聲名在外,愛慕之人自是不在少數,他也是大家之子,所以,他們她另嫁,他另娶。自以為這樣就完美錯過,兩不相欠。他們都自以為是,刻骨的痴纏眷戀,桃花樹下的蹁躚,山盟海誓都已如風消散。
他們的愛不過若夢浮生,幾何為歡。所謂的伉儷情深,相期始終,都不過空潭雲影,悠悠天地間眾生一抔黃土而已。唐婉,或許正如《沈園》: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她曾經也是他的驚鴻,不過“情深不壽,慧極必傷”,所以他們的愛夭折了,她成了失情的鳳凰,將所有過往,所有情凝成心頭一點硃砂。
他們都低估了愛情,十年江湖夜雨,幾多沉浮,說不清究竟誰可憐。他們都不過是封建的祭品,註定不會有善終。此時的重逢,他以一首“一懷愁緒,幾年離索”輕易的揭開早已落痂的傷疤,黑暗瘋狂的舔舐著她的傷口,想起“山盟雖在,錦書難託”,終於吞噬了她。如果說陸游是空餘遺恨,一曲《釵頭鳳》讓她相思成灰,等待她的便只有死亡。
道是當年春,不復當年人。十年江湖路,歸來已不復,曾經的情愛,都早已封緘。放翁的“咽淚裝歡”的苦她豈能不知,只不過早已習慣在無人時舔舐傷口。她以身作囚籠,囚禁著心魔,直到死亡到來。不必說她早已入詩箋,她應當死,所以成就了一曲悲歌,縱新夫虛谷,綠蟻新醅,傷過的情,再也回不來了,只餘下“春如舊,人空瘦”的為是人非而已。
不過,伊人已去,無從問那年是何年,今夕又何夕了。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而如今,在這荒蕪的彼岸,她如一朵花在黑暗中默默成長,默默綻放,又默默老去,縱然這一切只有曾經的陸游可見,即便是這樣,她便也不會覺得孤單了。唐婉與陸游的緣分,不過是五代那首《擷芳詞》:都如夢,何曾共,可憐孤似釵頭鳳。其間多少求不得,愛別離。
她頗負才名,聲名在外,愛慕之人自是不在少數,他也是大家之子,所以,他們她另嫁,他另娶。自以為這樣就完美錯過,兩不相欠。他們都自以為是,刻骨的痴纏眷戀,桃花樹下的蹁躚,山盟海誓都已如風消散。
他們的愛不過若夢浮生,幾何為歡。所謂的伉儷情深,相期始終,都不過空潭雲影,悠悠天地間眾生一抔黃土而已。唐婉,或許正如《沈園》: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她曾經也是他的驚鴻,不過“情深不壽,慧極必傷”,所以他們的愛夭折了,她成了失情的鳳凰,將所有過往,所有情凝成心頭一點硃砂。
他們都低估了愛情,十年江湖夜雨,幾多沉浮,說不清究竟誰可憐。他們都不過是封建的祭品,註定不會有善終。此時的重逢,他以一首“一懷愁緒,幾年離索”輕易的揭開早已落痂的傷疤,黑暗瘋狂的舔舐著她的傷口,想起“山盟雖在,錦書難託”,終於吞噬了她。如果說陸游是空餘遺恨,一曲《釵頭鳳》讓她相思成灰,等待她的便只有死亡。
道是當年春,不復當年人。十年江湖路,歸來已不復,曾經的情愛,都早已封緘。放翁的“咽淚裝歡”的苦她豈能不知,只不過早已習慣在無人時舔舐傷口。她以身作囚籠,囚禁著心魔,直到死亡到來。不必說她早已入詩箋,她應當死,所以成就了一曲悲歌,縱新夫虛谷,綠蟻新醅,傷過的情,再也回不來了,只餘下“春如舊,人空瘦”的為是人非而已。
不過,伊人已去,無從問那年是何年,今夕又何夕了。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而如今,在這荒蕪的彼岸,她如一朵花在黑暗中默默成長,默默綻放,又默默老去,縱然這一切只有曾經的陸游可見,即便是這樣,她便也不會覺得孤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