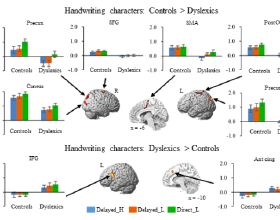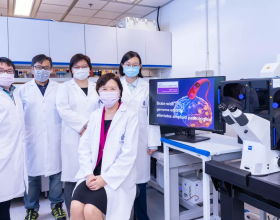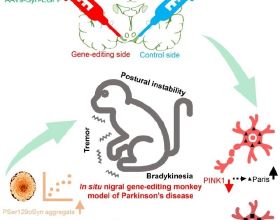由於外曾祖父這個“吃裡扒外”的保長種種的“通匪”行為,當局也已有察覺,不再信任,所以就早早地免去他保長的職務,並密切監視其行動。然而就是這段當保長的經歷,讓他在文革中被汙衊為歷史反革命,被殘酷地批鬥,受盡折磨。
歷次政治運動,為了完成上面給每個村定的批鬥指標,他都會被揪出來,或輕或重地被批鬥折磨一番。並連同其“販豬、轉房”等事也一起翻出來,作為“罪大惡極的罪證”來審判一番。最嚴重的一次,是被革委會判為無期徒刑。那次,為了迎合高漲的革命熱情,他們是想立功判個死刑出來的,但是經過多次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多少次指使人誣告和構陷罪狀,但始終也沒找出他“傷天害理”、“剝削鄉民”、“殺人害命”的死罪證據來,最多隻能以“自絕人命、拒不交代”為罪名判個無期徒刑。但是,死刑犯的滋味得讓他享受享受。
那一夜,他和另外四個也不知因啥罪狀被判了“死刑”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關在一起,等待第二天群眾公審宣判後就地正法。
“那天的夜太黑太靜太漫長了!”外曾祖父後來回憶道。
那一夜,腦子裡就像放電影一樣,他回憶了自己的前半生,他以為那就是他短暫的一生的最後一個夜晚。不知道這無邊的黑夜會持續多久,這濃烈並讓人窒息的黑夜,深邃無邊。不知道在死之前,天會不會放亮,如果死亡是不可避免,他只想死在陽光下。如果非得挨那一槍,他希望那子彈是衝著面門而來,而不是後腦勺。
天還是破曉了,民兵用一個竹筐送進來熱氣騰騰的飯食,無非饅頭、稀粥這些現在看來平常,但當時已經是不常吃到的好吃食了。唯一的驚喜也是驚嚇的是最後端出來的一小碗紅肉蓋面和一酒盅燒酒,標誌著這一餐的不尋常。
古往今來,南北東西的“斷頭飯”,也沒一個統一的規格標準。大家實在太餓了,也顧不上這是人間的最後一餐,三口五口都吃了個精光。
“捱餓半輩子,到死得混個飽死鬼!”大家或許都這麼想。
或許大家的頭腦都是悶悶的,身不由己也就什麼都不用想了。這人間也不過如此,下輩子再也不來了,這一句是我給杜撰的。
一會兒監門外開來一輛大卡車,他們一個個戴著手銬被押上車。車輛在冬日乾燥的土路上顛簸向前,車輪過處塵土飛揚。不到一個時辰,車輛就到了縣城東頭的廟坪。土臺上已經臨時搭建起了主席臺,下面用白灰圈出一個大空地,前面一側還用白灰標出十個小圈圈,幾個民兵保持高度戒備。會場周圍及遠處的土坡上、樹杈上也都擠滿了人,大家都在搶佔一個絕佳的位置,觀看今天的這場大戲。
外祖父他們被押進會場時,那十個圈圈已經被佔滿了五個。剩下的五個白圈圈在焦急地等待著他們。他們被架著小跑站到自己的圈圈裡,胸前掛著寫著自己名號打著紅叉叉的大木牌,身後站著兩名帶著紅袖箍的民兵。圈內的死刑犯和圈外的群眾,都在焦急地等待著那些坐主席臺的大人物。這時候,有一個圈圈內的囚犯癱坐在了地上,人群中一陣騷動。
大概上午九點的時候,幾輛吉普車開進了會場。車上下來十來個幹部模樣的人,緩步走上主席臺。一個個領導致辭,一項項罪狀宣佈,他們都說些啥,外曾祖父說他其實一句都沒聽清楚。只聽到一念到誰的名字,“罪名成立!立即逮捕!就地正法!”幾個排比句一出來,這個囚犯就被身後的民兵朝膝蓋後腿窩一腳給踹倒跪在地上,然後拿出準備好的麻繩來個五花大綁。每次做完這一套乾脆熟練的動作,都會迎來人群中一陣歡呼。
等最後一名囚犯被宣判結束,最大的領導發表了義憤填膺、激揚慷慨的總結講話後,他們就被押上了一輛卡車,準備去後山背陰處執行槍決。在車上,就有幾個囚犯已經腿軟地站不住了,也有人已經把早晨吃的紅肉吐出來了。
後山背陰處,殘雪還未完全消融,積雪周邊一團溼跡。他們被分散開面朝山坡跪成一排,後面各站著一個荷槍實彈的民兵。他們個個面戴著白口罩,手戴白手套,舉著槍,用黑洞洞的槍口對準面前的囚犯。
有人拿著名單,再次逐一核驗完死囚犯的身份,對“監斬官”一個示意。
“監斬官”立即下令:“午時已到,立即行刑!”
砰砰砰幾聲槍響,幾乎是在同一瞬間。外曾祖父說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身旁的囚犯都倒在了地上,而他只感覺到噁心,卻感覺不到一絲絲的疼。地上的雪水或者是尿水染溼了褲子。後來才知道,那天連他有三個囚犯是作陪的,他們三個被判的是死緩或者無期。
在勞改農場受盡折磨多年,後因病得奄奄一息,被送回來監外執行,病養到能爬起來下地後,就開始在農業社繼續接受勞動改造。至此十多年,作為一個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囚犯,在農業社幹最髒最苦的活,還不得記工分。兒子兒媳、孫子孫女們受此牽連,擔驚受怕,受盡村裡支書、貧協隊長等幹部的欺凌,也遭受著村民的白眼和無端的欺辱。
但是對於外曾祖父來說,總算是有了參加勞動的權利。幹活是最自由和享受的活動,雖然不給記工分,但是自己卻是一點不敢偷閒地積極參加勞動。那些年,外曾祖父常常是白天參加勞動,晚上接受審查和批鬥,眼圈時常都熬爛了,讓親人看著心疼。
文章摘自本文作者《夢迴塬上》一書,版權歸作者所有—
感謝關注,持續更新,關注微信公眾號“昨日旋律”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