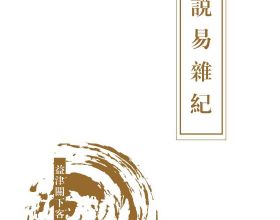作者 王偉偉
★ 為紀念父親誕辰113週年而作
海軍上將 王宏坤
(1909--1993)
上級與下級手心和手背
1968年,原海軍南海艦隊副司令王政柱(開國少將),帶著全家調北京待命時(任海軍後勤部部長),由於當時任命還未下來,他們全家沒有分配住房。
圖為開國海軍少將王政柱
1932年3月,父親時任紅四方面軍紅十師師長,救下了被打成反革命15歲的王政柱。被解救後,他成了父親在紅軍時的第一位秘書。海軍成立後,他又成了父親的老部下,兩人關係深厚。
所以,當父親知道王政柱全家在北京居無住所,十分關愛,安排他本人住在海軍第一招待所,而寧可讓自己家子女想辦法擠房子住,也得讓其夫人與三個子女住進我們家。一般都是上級住下級家,哪有上級家給下級騰房子住的,恐怕世上也少有父親這樣的高階幹部會為了關照他的下屬而這麼做的。
與王政柱同期上調北京的還有在紅軍時期,父親任紅四軍軍長時,任四軍軍部偵察科長的潘焱,他被任命為海軍參謀長。這兩個人都是父親先在紅軍,後在海軍的老部下,他們都是在紅軍“肅反”時,被父親所救。父親與他們都有著深厚的感情,對父親而言,這兩人就是他的手心手背,十分關愛。
深夜的電話鈴聲
潘焱的女兒潘豫沙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1967年冬‘文革’時,我父親任北海艦隊副司令,白天堅持戰備值班,晚上還要被造反派批鬥,身體受到極大傷害,血壓長高達200多。有一天晚上,他被潛校造反派批鬥到十二點,他們忽然心血來潮,要拉父親去北京批鬥。但是已沒有火車了,就硬要押他步行去北京。為了救父親,母親在萬般無奈下,一方面給艦隊報告了此事,讓他們想辦法通知北京阻止;另一方面只好半夜給王伯伯打電話求救。
圖為1955年的何挺阿姨
王伯伯吃了安眠藥已經熟睡,卻被來自青島這兩個電話叫醒。他聽聞母親的訴說,非常生氣,寬慰我母親後,馬上給艦隊打電話,讓艦隊馬上派人追回!命令造反派一定要確保潘焱安全。並表示送回後,要馬上向他報告。
圖為潘焱將軍和夫人何挺阿姨
王伯伯也沒睡覺,一直在電話旁焦急地等了一夜,直到我母親給他回電,告知父親已安全到家,他才放心去休息。這樣才保住了父親一條命,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潘焱夫人何挺阿姨在她的回憶錄《春梅晚唱》中寫道:“我給海軍黨委寫信,反映當前潘焱同志血壓200多,再鬥下去,有生命危險,我把信寄給了在北京師大一附中上學的大女兒,叫她見信後立即送到王宏坤政委家裡,請馮阿姨(王宏坤的夫人)轉交給王政委。因寄到機關,怕造反派扣壓,只有走曲線了。很快,王宏坤批准調潘焱到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就這樣潘焱將軍徹底擺脫了造反派的糾纒,脫離了困境,被保護起來。
圖為何挺阿姨寫的回憶錄《春梅晚唱》
潘焱將軍的女兒潘豫沙深有感觸的提到另一件事:
“70年代初,一次父親的高血壓又犯了,病臥在床。一天,王政委親自來看望父親,誰都沒料到的是竟還帶來一位名中醫給父親把脈。
他對父親說‘我給你請了一位老中醫,讓他給你好好調理一下。’
他眼看著老中醫給父親把脈開藥。
送走醫生後,他又留下安慰父親,還跟父親聊了起來。
我當時就在場,很感動。這種上下級關係哪找去呀!在幾次生死關頭都是王伯伯出手相救,真是無以回報!老一輩的生死情誼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
(注:父親請的這位老中醫,應是二姐黎利的老師——廣安門中醫院的高輝遠先生)
淚水浸溼的記憶
原海軍大院門診部老護士劉淑敏在公眾號《歷史與傳承》,寫的文章“首長對我恩重如山”中,用親身體會寫出了父親對她,一個普通護士的關愛:
“1964年至1965年期間,我主要給海軍副司令員王宏坤首長做保健工作,接觸他及他家裡人時間較長。
圖為六十年代的劉淑敏
我起初去他家,也是很緊張的,怕幹不好被批評。事後才覺得,他家並不像我想象的那樣,兩位老人都和藹可親。家裡的孩子們都親切地叫我劉護士,在他們家中,我絲毫沒有低人一等的感覺。
一天,我去王副司令家做保健服務,正趕上我的身體有些不舒服,被馮處長(我母親)一眼看到了。就問:‘小劉,你怎麼了,臉色這麼難看?’
我跟她說了下身體狀況。她說:‘你這是缺乏營養,需要補。’
這時王副司令員正好過來,問怎麼回事。馮處長把我不舒服需要補的事向他說了一遍。
王副司令員上來就說:‘給她買個王八煮湯喝,補,記在我賬上。’
我聽後都傻眼了 :‘這說的是我?還是首長在開玩笑?’又想:‘這麼大首長怎麼會跟我這個無名小卒開玩笑。’我趕忙勸阻:‘首長,您別、別......’
沒等我說完,就聽王副司令員說:‘馮明英(我父親都是這樣稱呼母親的),你叫那個舒師傅去辦!’
舒師傅是炊事員,看來買王八給我補身子是真的。舒師傅有些不太願意,但不敢不辦。他買了一隻王八回來,結果給警衛員玩死了。第二天警衛員不敢說實話,只好說是被蚊子叮咬死的。首長聽了後就說:‘這樣的王八吃了會死人的,讓舒師傅再去買一隻,都記在我賬上。’
舒師傅遵命又去買了一隻。買完王八後偷偷對我說:‘小劉,你福氣不淺,這王八是在特供店買的,首長都捨不得買著吃,讓你給享受了。’
我聽後,鼻子發酸,兩眼裡的淚水唰唰直流。要知道,在那個年代物質缺乏,包括老首長家的收入也不算太高,而且家大開銷大,就是有錢也買不到需要的東西。我這個窮苦出身的孩子,是吃苦水長大的,從小又失去了母親,沒有得到母愛。連想都不敢想,首長和夫人對我這麼關懷,竟自己掏腰包給我補身子,把他該享受的待遇讓我享受了。我親生父母就是有條件也不一定能夠做到,他們比我的親生父母還要親。
這件事,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內心的感動成了神經質的刺激,我一想起這件事,就控制不住感情,就哭......”
身處逆境仍關愛他人
兩個老搭檔 相對靜無言
1959年廬山會議後,在全黨全軍展開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海軍也不例外。父親和羅舜初副司令員(開國中將)被當成彭黃在海軍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和檢查。最後,終因父親歷史上不是一方面軍,而是紅四方面軍的人,更不是三軍團的,與彭德懷沒有歷史淵源,加上資格老,而沒靠邊,儘管如此還是要被迫做檢查。
此時,父親因肺結核第二次住進北京阜外醫院,海軍主要領導到醫院看他時,一方面讓他好好住院,一方面又讓他就批彭的問題寫檢查。並講:不能住院了就不寫了。還說父親與彭德懷的關係還是密切的,“彭不是說:‘以後讓王宏坤與羅舜初來彙報’嗎?這些你要講清楚”。讓父親揭發羅舜初、鄧華。(因1956年10月,父親作為中國軍事代表團成員,曾與鄧華為團長的一行人,出訪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而鄧又被打成彭黃分子。)這些話都被在場的人聽到了。
圖為1956年10月,中國軍事代表團在南斯拉夫訪問。前排左一為父親、左二鄧華上將。
1960年海軍批彭德懷結束了,父親僥倖沒被趕出海軍。但是他的老搭檔,親密的戰友,海軍副司令員、海軍常委之一的羅舜初將軍卻被海軍打成了彭黃分子,趕出了海軍。
圖為開國海軍中將羅舜初
羅舜初任海軍副司令時,家裡人來人往,比較熱鬧,現在被打成彭黃分子,調離海軍了,家就冷清了。此時正值春節,本該熱熱鬧鬧的,家裡卻一片淒涼。往年來拜年的同級或下級幹部都遠離他家,躲了起來,生怕招惹是非。唯獨我父親頂著被株連的巨大壓力,一個人披著大衣到他家去專門看望羅舜初——這位與他生死與共的親密戰友。
他們最早相識於1935年7月,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新成立了紅軍總部,父親離任紅四軍軍長職務,調任紅軍副總參謀長,羅舜初由紅一方面軍調任總部二局代局長。從此,兩人建立起了幾十年的戰鬥友情。
進了他家,父親與羅舜初落座沙發,默默無語,倆人面對面抽著煙,就這樣相互看著、抽著,無聲地坐了半個多鐘頭,父親才依依不捨的起身離去。兩個人同病相憐,什麼都不用說了,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不用解釋,不用寬慰,此時無聲勝有聲,他們對視的雙眼已表達了一切。
父親想幫助他,但卻無能為力,因黨的紀律約束,他必須遵守和服從。他冒著被別人告發的風險來看羅將軍,儘管不能明言,卻已表達出父親對他的無比同情與支援,父親只能用這種沉默的方式來表達了。
與警衛員的最後告別
父親身居高位是這樣關心人,但當他自身有難時,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別人。
1978年10月下旬,父親的最後一位警衛員小王因受父親的株連,要被調走離開他,小王來跟父親告別。當時,我也在場。
沒想到的一幕發生了:小王走上前抱住了父親,父親伸出雙臂也摟住他。這時,小王眼中熱淚止不住地淌下來,哽咽著說:“首長,我調走了!”
只見父親也是熱淚盈眶,強忍著不讓淚水流下來,依依不捨。我們見狀趕緊安慰小王,表示不會忘記他,等以後條件好轉,我們會幫助他的。實際上,當時我們受父親株連,處境也是岌岌可危。我們是親屬,替父親去承擔著一切後果是必然的。我們認為:小王是被組織派來照顧首長的,與父親應無牽連。所以,我們明知今後也幫不了他,還是儘量安慰他。
在我的記憶裡,父親從沒有與我們子女這樣擁抱過,這是我有生以來唯一一次看見父親為了一個小戰士竟然如此動容,對父親來講這是從未有過的事。
父親是因自己讓小王無辜受了牽連而於心不忍,他覺得因自己耽誤了小王的前程(那時他還不是黨員,更甭說提幹了),而對不起這個無辜的小戰士。在他危難之時,他全然不考慮自己,而是想著小戰士的前途,為他擔憂,對此父親因無可奈何而感到不安。
圖為1978年10月中旬的榆次,父親與警衛員小王合影
小王自從調給父親當警衛員,一直對父親照顧有加,尤其是父親捱整期間,他不像有的工作人員嚇得撂挑子,給父親使臉子,鬧情緒,而是不離不棄,始終如一。父親被髮配到山西榆次市,他陪著去照顧,給父親燒洗澡水,想辦法給父親改善伙食。危難時刻見真心,父親在處境最困難時非常感謝他。
這些跟過父親的警衛員、公務員們,與父親基本是朝夕相處,比我們子女接觸父親的時間還長。所以,在工作人員眼裡,父親既是他們的首長、領導,又是他們的師長,更像是老父親,他們對父親都有著深厚的感情,從某種角度講,他們對父親的感情並不亞於我們子女 。
這個場景,小王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小王常對我動情地說:“首長曾與我說過一句話,至今我還記得,首長說:‘如果我以後能出來工作,不管你在哪裡,我都要把你找回來。’
每每想到這些,我都會流眼淚......”
正是出於他對父親的這份深厚的熱愛,2015年7月他不顧路途疲勞,遠赴千里專程來到湖北省麻城市乘馬崗鄉石槽衝村父親的墓地,給他敬愛的首長掃墓。
圖為2015年夏小王從北京專程來到父親的老家給他掃墓
父親留給我們無價之寶
回顧父親的一生,他之所以義無反顧地參加革命,源自於他出生在一個貧僱農家庭,深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艱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吃苦耐勞的品性和堅定的革命信念。在1926年他17歲時,就與我爺爺一起積極投身到農民運動中。1927年11月,他參加了舉世聞名的黃麻起義。大革命失敗,國民黨反動派到處抓他,為了生存,他只好外出去“跑反”。臨行前他與我奶奶去告別,奶奶捨不得他走直哭。父親安慰她說:“天不生無路之人,一顆露水養一棵草。”面對白色恐怖,父親還是那樣樂觀,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1929年2月14日(正月初五),他“跑反”回來後,馬上就上山找到他堂哥王樹聲,參加了紅軍。
圖為六十年代父親與他堂哥王樹聲大將
就在這一天他創造了“三個第一”,第一天參加紅軍,參加了第一場戰鬥,第一次負傷。
由於父親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勇於犧牲的精神,優秀的軍事天賦和良好的軍事素質,他參加紅軍三個月就入了黨,相繼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等職,在黨的培養下,在紅軍中成長很快,24歲就當上了紅四軍軍長。
在戰鬥中,父親創造出自己一系列特色的戰法,成為了紅四軍的主要戰將。在以後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的戰爭指揮藝術得到繼續提高和發揮。他的原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於1938年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的彙報中,給父親做出了“指揮沉著老辣,身經千百戰”的高度評價。
父親這些優秀品質,對幹部、戰士、人民群眾的關愛,得益於他貧苦的出身,深知無產階級相互關愛的重要;得益於紅軍建立時,就定下的官兵平等、官兵一致,愛護老百姓的建軍宗旨。他把體恤官兵,關愛人民群眾,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中,化作本能的行為,當成他的理所當然。
父親在我們眼裡高大威嚴,我們崇敬他,深深感受到他慈祥的父愛。但因他平時忙於工作,又與我們交談的少,他做的那些好事、善舉,又深藏不露,所以我們對父親並未真正的瞭解,看到的僅是些表面現象。直到這些年,透過微信結識了許多父親老部下的子女們,從他們及其父輩的文章裡,還有網路上收集的資訊中,才知道了父親那麼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感到父親非常的了不起,對他更加敬仰!
父親這些感人的故事,高尚的品德,給了我強烈的震撼,我意識到:父親對子女的愛那只是小愛,對他的下屬、他的戰士的那種真心實意的愛和政治上的關懷,才是他的大愛。也就理解他那樣的高階幹部,為什麼還有這種樸實的舉動了。那麼,他還有多少我們不知道的故事?我下決心要真正走進父親的心中,去了解他,讀懂他,去探索他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去了解他的高風亮節,他對黨,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他的大愛......
此後,我便開始蒐集整理父親的故事。整理蒐集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才使我真正走進父親的心中,讀懂了他。
圖為1961年冬全家福。前排左起母親、弟弟燕京、妹妹京利、父親,後排左起作者偉偉、堂姐素香、二姐黎利、大姐相持、大哥新中。
父親離開我們已29年了,他把一生都無私奉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他沒有給我們留下金銀財寶,房子、車子,但卻給我們留下了:他忠厚、老實、樸素的農民本色;他不畏艱險,面對困難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剛正不阿,為人正派的人格品質;他心懷寬廣,心中時刻裝著人民,處處為他人著想,一生所為閃爍著偉大的人性光芒。這些是影響我們一生最寶貴的財富!
圖為1993年4月25日父親生前最後的留影。左起弟弟燕京、父親、大哥新中的女兒佳佳。
最後,以我父親在其回憶錄《我的紅軍生涯》中,其所寫的序中一段話為本篇結束。
“今天,時代和環境不同了,我軍的番號也幾經變化,但是,人民軍隊的本質,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變,紅軍的精神和傳統不能丟。在那艱苦鬥爭的歲月裡,成千成萬的先烈在我們前頭英勇地倒下了,其中就有許多和我並肩戰鬥過的首長和戰友,他們沒有能夠看到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祖國的強大,但是,他們的功勳業績是永存的。”
父親和他的戰友們早已離我們遠去,但他把無私的大愛留在人間;他們的功勳萬古流芳!
親愛的父親,我們永遠懷念您!
圖為麻城市將軍園父親的墓碑和銅像
2022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