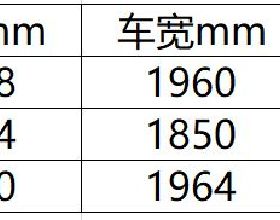“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歸”,光緒十四年(1888)七月,73歲的彭玉麟,在衰病之中最後一次平靜而決絕地向朝廷表達了辭官還鄉之意。
次年3月,孤獨的老人隻身返回湖南衡陽老家,兩年後,這個曾經叱吒風雲的湘軍水師統帥,在其搭建的草樓“退省庵”中平靜辭世……
在湘軍陣營之中,彭玉麟既有儒將羅澤南、李續賓等人的詩文才華,又不乏曾國荃、鮑春霆之輩的勇武彪悍,可謂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的全能之才。
尤其是在晚清追名逐利的政治氛圍和烏煙瘴氣的官場環境中,一生淡泊名利,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的彭玉麟,猶如芙蓉之離水,又恰似傲雪之寒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完美得就像一個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異類”。
為官不趨權貴,為將不圖名利,為臣無傾軋倨傲之心,只可惜這麼一個可為天下文士、軍人、官吏之楷模者,卻又是個命運多舛的可憐人。
少年痛失其怙、中年深囿於情、老來悲喪獨子,雖是沙場之上縱橫捭闔、無所不能的統帥,卻又一生都沒有走出情感的囚籠。
血染征衣鬢染霜,百戰歸來只畫梅,最終孑然一身,結草廬數間於鄉野孤獨終老。
1890年,隨著彭玉麟的悄然離世,大清帝國黯淡黃昏中最後一抹斜陽緩緩消逝,而塵世間卻從此多了無數個關於“雪帥”的傳奇。
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
嘉慶二十一年(1816)冬,一個寒風凜冽,大雨如注的夜晚,彭玉麟降生在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其父彭鳴九乃是當地三橋鎮巡檢,一個從九品的基層官員。
五年後,彭鳴九調任合肥縣梁園鎮巡檢司,並再添次子玉麒,一家四口雖算不上大富大貴,倒也其樂融融。
彭鳴九非常重視兒子的教育,早早便為長子請來先生,教授“四書五經”,而彭玉麟天資聰穎,詩書進步神速。
閒暇時梁鳴九也不忘傳授兒子一些槍棒拳法,用以強身健體。而梁園又是河汊縱橫,湖泊密佈之處,少年彭玉麟最喜放課之餘,與三五好友結伴戲水,也因此練就了一身浪裡白條的好身手。
只是誰又能想到,當年安徽鄉下無名池塘中撲騰玩鬧的少年,多年以後竟然成為縱橫千里長江的湘軍水師創始人,當然,這都是後話。
十五歲之前,彭玉麟的生活是快樂、充實、無憂無慮的,直到某次去懷寧外祖母家探望,邂逅了讓他一生刻骨銘心的“梅姑”。
梅姑是外祖母收養的義女,為其起名“竹賓”,竹賓姑娘雖在名義上與彭母王氏同輩,但實際年紀卻比彭玉麟還要小上兩歲。
玉麟善水墨,尤好畫梅,而竹賓又出身書香門第,琴棋書畫無所不精。少年揮毫潑墨,少女紅袖添香,相仿的年齡、相同的興趣讓兩人產生了許多共同語言。
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又都是情竇初開的年紀,一來二去之間,彭玉麟和竹賓便由對彼此的好感而互生情愫。
起初家中長輩並未察覺異常,直至二人越走越近還愈發親密,過來人的彭母王氏漸漸發現了端倪。
兩人雖無血緣,但在名分上仍然屬於姨甥關係,礙於顏面,母親並未直言,但此後便極力反對彭玉麟再到外祖母家中串門。
而母命難違,彭玉麟雖黯然神傷,也只能默默接受。
1831年,彭玉麟的祖母於湖南老家去世,彭鳴九年少離家闖蕩,老夫人于衡陽獨自支撐彭家門庭三十餘年,箇中辛苦自不必言。
如今老母撒手人寰,彭鳴九深感虧欠愧疚,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放棄仕途,舉家搬回湖南。
離開之日,舅舅前來碼頭送行,許久不見的竹賓竟也跟隨而來,久別後短暫的重逢雖然甜蜜,但更多的卻是離愁與不捨。
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湖南與安徽之間,相隔何止山水萬重,即將分別的小情侶執手相看淚眼,自知此地一別,恐怕今生再難相見。
原本故事至此,這段懵懂的愛情也就隨著兩位主角的天各一方而被迫畫上了句號,但生活卻偏偏要讓二人再次相遇,又以最殘忍的方式讓彼此分開,最後,留下彭玉麟用一生的時間慢慢品嚐思念與孤獨。
死生契闊,人間無常
回到家鄉之後,彭玉麟寄情于山水之間,整日遊山玩水,暫時忘卻了煩惱,但沉重地打擊又一次悄無聲息的降臨了。
原來,彭鳴九此前在安徽時,曾委託族人在衡陽渣江老家置辦了一些田產,處理完母親的喪事後,便向親戚索要,誰知這些親戚欺負彭鳴九離家多年,在當地既無實力又無倚靠,便對收錢買田之事矢口否認。
彭鳴九本有重疾在身,迴歸鄉里又遭族人欺凌,悲憤交加之下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了。
父親突然辭世,只剩彭玉麟兄弟與母親相依為命,而失去了彭鳴九這個頂樑柱,彭家境況也是日趨艱難。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身世可憐的孤兒寡母不僅沒有喚起鄉鄰左右的同情,那些曾經算計過彭鳴九的親戚,又開始變本加厲地欺負他的孩子。
當時,彭玉麟年僅十三歲的弟弟因為要補貼家用,只得做點小生意,誰知某日在外搬貨時,竟被親戚們合夥打倒,然後丟入池塘,幸好彭玉麒水性不錯,才倖免於難。
聞聽弟弟的遭遇,血氣方剛的彭玉麟便要抽刀出門報仇,卻被母親死死拉住,只是經此一事,王氏深感老家不可久留,便囑咐兄弟二人出外另謀生路,而自己則留守家中。
彭玉麟離開家鄉,前往府城衡州,隨即考入了當時衡陽最好的石鼓書院,有趣的是,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曾國藩也曾在此處求學,而多年以後,湘軍水師又正是由石鼓山麓之下的江面開拔,曾國藩、彭玉麟、湘軍水師,不知冥冥之中是否一切早有安排。
在書院求學之餘,為了賺錢養家餬口,彭玉麟考入了衡州府城中一支綠營騎兵部隊,充當文書。
在這裡,彭玉麟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位貴人——時任衡州知府的高人鑑。
某日高人鑑來軍營拜會協鎮,偶然發現案頭彭玉麟的文書,字型俊美,不禁大加讚賞,又見其人談吐得體,氣宇軒昂,知府愛才,便將彭玉麟收為弟子,親自為其傳授學業。
得知府青睞,彭玉麟在衡州漸漸有了些許名氣,人生的道路也因此而順暢了許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遠在安徽的舅舅突然病逝,年邁的外祖母和竹賓姑娘孤苦無依,生活陷入了困頓。
此時彭家雖然並不富裕,但生活已漸漸有了起色,因此彭玉麟毅然決定將二人接來衡陽居住。
當日梁園碼頭一別,不覺已是一十二載,有情人再度重逢,頓時燃起了比當年更為炙熱的愛火。
只是時過境遷,彭母固執的倫理觀念依然沒有絲毫改變,眼見二人卿卿我我,你儂我儂,又同在一個屋簷下,王夫人每日如坐針氈深怕他們做出有辱門風之事。
1845年,外祖母病逝,王夫人便立即將“妹妹”嫁了出去,可憐竹賓寄人籬下,只能聽憑擺佈,而彭玉麟又十分孝順,即使面對母親無情的棒打鴛鴦,也只能再一次逆來順受。
緊接著,母親又安排為彭玉麟完婚,只是來自普通人家的妻子鄒氏,與其完全沒有共同語言,而且婆媳之間關係也相當惡劣,每日爭吵不斷,這段婚姻沒有讓彭玉麟感到一絲甜蜜,只有無盡的煩惱,同時心中更加思念已嫁做人婦的梅姑。
鄒氏過門第二年即產下一子,但夫妻二人的感情並未因此得到任何的改善,終於又一次鄒氏與母親激烈爭吵後,彭玉麟從此便不再理睬妻子,直至鄒氏離世,兩人始終都形同路人。
1849年,竹賓意外死於難產,夫家以為不祥,將其草草安葬。噩耗傳來,彭玉麟痛不欲生,既痛心竹賓的悲慘遭遇,又痛恨自己的懦弱無能。
此後,彭玉麟親自前往梅姑墳頭祭拜,青山依舊,而伊人已去,回憶過往種種,怎不令人肝腸寸斷。彭玉麟淚如雨下,久久不願離去,心中暗暗發誓,有生之年,定要畫萬幅梅花,以酬謝紅顏知己,更為紀念這段天人永隔的愛情。
此後數十年,彭玉麟始終孑然一身,再未納妾,而且無論是與太平軍作戰還是巡防長江,無論公務繁忙與否,始終堅持每日畫梅不輟。
人生有很多錯過,有“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的遺憾,有“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的無奈,而梅姑的紅顏薄命,彭玉麟的一生痴情,以及兩人命中註定的有緣無分,似乎更讓人為這種“錯過”而惋惜。
守耒陽鋒芒初露
只是還來不及悲傷與消沉,作為軍人的彭玉麟便遇上了其戎馬生涯的第一次大規模戰鬥。
1849年夏秋之交,湘南遭遇水災,民不聊生,隨即李沅發聚眾於新寧起義,清廷隨即調遣兵力前往鎮壓,而彭玉麟所在的衡州協也參與其中。
其後,彭玉麟隨部隊一路轉戰湘桂黔三省,沿途多是叢山峻嶺、懸崖峭壁,條件艱苦,補給困難,但惡劣的環境也讓彭玉麟得到了極大的歷練。
最終,李沅發起義軍失敗,而彭玉麟不僅因功被授予藍翎頂戴,還意外獲得一個從七品的訓導之職。但考慮到渣江老家的母親年老體弱無人照料,事母至孝的彭玉麟毅然選擇辭官回鄉。
就像彭玉麟詩中所言,“書生從此卸戎裝”,離開軍隊後,其在老家專心侍奉母親,但好友在耒陽從事典當行,知道彭玉麟拳腳了得還能寫會算,經不過友人力邀,便勉強出任了當鋪管事一職。
其時,一場聲勢浩大、規模空前,日後更是席捲大半個中國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已經在廣西爆發,並迅速蔓延至湖南境內。
兵荒馬亂之際,耒陽也不太平,當地原本就有會黨組織,太平軍由桂入湘,受其鼓舞,會黨眾人亦準備攻擊耒陽縣城。
彭玉麟得知訊息,迅速報告知縣,誰知地方官老爺早已嚇得六神無主,慌亂中竟全權委託彭玉麟負責城防事宜。
不久,會黨大軍兵臨耒陽城下,是役,彭玉麟帶領毫無戰爭經驗的鄉民,先是頂住了會黨土炮的猛烈轟擊,又身先士卒殺退了強行登城之敵,最後更是出其不意率死士衝出城外,一舉擊潰會黨,解除了耒陽的威脅。
耒陽一役,彭玉麟初露鋒芒,其以一介布衣,卻組織山野鄉民擊退會黨數百人的事蹟,很快傳遍三湘大地,“彭玉麟”這個名字也漸漸引起了某些重要人物的注意。
1852年9月,彭母王老夫人離世,彭玉麟于衡陽守孝期間,恰逢曾國藩在此訓練水師,求賢若渴的湘軍主帥,對彭玉麟早有耳聞,悉其熟讀兵法,水性出眾,又擅長帶兵,便遣人上門遊說其出山相助。
只是彭玉麟始終以守孝三年未滿,不肯離家,最後還是曾國藩親自出馬,三顧茅廬令其深受感動,又用家國大義加以開導,彭玉麟最終答應隨其出山,加入湘軍水師,並由此開始其日後數十年波瀾壯闊的戎馬生涯。
平生最薄封侯願
1853年,湘軍水師在衡陽完成籌建訓練之際,太平天國摧枯拉朽的西征也由長江下游浩浩蕩蕩直抵湖南。
湘軍主帥曾國藩奉命率十三營陸師、十營水師,共計萬餘名湘軍將士沿湘江馳援長沙,在這裡,彭玉麟迎來了其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水戰。
此時,西征軍主力由林紹章統帥,陳兵長沙南面的湘潭,而北面則由老將石祥貞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
面對太平軍對長沙的南北夾擊之勢,湘軍內部對先攻湘潭還是靖港產生了分歧,最後曾國藩採納了彭玉麟的意見,由悍將塔齊布統陸師五千,褚汝航、夏鑾、楊載福、彭玉麟等率水師五營,水陸並進,直撲湘潭。
湘潭之戰是太平軍主力與湘軍的第一次正面交手,也是關係到西征成敗和湘軍存亡的關鍵之役。
最終,雖然曾國藩沒有按照彭玉麟事前的計劃留守長沙,而是擅自帶剩餘五營水師偷襲北面的靖港,結果中伏慘敗,湘軍主帥羞憤投江自盡,幸被左右救起。
但好在湘潭主戰場,塔齊布與彭玉麟這一路湘軍取得決定性勝利,打敗林紹章的西征太平軍主力,並正式拉開了湘軍反攻的序幕。
而此戰過後,不僅讓曾國藩對彭玉麟刮目相看,更由此確立了彭玉麟、楊載福對湘軍水師的領導地位。
湘潭之後,湘軍進攻嶽州,江面之上雙方炮艦互射,一時彈矢如雨,濃煙蔽日,而彭玉麟傲立船頭,不顧危險親手點燃大炮,一舉擊斃對面太平軍將領,兩艦交錯之時,又身先士卒,抽刀登舟,斬殺太平軍丞相。
太平軍陣腳大亂,隨即四散潰逃,而彭玉麟因嶽州之功,賞加同知之銜。
此後無論田家鎮半壁山之役,還是九江湖口水戰,抑或最後的天京圍城,彭玉麟統領湘軍水師,不僅智計百出,且每每必親臨戰陣,而其麾下丁勇受主帥感召,亦是竭盡全力奮勇爭先。
諸將衝鋒,玉麟每乘小船督戰,以紅旗為識,或前或後,將士皆惴惴盡力
——《清史稿·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隨著戰爭的進行,彭玉麟聲名鵲起,因其字雪琴,故而湘軍內部皆尊稱其為雪帥,而朝廷對這位文武雙全的水師將領也十分讚賞,一路恩賞不斷。
但彭玉麟上陣殺敵只為報效國家,功名利祿只是過眼雲煙,雪帥根本未嘗放在心上。
1861年,湘軍攻克重鎮安慶,戰後敘功,僅僅秀才出身的彭玉麟,被破天荒地實授安徽巡撫,但面對這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封疆之職,彭玉麟竟以不善政務為由,固執的三次上書請辭。
如此做派在當時簡直不可思議,一時之間朝野譁然,輿論更是指責其沽名釣譽、惺惺作態。由此也可見晚清的官場是多麼的畸形而可笑——潔身自好即是假清高,不同流合汙便是真敵人。
當然,彭玉麟不會活在別人的議論之中,他有自己的操守和堅持。1865年,平定太平天國後,清廷又委以漕運總督之重任,彭玉麟又再次固辭不受。
即使在1881年,清廷命其代理兩江總督併兼南洋通商大臣,這一職位在當時僅次於號稱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可謂是位極人臣,但彭玉麟依舊選擇辭去。
終其一生,彭玉麟始終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且從未對高官厚祿產生過任何興趣,這一點不僅在晚清的官場十分罕見,即使與同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相比,也顯得尤為突出。
就像其詩中早已表明過的心跡“平生最薄封侯願,願與梅花過一生”——人世間那些名利,他早已看淡,而他在乎的,卻已永遠埋葬在了1849年的秋天,湖南鄉間那孤獨的墳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