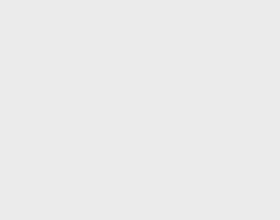一個人,要想自由,萬不可有宗教信仰;要想自立,萬不可沒有宗教情懷。
我這話,左邊得罪了信徒,右邊得罪了無神論者,可還是堅持。
1、有所信賴
對喜歡思考的人來說,現實世界最討厭的地方就在於絕對的變動和絕對的差異——運動是絕對的,所有的靜止都是相對的;差異、多樣是絕對的,相同點是相對的(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我們敢於把它們都叫“樹葉”,是因為我們選擇性地忽略了它們的不同)。
變動和多樣化的世界,給人類可憐的智識帶來很大的挑戰。
人類理性偏愛那些靜止的、同類的認識物件,它們更容易總結、歸納、掌握。但是世界恰恰是混亂的、多元的甚至是無厘頭的,理性在這裡會亂了陣腳,甚至會失去安全感。最好能打造一個穩定的底座,把這個滑溜溜、無處下手的世界鑲嵌其中,它是分解世界的座標和操作檯。有了這個東西,我們才能重新討得心安,有足夠的底氣和這個世界糾纏、對峙。這個底座、這個座標是超於變化、絕對靜止的。
上哪去找這個底座呢?只能超出世俗社會之外去尋找。
宗教信仰是一種很方便的策略,它為人們設定了一些神靈和偶像。
這些神袛,他們作為世界的創造者和維護者,站在宇宙的歷史之外,超然獨立於所有因果鏈條,甚至獨立於時間存在。他們不以任何事件為因,因此也不受任何因素的制約。
但他們卻必須是所有事件的因。
每一事件都有前因後果,我們可以無限地往前追溯,但如果沒有一個終極原因(即它只能是別的事件的因,它前面再不能有原因——它以自己為原因),那麼這個因果鏈條上的多米諾骨牌將永無休止地推下去,這樣一個沒有盡頭、沒有邊界的推演是人類理性無法接受的,必須在某一個退無可退處有個了結,在那裡承擔了結任務的肯定是一個別的事物都依賴它,而它卻不用依賴外物的一個絕對獨立的事物——它是終極原因,是世界的源頭。這個源頭那麼堅強、那麼穩定、那麼絕對自足,它只給予,而從不索取,它只能是神。它所有事物的源頭,它保留這個世界所有良善與罪惡的最終解釋權。
有了他,世界就算再多動,也似乎有了根;就算再混亂,也似乎有了譜系。我們的心也似乎有了歸處。
可是宗教信仰畢竟是一種偷懶和敷衍:
首先,這個無所不能的神本質上只是一種設定(甚至假定),而不是我們探索和追問的結果,是否真的有這樣一個如我們所期待、如我們所相信的神呢?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我們只是願意這樣相信,但你我都知道,“願意相信”並不代表真的存在——認識論層面上的必然和存有論層面的實然畢竟是不沾邊的。
只要有這樣一個設定,幾乎所有棘手的問題都可以一勞永逸地推給他——那個全知全能的神。那些傷腦筋的自然謎團都屬於“預定和諧”,我們只需要訓練自己接受它就可以了,研究的事情往後放放也無妨;至於善惡報應的問題,神也已經在來世安排妥當,我們只要安心吃虧就行,制度層面的改革和革命純屬瞎操心。
宗教偶像是個很奇怪的角色:他實際上什麼具體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人類照舊如此無知和無能,但是我們卻在他身上獲得了心安,也就是對那些未知和不公迅速達到見怪不怪的心境,我們稱其為“境界”、“得道”。
與宗教信仰急於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不同,宗教情懷不會無中生有、越俎代庖。它不會固執地呼喚一個固定不變、完美無缺的本體,它願意承擔一個變動、混亂的世界,並且鼓勵我們在這個混亂和變動中自主地、一點一滴地制定一套秩序。
不過,它也認為有些東西是不能變的,但這個東西不能是一個虛幻的安慰,而是一套元價值——不管世事再怎麼變換,我們每個人心中應該有所堅守、有所秉持,以心中的不變來應萬變。比如到什麼時候都不能損人利己、不能自私冷漠,這是超越所有時代和立場的絕對命令。
為了滿足精神依賴,宗教信仰不惜設立一個幻影,但是宗教情懷劃定的卻是一種要求。
它要求我們勇敢地面對世界,不僅如此,還要求我們堅定自己的操守,活成一個大寫的人,這樣活著當然會比隨波逐流更難,但是等回首往事時,我們會發現這個情懷給自己修建了一個牢固的精神大後方。
2、有所敬畏
當生產力跨過溫飽水平線時,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更加從容的發展階段。
我們最大的敵人不再是自然界,而是自己。更確切地說,是自己的慾望。這個敵人比前者更可怕,自然界天生站在我們的對面,是一種天然的客體,我們自然地產生與它對立和鬥爭的想法。但是現在我們需要把自己當成敵人去戰勝和超越——對一部分自己的否定恰恰成了整體自我脫胎換骨的過程。
怎樣才自我戰勝和超越呢?要知道,一個人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這個比賽是很難進行的。
宗教信仰的辦法是設立一個獨立的意志、一個具象化的人格盤旋在你頭上,他俯視你、監督你,並有權對你進行即時的道德獎懲,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
如果這個獎懲遲遲不兌現怎麼辦?這個神明的公信力不是削弱了嗎?沒關係,他還會在你死後(或是世界末日)給你算總賬,決定你下一輩子的去處(就像期末給你兌換學分一樣)。
這樣一來,“善惡報應”就變成一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無法證偽的學說。從自身利害的角度出發,你倒不如權且相信它——如果它是假的,你僅僅吃點小虧而已;如果是真的,你就賺大了。這讓你始終覺得一個人的言行和慾念不可以太放縱,而是總要受到一個超於自己的力量的約束。
很多人將懷疑精神的矛頭指向“神靈”的有無上,這就無聊了。其實這裡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神靈是否真的存在,而在於:本想透過這一設定實現人們對道德的遵守,但卻導致神靈和道德的雙重跌落。
神靈變成一個瑣碎又專制的班主任,他只知道帶著挑剔的眼光在凡人身上尋找慾望的馬腳,再不復設定之初寬宏、高邁的形象。
而道德呢?變成了一個靠恐嚇和威脅得以維持的專制秩序,我們無法分清那些仁義禮智信到底有多少是發自內心而值得感佩的,又有多少是出於對懲罰的恐懼不得已而為之的。
道德變得如此世俗和功利,也就失去了崇高之美。
人應該有敬畏,沒有敬畏之心的人是可怕的,他們的心裡只有工具理性而沒有價值理性,這樣的人做出多麼超乎倫常的事情都不應在意料之外。但是如果像宗教信仰一樣,將敬畏之心託付給一個外來的、具象化的人格身上,這無異於一場意志層面的自我閹割,這樣的敬畏只會讓人變得愚蠢,並由愚蠢衍生出殘暴。
宗教情懷致力於保留和淨化這種敬畏之心,它敬畏的物件是心中的道德律令,請注意,這個道德律令不是社會和歷史中現成的風俗習慣,而是經過自我理性充分審定的、心悅誠服的絕對命令。這樣一來,這種敬畏之心指向的並不是外在力量,而恰恰是自己。
自己為自己立法,理性為言行跑馬圈地,在其中,自由才能得以伸張,人格才能得以挺立。
3、有所期待
現實生活和理想狀態總是有差距的,我們為自己設立了值得相信、值得敬畏的東西,不折不扣地去遵照執行。但是然後呢?
當你看到有人把你的原則棄如敝履、貶為“迂腐”,利用你的堅守佔你的便宜、搭你的便車。你發現,公平正義並不能時時刻刻、足斤足兩地滿足我們,你終於對堅守的東西產生了疑竇。
當你遇到了死亡,這種疑竇發展到了極點。死亡作為一種極端的幻滅,它將你的生命連帶你生命中所有的意義都送進墳墓。你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堅守與敬畏,和你的腸胃、你的容貌面臨同樣的腐敗命運。所有的標的都顯得可疑,所有的功業都歸於沉寂,不管你生前多麼高尚、多麼規矩,死亡帶來的孤獨與恐懼似乎總能一下子把你打回原形——一個有死之人能期待什麼,敢索要什麼?
宗教信仰透過給我們許諾一個幸福的來世或得救的靈魂,來消弭對死亡的恐懼。它告訴我們人死之後會去到另一個世界或者會重新回到這個世界,你下一段生命的生活質量直接和你今生的績效掛鉤。於是你有了期待——期待來世的幸福和死後的審判。
不得不承認這是一舉兩得的做法:
一方面,它把死亡變成了今世的視界而不是終點。死亡不再是一個無法凝視的深淵,它只是靈魂無限轉世中一個階段的告終。
這種對死亡的淡化,其關鍵就是靈肉二元論。
我們發現,不論什麼宗教,無論對死後生活的描述多麼大異其趣,有一點不約而同,那就是靈肉分離:肉體的腐爛是顯而易見的,這裡做不得信仰上的手腳,於是就有了靈魂不死的設定,靈魂在肉體腐爛之後承載著生命的形式,也繼承了生前的福報與罪愆(當然也承載著淡化死亡的期望)——升上天空。
有了靈魂,死亡就變得不再那麼嚴重,因為生活還可以繼續(雖然是以一種我們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形式),我們也因此可以保持期待。
另一方面,死亡變成一個把柄:你在現世要好好表現、要隱忍、做個好人,來世或死後你就能獲得幸福。否則另一個世界的你將不得不為現在的你埋單——你現世的行為是對另一個階段生活質量的投資。於是,死亡不僅被淡化,甚至還被庸俗化了——庸俗化成為一種兌現過程。
死亡是人類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的教育契機:正因為不得不面對終有一死的殘酷現實,我們才願意去壓縮生命的密度,擴充生命的價值。
死亡逼著我們學會思考,學會與世界、與自己相處。我甚至認為死亡是人類文明得以進步的根本保障,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死的人類會創造出文明,這句話本身就是個悖論。
只是,諷刺的是,這種將死亡淡化乃至庸俗化的結果,竟然出自於以超越死亡為己任的宗教信仰!
我們起不去探討靈肉是否二元,也不爭論是否有天堂地獄、轉世輪迴,其實問題也不在此。
任何企圖讓死亡落地的執念本身就是錯誤的:有些讓我們難受的事情不一定應該被消滅或被解決。生存本來就不應該是一件多麼輕鬆的事情,輕鬆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狀態。宗教追求內心的寧靜固然不錯,但是寧靜卻不等於安逸。混淆了這二者,宗教被指責為“精神鴉片”委實不冤。
宗教情懷對待生命與死亡有自己的立場。
在常人看來(甚至一些宗教家看來),生命是一個畫得好或畫不好的圓,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讓自己的生命“圓滿完成”。宗教情懷也要求人們熱愛生命,但是在它看來,生命是用來揮灑的,而不是有待完成的。把生命浪費在那些美好而有意義的事情上,才算對生命的尊重,我們就不虛此行、就“值了”。
就像一道美食,它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被做出來、被完成,而是被吃下去。
生命的結局不應是封閉的、唯一正確的,而是開放的。生命變成一種姿態,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姿態,求索和進步永遠是進行時:當可能性敞開時,我們盡情去創造,當它關閉時,創造戛然而止,乾淨而決絕。因為宗教情懷早已經知道,在和死亡的戰鬥中,不可能有功德圓滿,也沒有徹底的勝利,我們不可能打敗什麼,我們所能做的僅僅是不在荒蕪的世介面前認輸。
這樣的死亡觀才是真正灑脫的死亡觀,我們不會在死後期待什麼,因為今生該做的、能做的,已經都做了。那些沒來得及做的,如果假我以時日,也一定能做到,只是時間不夠了而已。
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義。
4、有所擔當
宗教從來不止於獨善其身,它認為自己超越了飲食男女的瑣碎和貪慾,懷著巨大的優越感去悲憫和同情。在宗教眼裡,世俗世界充滿了假象和執念,是個不堪的所在。信徒們不能光顧著自己的超拔,也要幫助更多俗人認清世界的真相,將他們從迷思和迷狂中解救出來。
諷刺的是,最倡導寬容和憐憫的宗教,往往引發最殘忍的黨同伐異。宗教的精神一經落地,勢必沾染上狹隘的人性,走向變態和凋落。這是宗教的尷尬,更是歷史的永恆輪迴。
宗教情懷呢?
宗教情懷保留了宗教中最基本的慈悲和博愛,它沒有具體的偶像和信條,所以不會滑向狹隘的原教旨主義。它也不會一廂情願地去救贖、去推銷,更不會將自己的思維和價值強加在別人頭上。它甚至反對任何脫離世俗的優越感,它堅信世上沒有聖賢、沒有先知、沒有神意的代言人——所有人都是凡人。
它不願意用內心的慈悲和博愛去做太大的事業,而是隻想含著它們,用它們去理解異乎尋常的現象、寬宥加諸於己的傷害、體察灑掃日用的人情。
它當然不拒絕擔當,但它更知道越俎代庖本質上就是一種傷害,所以它只擔當應該擔當的那一部分。
正心、誠意、修身是自己的事,但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前一定要徵得別人的同意。
不管迎來多少指責,在未以理性說服之前,我還是堅持認為宗教信仰是一種思維層面的偷懶行為,一種價值層面的畫地為牢,一種生命意志的蜷縮乃至自我閹割。
但是生命要想進退有據,動靜有序,必須有所堅守,至於堅守什麼,必須由理性和自由意志說了算,而這二者最終會凝結成同樣虔誠的情懷,我無以名之,只好稱之為“宗教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