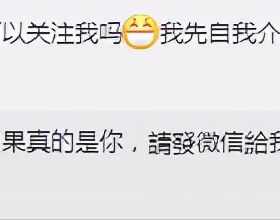【戲劇名家講故事】
在一次我的作品研討會上,大家對我的發言做出規定:不談創作,只講人生。當時我講了我自己的人生,但同時向大家說明:人生就是創作的全部,而花環是由荊棘編成。
1950年,我從破裂的家庭出逃到西安,養母收容了我。那年我十二週歲。這該算我第一次人生選擇。
和養母生活了不到一年,因為養母的三姨對我態度輕慢,我再次出走考入西北戲曲研究院學唱秦腔。那是我第二次人生選擇。在西北戲曲研究院演過《十二把鐮刀》《打金枝》《血訓圖》均不成功,終因不得要領而改行做了打字員。
因禍得福。我為大劇作家馬健翎院長列印劇本,猶如上了古典文化藝術培訓班。以後我又多次在他下鄉體驗生活的時候為他做速記員。受了他的培養和薰陶,提高了文化,同時產生了幻想。我不知天高地厚在日記裡寫下:要把他作為我奮鬥的榜樣。心裡醞釀著第三次人生選擇。
一九五七年,我十九歲,考入陝西省話劇團學做話劇演員。我買了一套莎士比亞全集和剛剛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在寄賣行買了一隻舊唱機和兩張舊唱片,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貝多芬的《命運》。沾著三秦文化的泥土走進西方戲劇世界,開始拼搏。我如飢似渴地按《辭海》文藝分冊的條目讀書自修。四十歲時,我終於站在了主考官徐曉鐘面前。第一次體味到平等競爭的尊嚴,體味到人的價值被承認的幸福,在等待錄取通知的兩個月時間裡,我設計著第四次人生選擇的前景。我的生命來之不易,她在屈辱中度過了一半,我要用未來的一半證實我全部生命的價值。從踏進棉花衚衕的那一刻起,我從不敢懈怠,我愛我的母校,敬重我的恩師。中央戲劇學院校園是人生苦旅中的一片綠洲,我在那裡修身養性,苦解真經,徐曉鍾教學小組給予我們這一批四十歲左右的大學生嚴格、科學、精密的訓練,我的藝術生命從這裡開始。
導演系的第一課是導演職責,導演職責的第一章是導演對人類和人類文化的責任,我不敢只為證實自我而褻瀆了神聖的、我心中的藝術。學成畢業,我抱著把陝西人藝建造成真正的藝術聖殿的理想回到西安。在完成了劇院選定的兩個劇目後,我發現了《女人的一生》這部日本名作。這部作品給表演藝術留下了充分的創作空間,我想從培養演員出發,實現我的理想——用經典作品建設演劇隊伍和觀劇隊伍,澆灌荒蕪了十數年的戲劇土壤。幾部經典作品的連續排練和學術探討,給劇作家注入新鮮血液,提高了劇目的創作。《女人的一生》創作活動初見成效,並於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西安首演成功。
在這次創作活動中,陝西人藝及陝西文化廳、陝西文藝界給予我極熱情的支援。上座率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連續演出七十三場。召開了各種座談會。從觀劇情緒及座談會上的發言中,我們的追求得到證實。觀眾在獲得欣賞滿足的同時思考人生選擇的主題。
第一屆戲曲現代戲年會在西安召開,與會代表觀看了演出,賀敬之、劉厚生等給予我們充分肯定並建議我們進京演出。陝西人藝成立三十餘年從未去過首都,這個提議振奮了全體演職員。老院長周軍派我赴京聯絡。在北京我得到了藝術院團體制改革的資訊。聯絡好演出,趕回西安,將資訊帶回了劇院;不料因了這樣一個原因,赴京事擱淺。藝術院團體制改革深得人心,許多青年建議我組建藝術承包隊伍,實施我們的理想。
經過幾個月的醞釀,自由結合的藝術承包隊成立。藝術承包隊的第一項措施是復排《女人的一生》並進京演出。一九八三年春節我登上空蕩蕩的列車,再次進京,為第一個話劇承包隊聯絡演出。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女人的一生》在北京首演成功。
一九八五年正月初七,我帶著《奧賽羅》導演計劃走進這幢小樓(研究會會場西交民巷38號鐵路話劇團),向領導講述了我的《奧賽羅》的故事。經過半年考核,他們接受了我。一九八五年十月正當我向團部遞交《奧賽羅》排練報告的時候,中國第一屆莎士比亞戲劇節於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召開的通知下達。當時的兩級團長立即拍板定奪,並撥款一萬元。
我相信,美,是永恆的。這信念,成為這次創作《奧賽羅》的焦點。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莎翁生日的這一天,中國第一屆莎士比亞戲劇節在北京開幕。中國鐵路文工團話劇團演出了《奧賽羅》!
再以後的事,在我的那張創作年表上都有記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女班話劇《奧賽羅》在上海首演,我也曾手寫書信,邀請張文宏醫生來觀看。
我的人生是隨著時代而演變的戲劇人生。我的戲劇是時代演變中的人生戲劇。
(作者:陳薪伊)
人物連結:
陳薪伊,國家一級導演。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特殊貢獻話劇藝術家”稱號,從事戲劇創作近70年。連續10屆、14次獲“文華獎”系列獎項。早年因成功導演日本話劇《女人的一生》及莎士比亞悲劇《奧賽羅》成名。代表作有話劇《商鞅》《白居易在長安》、京劇《貞觀盛事》《梅蘭芳》、歌劇《張騫》《巫山神女》等。
來源:光明日報